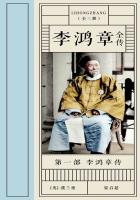我回答他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所有的赫列斯塔科夫在这一幕都不是这样演的,我想跟他们不同。他问道:“您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要像您那样表演呢?”
我三言两语说明我所遵循的设想,马尔蒂诺夫沉吟了一会,说道:“我不想马上就答复问题很有意思今天晚上到我那里去吧,咱们随便聊聊。”
我当然赶紧到他那里去,急切地等待着他的“解答”。
“今天我看了您的排演回家,”他说,“特地再看了一遍第三幕,看了果戈理关于《钦差大臣》演出的信《〈钦差大臣〉初次公演后作者迅即写给一个文学家的书信片断》。,然后又以理由最充分的方式想象了一下”
“我应该认为自己是失败的?”
“您就假定不是吧。我得出结论,您是对的只不过您的表演中也有不足之处,还不是小小的不足,一定要纠正。大概正因为这缘故吧,我第一次看时没有同意您的看法。”
“究竟什么地方不足呢?请您指出!”
“您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您说,赫列斯塔科夫在这一场中的处境是悲喜剧式的,正如您告诉我的,他说得很对啊,那叫什么来着不过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说得清楚些(一般说来,马尔蒂诺夫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观点是很吃力的,因此,许多对他不甚了解的人,凭第一个印象作判断的人,总是肤浅地认为他‘知识有限’)既然是悲喜剧式的,那么,应当是既有悲剧的,又有喜剧的您把赫列斯塔科夫演成叫什么来着,演成英雄——又用姿势,又用声调,又用手势去演;您演得很好(尽管只有一次嗓子‘发沙’,演员可千万不能这样!),可是实际上喜剧的成分很少,脸上的很少,丑角身上,嗯,甚至作的怪相都很少喜剧性(因为这儿不作怪相不行)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说清楚,您是否了解我的意思最好等一等,让我做给您看您给我提词,——拿着书不大方便。”
他在扶手椅上坐下,照着我的“提词”开始念起他记忆中相当熟悉的那一段独白,开头是讲彼得堡的舞会。这段台词念得我不满意。作为一个伟大演员的马尔蒂诺夫却是个蹩脚的朗诵者(例如法穆索夫的独白他就念得很不高明),加上赫列斯塔科夫这个角色跟他根本不对路。不过,为了给我上课,他这时已按照我的路子进行表演,从扶手椅上一跃而起,摆出“英雄”的架势,他脸上的表情,随着他念的台词,变得那样富有喜剧意味,变成“怪相”,就是他刚才提到的怪相,那实际上以惊人的面部动作装出来的,造成“悲剧性”与“喜剧性”之间那么富有艺术情趣的对比,那么富有艺术性的均衡配置,使我顿时恍悟了我那天才的老师刚才还不能十分清楚地向我讲述的东西是的,我明白了,同时也懂得了,理论上充分掌握这一课之后,在实际运用上我将仍然是自己的榜样的最苍白的拷贝。不过无论如何,按马尔蒂诺夫、皮谢姆斯基和若干其他人在总排演中对我所讲的话来看,这一课并没有白上。
题解:
彼得·伊萨耶维奇·魏恩贝尔格(1831—1908),文学史家,诗人,翻译家,《星火》杂志及其他期刊的撰稿人(见《〈星火〉诗人》关于他的部分,列宁格勒,1955年,第2卷,页617及其他)。1859年底,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回来后立即与之相识。六十年代初,他们两人积极参加文学基金会的活动。魏恩贝尔格所述的演出是1860年4月14日举行的。(见资助穷困文学家与学者协会出版的《二十五年文集,1859—1884》,圣彼得堡,1884年,页431—432)
尤·费·潘捷列耶夫尤金·费奥多罗维奇·潘捷列耶夫(1840—1919),参加六十年代革命运动,“土地与意志”社成员,1877年起任出版人。所说的演剧与事实稍有出入。(《回忆录》,页229—231)对演出的评论见《现代人》1860年第4期中的《现代评论》,页445—446;《星火》,1860年,第17期,页177—179。
魏恩贝尔格所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贝京一角的社会意义的评价是很引人入胜的。它同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中对“西贝京们”的评价相呼应。
本文根据《帝国剧院年鉴,1893—1894年戏剧季节》附刊第三册,圣彼得堡,1895年,页96—108原文刊印。
《童年回忆》选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
安纽塔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每当有什么事情使她操心或特别感到兴趣的时候,她总是这样踱步。这时她的神情是那么心不在焉,灿烂的绿眼睛变得完全透明,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她常常随着自己的思绪的节拍在走动,这一点连她自己也没有察觉。如果心情哀伤,她的步子就缓慢,懒洋洋的;如果心情兴奋,她开始在考虑什么,她的步子就加快,到末了,她不是踱步,而是满屋子奔跑了。家里的人都知道她有这个习惯,都取笑她。她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常在暗地里观察她,因为我很想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尽管我凭经验知道这种时候走到她身边去是没有用的,不过此刻我看到她一直走个不停,我终于熬不住,拿话儿去试探她。
“安纽塔,我无聊极了!把你的书给一本我看吧!”我以撒娇的声调要求道。
可安纽塔继续踱来踱去,仿佛不曾听见。
又是几分钟的沉默。
“安纽塔,你在想什么?”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了。
“嗐,请你别来纠缠我!要我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呀,你还太小,”我得到的是轻蔑的回答。
这下子我可是委屈极了。“噢,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呀,你连跟我说句话也不愿意!现在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弗兰采夫娜,英国女人,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基家的家庭女教师。由于她经常和安·瓦·扎克拉尔冲突(玛格丽特·弗兰采夫娜轻蔑地称她是“女虚无主义者”,“进步小姐”),她不得不离开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基家。走了,我以为我可以跟你要好地待在一起了,结果你撵我走!好,我这就走,我一丁点儿、一丁点儿也不会爱你了!”
我几乎要哭了,我正打算离开,姐姐却喊住我。其实她自己也巴望跟什么人谈谈她心里翻腾着的事情,可是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她可以谈谈的人,没有更好的听她说话的人,所以她也只好将就着跟十二岁的妹妹说说话了。
“听我说,”她说,“你如果答应无论怎样永远也不告诉任何人,那我就把一个大的秘密告诉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干了,仿佛我不曾动气过。我当然发誓我将守口如瓶,急切等待着她要告诉我什么。
“到我的房间里去,”她得意扬扬地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一样东西,你一定意料不到的东西。”
当下她带我到她的房间,走到一张古老的写字台旁,我知道那里面藏着她最心爱的秘密物件。她故意磨磨蹭蹭以延长我的好奇心的急切难熬的时刻,她慢吞吞地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只公事用的大信封,印着“《时代》杂志社”的红字。上面写着:陀姆娜·尼坚季西娜·库兹明娜收(这是我们管家的名字,她对姐姐忠心耿耿,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姐姐从这只信封里抽出另外一只稍微小一些的信封,上面写明:“转交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她终于把一封信交给我,信上是男人的粗大笔迹。这封信如今已不在我手头,不过因为童年时经常看了又看,所以已经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故而我以为我可以逐字逐句把它写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封信的原件不知下落。科瓦列夫斯卡娅转述的内容可能不确切。在《回忆录》中凭记忆复述的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第一篇小说《梦》也不确切。显然是把《梦》与《米哈伊尔》两篇小说搅在一起了,添加了许多东西。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女士!您的来信充满了对我的如此亲切而真挚的信赖,使我颇感兴趣,立即拜读您送来的小说。
坦白地对您说,开始看时我不无隐忧;我们,杂志社的编辑们,经常负有可悲的责任:年轻的初学写作者常把他们的文学习作寄给我们,要我们提意见,我们总是使他们扫兴。您的来稿如果这样我将深为惋惜。不过我一边看稿,一边我的忧虑也就渐渐消失,我越来越被您的小说里透露出来的少年的直率,感情的真挚与温馨的魅力所吸引。
正是您的这些素质使我对您产生了好感,以致我担心,是否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正因为这样,我还不敢公正而坚决地回答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您将来是否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女作家?”
我要告诉您一点:您的小说,我将(极其愉快地)把它刊登在下一期刊物上。至于您的问题,那么我要劝您:写吧,工作吧;其他的让时间来鉴定。
我不瞒您,您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不够完善、过于幼稚的地方;甚至——请恕我直言,甚至有违反语文常识的错误。不过这些微小的不足,您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总的印象是极好的。
因此,我再说一遍,写吧,写吧。如果您觉得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再多告诉我一些,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您多大年纪,生活情况如何。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我正确估计您的才能是很重要的。
您的忠实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看着这封信,惊奇得字行在我眼前飞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我所熟悉的;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吃饭的时候,姐姐和父亲争论的时候,常常提到。我知道他是最著名的俄国作家之一;可是他怎么会写信给安纽塔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一时之间我不由得想到,姐姐是否在作弄我,然后再来取笑我的轻信呢?
看完信,我默然瞅着姐姐,不知说什么好。我的惊奇姐姐分明非常高兴。
“你懂吗,懂吗!”安纽塔终于用快乐的、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了起来。“我写好一篇小说,跟谁也没有说一声,把它寄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不,你看,他发现小说写得好,要发表在他的杂志上。这样,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现在我是俄国女作家了!”她高兴得抑制不住,几乎大声叫喊道。
要了解“女作家”这个词儿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就应当记得我们是居住在乡村一般的偏僻地方,远离一切文化生活,甚至与文化生活的一点微弱迹象也相距甚远。我们家里看书很多,也订购许多新书。对每一本书,书上印的每个字,不但我们,而且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当作是来自远方的什么东西,来自神秘的异乡他国、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无论这可能显得多么奇怪,然而事实是,无论姐姐还是我,至今都还没有机会遇到过一个发表过作品的人,哪怕只发表过一行字的作品的人。虽然我们县里有—位教师,忽然传说他在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我县的通讯,我记得从那以后大家对他是如何地肃然起敬,直到后来才弄清楚这篇通讯压根儿不是他写的,是彼得堡来的某个新闻记者写的。
现在,我的姐姐忽然成了女作家!我找不出话儿来表示我的欣喜与惊奇;我只是扑上去搂住她的脖子,我们久久地亲热着,笑着,高兴得直说胡话。
姐姐不敢把自己的胜利告诉给家里的其他任何人;她知道,所有的人,就连咱们的母亲,都会大吃一惊,然后原原本本地去告诉父亲的。在父亲的心目中,她未经许可便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来评论自己,授人以笑柄,这种行径近乎大逆不道。
我可怜的父亲!他那么憎恨女作家,那么怀疑她们每个人的与文学无关的举动!然而命运注定他要成为女作家的父亲。
我记得,几个星期以后《时代》杂志来了,我是多么高兴啊,在目录页上我们看到:《梦》,尤·奥——夫作中篇小说(尤里·奥尔别洛夫是安纽塔取的笔名,因为她当然不能用真名去发表)。中篇小说《梦》发表在1864年第8期的《时代》上。
安纽塔自然早已照着她保存的草稿把小说念给我听了。可是现在,在杂志上看到小说,我却觉得是崭新的,异常漂亮。
初次告捷,使安纽塔精神大振,她立即着手写另一篇小说,几个星期后即告完成。这一回她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人,名叫米哈伊尔,在远离家乡的修道院里,由他当修士的叔叔教他念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第二篇小说比第一篇更加称赞,觉得它更加成熟。米哈伊尔的形象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的形象有些相似。中篇小说《米哈伊尔》发表在1864年第9期的《时代》上,作者称它为《见习修道士》。但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12月14日的信所证明的,这一名称“教会的检查机关认为不合适”。(《书信集》,第1卷,页381)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人,想在生活中寻找目标,实现他在快乐清醒的时刻所想象的崇高理想,他为此而苦恼。他离开修道院,想过一过尘世生活,失望之后,他又返回修道院,疑窦没有解决,就这样死了。在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小说中有些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因此,可以把佐西马长老死去的晚上阿辽沙的心情和米沙在教堂作礼拜时虔敬的狂喜心情作个对比。(《时代》,1864年,第9期,页8—10)若干年后,这部长篇小说问世,我看这部小说时,这种相似之处很引人注目,我向这时经常见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此事。
“这大概是真的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手拍拍脑门,说道,“但是,请相信我一句话,我在构思我的阿辽沙的时候,根本记不得米哈伊尔。不过,也许我无意识地梦见过他吧,”他想了想,又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