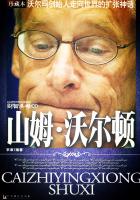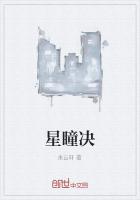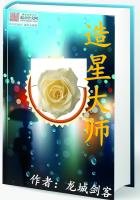当国民党要求各大学系主任以上的教授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时候,闻一多还天真地邀朱自清一块去登记入党(当时闻一多再三推辞未果,担任了清华中文系主任)。还是朱自清老练,提议“以未收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闻一多等人才没有成功加入。而这时候的闻一多对领导抗日的国民党还是很有信心的。不久,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情,完全改变了闻一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看法。
1943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其内容是: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主张恢复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重建社会道德基础。这一国策性著作发表后,立刻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自由知识分子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金岳霖拒绝阅读这部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闻一多读了之后终于恍然大悟:蒋原来是这种人物。他后来在回忆中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的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目睹了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和文化上的保守,连“最高领袖”蒋介石也要复古,背叛五四,闻一多是无法容忍的。他曾经崇拜的蒋介石不再值得信任,他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信仰上失去自由,再加上物质生活上的巨大落差,使他难以保持沉默。有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七七纪念会上,闻先生以响亮的声音,富有节奏的语调,忽徐忽疾地驳斥反动派污蔑学生运动的谬论道:‘有人说,近来昆明的学生又动起来了,是的,但是为什么?’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经济的负重,物质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让闻一多连自己在30年代研究学问的事都否定了,最终导致心理完全失去平衡。
交友说:身边不乏政治思想传播人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的人际圈往往会影响他的思想,这给剖析闻一多40年代的转变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除了自己本身的原因外,与闻一多交往甚密的几个朋友都是“左”倾知识分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晗、罗隆基和华岗,前两位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与闻一多是同事。罗隆基是清华园自由主义分子中最热心政治的一个。吴晗是比闻一多先一步,由学者转向政治的革命者,而华岗则是地地道道的职业革命家。
早年参加“新月”,闻一多是出于对诗歌、戏剧的热爱以及和徐志摩的友情。当“新月”的同人们为人权问题与国民党对抗时,闻一多却很平静,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做学问,毫无参与政治的兴趣。到了30年代,他还嘲笑罗隆基的政治热情,甚至还当面挖苦过他。但是,进入40年代,闻一多对现实生活极度失望后,改变了过去衡量人物的标准,只要对现实不满,在政治选择上和自己相同的,就会与他走到一起。最终,罗隆基成了闻一多进入民盟会的介绍人之一。
闻一多与吴晗性格气质截然不同,由于置身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走到一起。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吴晗当时是清华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清华当助教。后来,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去了昆明,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后,他又到联大,这时候两人还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吴晗在《哭一多》中说:“当你做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
在西南联大的吴晗小闻一多10岁,他身边有几个亲戚就是共产党员。与闻一多交往多次后,吴晗被闻一多的人格魅力和学识折服,同样,在大家都在对现实生活抱怨的时候,吴晗就会向闻一多谈起他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和描述他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这是闻一多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开始,但他并没想到要成为它的一员。闻一多早年参加过类似的社团活动,那些社团组织几乎和共产党同期诞生,那时的他对所有党派都是有成见的,所以他在20年代末期后,转向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在学校的几次人事斗争中,他已感到自己不是一个适合政治活动的人。但是,到了联大后,他却改变了青年时代的认识,重新热心于政治活动,这样的转变是非常不易的,同样也与吴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闻一多在加入民盟之前,曾和当时中国西南局的一个名叫刘浩的工作人员有过一次长谈。多年后,刘浩回忆道:“我和闻先生很亲切地畅谈了大约两小时,向他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主张,同时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闻先生很激动地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全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并说,现在有些人还看不清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
当时的吴晗已为民盟中央工作,他的活动目标很明确,就是在西南联大中发展一些教授进入民盟。而且,在闻一多加入民盟之前,他早年的许多朋友,如潘光旦、曾昭抡等人,已经是民盟的成员。可是,当吴晗请闻一多加入民盟时,他却并没有一口答应。他之所以犹豫,应该说其实也是顾及到了当时民盟里有些人的为人,不愿与这些人为伍,他有“不如加入共产党”这样的意愿,也是源于他阅读了共产主义的相关著作,对其中一些理念表示认同和理想式的向往。
当时的民盟,还是一个秘密组织,成员并不公开,闻一多的入盟词和登记表就被当场烧毁了。他加入民盟后,不少人对他的这一做法表示不解,柳映光在《闻一多就是我们的旗子》中这样描述:“当闻先生告诉我参加民盟的时候,我曾经劝阻他,我说:‘您没有加入的必要。’‘什么?没必要?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他先是很生气,后来又很缓和地说:‘连孙毓棠先生也这样劝我,唉,以前我们讲清高,故意表现狷介,其实这才是上当。历代的统治者们有意地提倡这一套,目的就在使大家不去过问政治,好让他们为所欲为。今天我们不再自己上当了。’”
加入民盟,是闻一多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原本就是一个专注认真的人,进入民盟后,他表现积极,还动员所了解的朋友和学生加入。他的朋友饶孟侃已信佛,闻一多还写了封公开信给他,说明自己这几年关心政治的原因。闻一多说:“念佛与革命,都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念佛看似通脱,实在通脱不了。革命呢?倒真是通脱得了的。”
闻一多加入民盟,纯属个人选择,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他本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做出那样的选择,除了个性、经济、交友方面的原因外,也与他所信奉的理想有关。他对他所信奉的东西几乎都当成一种宗教,这源于他浪漫主义的情怀。
吴晗使闻一多成了一个有党派色彩的知识分子,但在闻一多加入民盟后,是华岗对他不停地植入共产主义信念,从而改变了他所信奉的东西,也就是他的信仰。
当时华岗是中共地下党员,去昆明是因为中共派他去做大学教授统战工作。起初,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与罗隆基和高知识分子联络,他到昆明后就组织了一个西南文化研究会,该秘密组织的活动,闻一多都参加了。在获得中央指示吸收闻一多这类的教授后,华岗多次找闻一多开诚布公地长谈,使他“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闻一多终于走出了象牙塔,重新出现在战场上。不过,起初他是出现在文化批判的战场,至于政治批判,那还要过一段时间。这一过程也符合知识分子的思想逻辑和行动逻辑。但是,即便在他参加民主活动最积极的时候,他还是对吴晗表示,一旦民主自由实现了,他就要回到书斋去。
由此可见,闻一多并不像罗隆基那样,对政治一直有追求。他只是受到了外在的许多宣传的影响,主观地认为,当下的社会形势,只有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他理想中的东西。特别是当他阅读了《联(布)共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之类的革命著作后,他对共产主义理念十分认同,很快就将其升华成了他的信仰。为此,吴晗在一次纪念他的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闻先生在应允加入民盟的晚上,曾说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这显然是信仰驱使,其乌托邦的理想需要一个支点,因此他毫无功利地为自己选择一个类别,使他那楚人式的浪漫主义激情寻到一条皈依之途,让精神生活有寄托。
如今,在大环境的影响和渲染之下,人们所看见的闻一多,只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红色革命战士,他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底色却被掩盖了。其实,闻一多反对一切专制,而非只是反对这个专制,不反对那个专制。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闻一多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清华中文系,当时与闻一多一起变的,还有朱自清。但朱自清是边走、边看、边想,虽然有变,但骨子里是怀疑的。相比之下,闻一多却是坚定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早年接受过美式的民主自由教育,怀着无限激情,为那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一步步走向激进,无条件地走向左翼的怀抱。传统自由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就这样变为一个有党派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者的残暴杀戮中,被枪定格为为人民牺牲的革命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