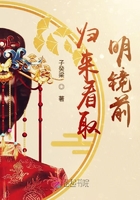世宗孝武皇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上顾群臣曰:“黯自言为便辟则不可,自言为愚,岂不信然乎!”
上世纪80年代,锐圆大学毕业,分配到报社写小评论,当时,选题是最头疼的事,每天抓瞎,有前辈告诉我:“没有题目,就写‘人才’,‘人才’是永恒的题目。”
“爱情是小说永恒的主题,人才是评论永恒的主题,哈哈,我明白了。”
当时,大家动不动就拿韩愈的《伯乐相马》说事,动不动就引用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当时引经据典的频率上,我们可以发现人才问题的根结所在:一曰“天公”,一曰“伯乐”,说来说去,人才是被动的,呼唤伯乐,祈求天公,多如牛毛的人才文章其实就是在“呼唤”和“祈求”的方式上变花样,看谁能说动圣心。
现在,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已经不是媒体报道的主流了,反对压制人才、浪费人才的文章也不多见了,因为伯乐多了,天公也多了,关键是伯乐与伯乐,天公与天公之间有竞争了,起码在官场和国有机构之外是这样了。
在大一统的时代,只有相马的机制,不可能有赛马的机制。所以,坐稳了江山的皇帝,从来是不愁什么人才的,汉武帝笑话汲黯的一段话,我认为点到了帝王体制下人才问题的关键:“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人中有才如苗中有秀一样,老天爷是自有安排的,不因治世而多,也不因乱世而寡,全在选拔、使用而已。而选拔使用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制度性的,如举孝廉、科举等;一是际遇型的,命好运气才学好,撞到了伯乐或者天公的鼻子下,一下子把你拎起来,你就是那个旷世之才。在古代,就仕途一条道,大家踊跃地往上挤,只要皇帝稍有作为,随便一整就是“人才济济”,真正牛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能有几人?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十斗米、百斗米折不折?
汲黯劝汉武帝爱惜人才,说他“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对汉武帝来说,人才是杀不绝砍不尽的,想为五斗米折腰甚至卖命的多如过江之鲫(古代未污染之前的江,才有这许多鲫,要按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多如太湖之藻”),所以,我以为汉武帝的人才观那是相当实事求是的。
帝王家摧残人才是平常事,一是因为垄断就业市场,永远不怕他人寒心,永远不怕名声不好,树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二是比起诸多奢侈糜烂来,废弃人才的经济成本太低了,根本不必要心疼。在这样的体制下,你给皇帝讲“万马齐喑究可哀”他是坚决不认同的,你磕头祈祷“我劝天公重抖擞”,天公说你丫纯粹多事:拉出午门把小鸡鸡割了!
皇上英明伟大,加上各种机缘配合,一不小心能混上个所谓盛世,仔细观察,盛世之下,果然是人才济济,不过也是些循规蹈矩的人才。真正的人才时代是在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竞争让尊重人才可以落在实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才是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