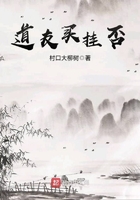我看着窗外,眼睛湿了。想着那两座高山,漫过桥的大水,泥泞的山路上一高一矮两个单薄的身影。我为曾经的犹豫感到羞愧,幸亏寄出去了,要不永远对不起孩子,伤了他们的心,拿什么来补。
后来陆续又寄了一些书和文具。秋天来了,我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李庄的。里面是大枣,红亮红亮地透着喜庆,夹着纸条,“姐姐,队长说今年最好的枣不许卖,寄给北京。”我把枣分给捐书的同事,大家说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枣。
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什么叫“一诺千金”,什么叫“言而有信”。
聚会
文/佚名
去年深冬的一个周末,我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我们这些19年前的同学,年轻的痕迹已经渐渐远去,留下的,也许包括静思中的那种忆旧,一旦需要交流,便走到了一起。
那是一个辉煌的自助餐厅。或许是叙情的一种境界就是酒醉,26个同学都挺投入。可是,谁也没有忘记找对方要过通讯录,把电话号码留下。
这一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直没有怎么声张的夏文。记得上学的时候,她就不善言谈,属于容易被人忽略的女生。在这次同学聚会上,面对别人太多的成就,她始终保持着一种谦恭的沉默。午夜时分,同学们迈着酒步,满嘴承诺,感慨,相拥,惜别,那场面感人至极,甚至有些悲壮。然后,纷纷上了出租车。
这段大街很快沉寂下来。只有夏文没有走,她正在昏暗的马路边寻找什么。原来她丢了自行车钥匙。我忽然发现26个同学中只有她是骑着自行车来的。
我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要打车送她回家,但被她婉拒了。夏文提醒我不要忘记刚才的承诺,明天早上到我家去擦抽油烟机。
我真正认识夏文,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第二天上午9点我才醒来,显然已过了同夏文约定的时间,我连忙打开屋门。夏文在楼道好像已经站了许久,隆冬时节,她只穿了一件皮革绽裂的夹克。那上面油污遍布,酷似一幅退色的地图。她的左手拎着帆布兜,右手提着铁桶……
我赶快抱歉,让你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夏文笑笑说,你言重了,你现在不要考虑咱们是同学关系。我是个体家政服务员。好吧,请你烧一壶水。
那次同学聚会,大多话题就是抚今追昔。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交流,我虽然预计多数人可能比我过得好,其实,还是没有预料到,两张条形餐桌上,居然有16位科长、处长还有经理。我这个写字的人,属于“独有”的人物,自然难以入流。那天,收获最多的就是夏文了。她显然是有备而来,准备了一本便条,把邻居(公用电话)的号码写在上面,然后说请大家帮帮忙,我早已经下岗了,请同学们给联系点儿活……
我忽然发觉,她有一点哽咽,眼里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晶莹。是面对这么多有成就的人“汗颜”,还是一种别样情怀?
夏文毕业以后顶替母亲进了构件厂。平平淡淡的15年间,她一直是默默地工作。这期间,恋爱、结婚、生子。丈夫比她大两岁,也是不善言谈,甚至有些木讷。他是街办工厂的搬运工,每月工资470元,最高职务是车间的小组长;儿子是4年级的学生,虽然努力,但成绩一般。
这是一个平平淡淡,无奇无异,没有太多向往的家庭,演绎着我们所惯见的生活模式。
夏文先在屋中央铺好塑料布,然后蹬着凳子去拆机器。厨房极小,是那种摆上用品,就难以转身的空间。夏文的头已经顶到挂满油泥的墙上,根本无法直起身子。15分钟后,夏文抱着机器下来了,她已是满头大汗。
我和夏文的聊天,是在她为我擦油烟机时开始的。我经常能在道桥边上,看见等活干的民工,我一直以为,是他们垄断了这项工作。
夏文平静地说,丈夫是自己的师傅。
两年前,夏文丈夫所在的街办工厂由于产品销路受阻,他被圈入了阶段性下岗的名单。那夜,夫妻俩默默对视到天明。虽然抑制着眼泪,但夏文知道,两个人都下岗了,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早上,夏文的脸上挂着笑容,一家人吃过早饭,夏文和丈夫一起去卖货。
他们卖的是手套,这是丈夫所在的难以为继的工厂“以物抵工资”给的。一星期后,180副手套只卖出了21副。有一天狂风大作,货架上的手套被卷起来。夏文无助地望着随风刮走的手套,强忍着泪水在街上追逐……
下雨的日子不能出去了。为了省些钱,丈夫把风扇已不能转动的抽油烟机拆下擦洗。整整10个小时,丈夫终于装好了机器。
夏文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擦抽油烟机——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农村来的民工那样也去干呢?
从此以后,丈夫成了她的师傅。这台机器,拆了装,装了拆,床上铺上报纸,就成了演练场。每个螺丝,每个夹板,已经深嵌到夏文的记忆中了。
就这样,夏文两个月后“出师”了。她学着别人的样子,把工具兜子、水桶绑到自行车上。她的这种装束,在熙攘的大街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景。
起初站了一个月的马路,夏文只做成了7次活。最早出去的一次,凌晨5点半离开家,赶到住户家已是8点整;最晚回家的一次,《晚间新闻》主持人已说再见。尽管如此,每次按照约定的时间上门服务,她的心里就会涌动着一种希冀,每蹬上住户的一级楼梯,就会有“成功的一次”的激动。
她告诉我,这种“精神胜利法”其实挺重要,否则,哪里去寻找自信?
她手中的小铲上下舞动,机器内壁的油泥蜷曲着翻滚下来。接着,她取出一把挺特别的布球,擦洗顽渍。我问她这布球的来历,才知道这又是一个夏文式的“典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夏文从业的初始阶段,用50元钱购置了一套组合工具。可是,消耗最多的是一次性清洗棉球。起初,她把家中所有的旧布都用上了,却还是供不应求。有一次她望着一家美容厅晾晒的毛巾发呆。毛巾非常多,甚至算是壮观。夏文去找经理。经理迷惑地问,你想买旧毛巾?夏文说,我想要这种东西,可是我没有钱,但可以给你们干活。
经理显然没有这种“业务洽谈”的经历。他愣了半天,才弄明白这个特殊打工者的用意。他欣然答应:夏文每月给理发厅做一次大扫除,报酬是替换下来的所有毛巾。
就这样,夏文用她的艰辛启动了同样艰辛的擦抽油烟机的劳作。
4个小时后,夏文终于装好了机器。由于长时间蹲着干活,她站起来的时候居然有些蹒跚。这个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中药气味。夏文淡淡地解释说,这些日子经常腰痛,就穿上了带中药袋的棉裤。她的脸上还淌着汗水,油污和汗水的混合就像是一副戏剧脸谱……想起昨晚风光无限的同学们,我突然有了一种辛酸。
我惟一能做的,或许就是多付给她酬金。然而,尽管我当时的态度异常坚定,可还是没能说服她多收下一分钱。
夏文平静地说,你应该给我20元钱,这是我今天劳动所得……我应该感谢你,感谢你给了我这个倾诉的机会。不过,我觉得我是幸福的,我的家庭也是幸福的。我已经学会了在清苦的日子中寻找幸福。我想,这也许就叫做勇气……
我再一次发觉她的眼里闪烁着感动。
即使一个弱小的人,也会有足够的力量感动你。
父亲的跪
文/佚名
我永远忘不了自己在中学时所发生的荒唐的一件事。
自从我步入这所重点高中的大门,我就不是个好学生。我来自农村,我以此为耻辱。我整天和班里几个城市的小流氓混在一起,一起旷课,一起打桌球,一起喝酒,一起看录像,一起追女孩子……
我忘记了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多交了几千块钱的自费生:忘记这是父母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血汗;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忘记了父亲的期盼。只知道在浑浑噩噩中度过。
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个夜晚夜色很黑。我趁着别人在上晚自习,又和他们再一次逃出了校门,窜进了街上的录像厅内。后来,我们又商量去偷自行车,结果被学校政教处的老师从派出所求情带了回来。
第二天,在政教处蹲了一上午的我被通知回家喊家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平素对学生要求甚严的重点高中让学生回家意味着什么。我哪敢回家,哪敢面对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双亲!
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我想起来有一位喊表嫂的远方亲戚,我到了她家,战战兢兢地向她说明了一切。请她去给说情,求学校不要开除我。并哭着请她不要让我父亲知道这件事。但也没有什么作用。
次日上午,我失魂落魄地躺在宿舍里。我已经被吓傻了,学校要开除我的消息让我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被开除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样跟父亲说,我还怎样有脸回到家中……”这时,门“吱”一声响,我木然地抬头望去,啊,父亲,是父亲站在我面前!他依旧穿着我穿旧的那件破旧的灰茄克,脚上一双解放鞋上沾满了黄泥——他一定跑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看了出来,那目光中包含了多少失望、多少辛酸、多少无奈、多少气愤,还有太多太多的无助……
父亲坐在楼下的一块石板上喘着气。这飞来的横祸已将他击垮,他彻底绝望了。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儿子身上,渴望儿子能成龙成凤,然而,儿子却连一条虫都不是……想起父亲一天滴水未进,我买了两块钱的烙馍递给父亲。父亲看了看,撕下大半给我。自己艰难地咽下那一小块——脸上的青筋一条条绽出。那一刻,我哭了,无声地哭了,眼泪流过我的腮边,流过我的胸膛,流过我的心头。
晚上,父亲和我挤在宿舍的床上。窗外哗啦啦一片雨声。半夜,一阵十分压抑的哭声把我惊醒,我坐起来,看见父亲把头埋进被子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天哪,那压抑的哭声在凄厉的夜雨声中如此绝望,如此凄凉……我的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早晨,父亲的眼睛通红。一夜之间,他苍老了许多。像作出重大决定似的,他对我说:“儿啊,一会儿去李校长那里,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上学,就在这一次啦。”说着,爹的声音哽咽了,我的眼里,也有一层雾慢慢升起来。
当我和父亲到李校长家里时,他很不耐烦:“哎哎哎,你家的好学生学校管不了了,你带回家吧,学校不要这种学生!”父亲脸上带着谦卑的笑容,说他如何受苦、受难供养这个学生,说他在外如何多苦多累,说他从小所经受的磨难……校长也慢慢动了感情,指着我:“你看看,先不说你对不对得起学校,对不对得起老师,你连你父亲都对不起呀!”
就在我羞愧地低着头时,突然父亲扬起巴掌,对我脸上就是一记耳光。这耳光来得太突然,我被打蒙了。我捂着脸看着父亲,父亲又一脚踹在我的腿上:“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给我跪下!”我没有跪,而是倔强而愤怒地望着父亲。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我那50多岁的父亲,向30多岁的李校长缓缓地跪了下来……我亲爱的父亲呀,当年你被打成黑五类分子,你对我说你没有跪;你曾一路讨饭到河北,你也没有跪;你因为儿子上学而借债被债主打得头破血流,你仍然没有跪!而今天,我不屈的父亲呀,你为了儿子的学业,为了儿子的前途,你跪了下来!
我“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父亲搂着我,我们父子俩哭声连在了一起……
两年后,我考入了西南政法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跪在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那一天,我没有想到父亲为了我竟然放弃了他的尊严。
生命的美丽约定
文/佚名
晌午,安娜坐在医院外面的草坪上晒着太阳,虽然身旁有着一簇一簇鲜艳的小花,但她的脸上却始终是一副忧郁的表情,因为她被诊断患有绝症,而且时日不多了。母亲总是含着眼泪站在她身旁,为她梳着头发。她的头发一天天变少了,像秋风中摇曳的枯草。
在回病房的路上,一个男孩走了过来,在他们四目接触的一刹那,一种特有的神采闪在安娜的眼前。男孩拿起手中的风筝塞到安娜手里说,“你瞧这是一只小鹰,它是我的朋友,它很勇敢!我叫约克,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快乐!”就这样他们聊了起来,原来约克也患有绝症,每天他在医院的草坪上经过时都会看见安娜在静静地发呆,脸上写满忧伤,约克觉得这么美丽的女孩应该有最灿烂的笑容,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的日子也不多了。今天,他看见安娜坐在草坪的花丛里,觉得应该让她像艳丽的花朵般笑起来,于是他鼓足了勇气和安娜讲话!这天傍晚,他俩已成了仿佛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两颗已经濒临绝望的心相撞了,闪出了希望的火花。他俩在一起聊天,一起放风筝,这对少年仿佛拥有了整个天空。
终于有一天,他们都得知病情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他们相拥而泣,但还是互相鼓励着,他们约定:好好地过完每一天,为对方祝福,永不言弃!但他们一直都会通信给彼此鼓励。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一个下午,安娜手中握着约克的来信,抱着那只小鹰风筝,合上了眼睛,嘴角边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母亲流着泪默默地拿过约克的信,一行行有力的字跃入了眼帘:“……当命运捉弄你的时候,不要彷徨,不要害怕。因为还有我,还有很多爱你的人在你身边,你绝不孤单。”母亲拿信的手颤抖了,泪水一点点润湿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