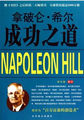然而,蒋介石调转头来,就扑向南昌,敲响了第四次“围剿”的锣鼓。他在到达南昌的第二天,就发表演说,声言:“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攘外必须安内。”
第四次“围剿”和前三次同样的败局收场。这一次,蒋介石停止了进军,命令所有部队在阵地和交通线上构筑工事,他的德国顾问们正在制订新的“围剿”计划。中央苏区得到一段喘息时间,一直持续到1933年秋。
国民党中央政府军停步不前,不仅限于军事上的原因,还有种种政治上的背景。日本军国主义者撕毁了1932年与蒋介石签订的停战协定,继续侵略中国。1933年年初,日军从满洲经过上海向华东、经过热河向察哈尔进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他正忙于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他又一次指天发誓,这次“围剿”会最终战胜共产党人。他暗喜的是:如果华北各省过于独立的地方将领和行政长官不得不单独抵抗日本人,并因此而遭削弱,不也是一步好棋么?
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群众抗日运动的烈火在全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华中熊熊燃烧起来。一些国民党将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同情人民的抗日情绪。比如张学良,在日本关东军占领整个东北之后,他和东北军一起被蒋介石撤到西北的陕西;在抗日浪潮推动下,张学良亲赴南京请战。蔡廷锴在上海市郊闸北进行了英勇保卫战之后,蒋介石把他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南方的福建,与共产党人作战;虽然蒋对十九路军进行了清洗,但是抗日的情绪,包括对蒋介石的愤怒,在军队中和指挥机关中仍旧有增无减,他们枕戈待命,对继续进攻中央苏区,修筑旨在形成福建封锁圈的工事也不特别热心了。还有冯玉祥,他的势力范围内蒙古直接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领导看出其中的有力转机,想以此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日。即使不能形成这种局面,起码蒋介石为了驯服这些难以驾驭的将领,也不得不暂时延搁他的进攻意图,减少集中对付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据说宣言是洛甫(张闻天)起草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宣言上签了字。尽管由于当时的党中央还没有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而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仍然坚持其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但还是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宣言起到了它的作用。在国民党的范围内,甚至在南京,表示拥护联合一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进行抗日的呼声很高。冯玉祥和蔡廷锴发表了相应的声明。据电台报道,广东和广西两省省主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图,尽管他们看起来似乎还在幕后抱着观望态度……
这年秋天,像预示冬天就要来临似的,风早早地变得尖利起来,落叶铺天盖地地染黄了山峦。更为气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同时,来自内部的“左”倾的压力,使人有一种缺氧而窒息的感觉。
中央苏区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王稼祥,没有想到,在此时此刻,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外宾”:他叫奥托·布劳恩,是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人,据说当过苏联一个骑兵师的参谋长,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原曾利用他的德国人身份,在苏联远东和我国东北搞日军的情报,后来又到了上海,成为共产国际驻华高级军事代表弗雷德的助手,并被他派来中央苏区,先化装为奥地利籍牧师从上海到潮汕地区,再由专人护送到瑞金,一路上也冒了不少风险。红军师政委伍修权被中央指定为他的翻译、秘书还兼参谋。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摘掉帽子,露出他那一头“怒发冲冠”的直发,介绍着:“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家一律用中文称呼‘李德’,不得泄露他的顾问身份和原名。”
李德30多岁,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薄薄的嘴唇严肃地紧闭着,显出一种矜持、自信以至固执。
周恩来同他握手,用英语说了句:“非常欢迎你,李德同志!”
李德向毛泽东伸出手,毛泽东把右手的烟卷换到左手,起身应酬着:“幸会,幸会!”
王稼祥熟悉英、俄两种语言,忙用俄语介绍了自己,并说:“我将尽自己的职责,给予您必要的配合和合作。”
李德快活起来:“我早已听说你,相信你会像博古同志一样支持我。”
从这天起,中共党内发生了令后世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不很懂军事、更不懂苏区实情的外国人,又没有明确职务,竟指手画脚地凌驾于中央和军委之上,指挥起红军千军万马来。红军专门为他盖了三间新瓦房,由于它坐落在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田野之中,人们都叫它“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最近的“外交部长”的房子还有二百米远。独立房子的主人时常在其中一闷一整天,在左右的军事地图上指指点点,以收“运筹于帷幄取胜于千里”之功。王稼祥怕洋大人过于劳累,曾派人去慰劳一下,去的人回来说屋里正在秉烛夜战,大打扑克哩。王稼祥只得粗声叹气。
李德并不总在玩。他更多的还是与博古纸上谈兵,谈到极兴处,博古都忘了中国话,笑声都带着俄语腔。他们谈着,既丧失了与冯玉祥联合抗日的机会,又错过了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的良机,还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按博古的说法:“老毛又犯了外交病!”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李德“大臣”才偃旗息鼓。
长征还在艰难地继续着。毛泽东的担架和王稼祥的担架偶尔相遇。
毛泽东:“日本有什么新消息吗?”
王稼祥:“根据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截获的情报,日本正继续加紧入侵华北,由内蒙古向西推进。在中国,特别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越来越广泛的阶层卷入了抗日群众运动,不仅有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群众运动甚至在国民党军队中,包括军队高级指挥官中也有很大开展。”
“对日本占领内蒙的企图,应该表明我们的态度。以前我们喊‘帮助苏联’,看来现在更要喊‘帮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