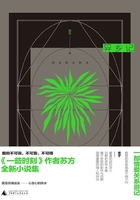田耳(1976年~),原名田永,湖南凤凰人。主要作品有:《围猎》、《重叠影像》、《氮肥厂》、《铁西瓜》、《夏天糖》、《人记》、《一个人张灯结彩》、《你痒吗》等。
现在,但凡小丁回忆起住在氮肥厂的日子,首先脑袋里会蹭出那个姓苏的守门人,以及他在空旷、灰暗并且嘈杂的厂区内来回走动的样子。大家说老苏是个倒霉鬼,但老苏脸上一天到夜都挂着笑,比别的所有职工的笑脸堆起来还要多,还要欣欣向荣。倒霉的老苏以前在县政府当守门人,难得有笑的时候,一到氮肥厂,他就开心起来,仿佛这氮肥厂是他一个人的天堂。
老苏的左腿虽然比右腿短了十几公分,但能够凑合着用;右腿看上去显得完整,其实是条累赘。于是,他走路的姿势就成了这样:左腿永远摆在前头,右腿作为一个支撑点,只在左腿腾空时勉为其难地撑几秒钟;左腿往前挪了几公分远,我们的老苏身体借势往前倾,就把右腿顺带着拖动几公分。其实还可以讲得形象一些:就好比男人单膝跪地向女人求婚,女人却掉头走了,男人则保持着这一跪姿向前追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当老苏行经眼前,小丁好几次听见岳父老陈说,我看着眼睛都蛮累。小丁揣摩到,老陈往下还有一句没说出来的话:他老苏何事能活得这么快乐,这般滋润?
这也是氮肥厂几十号职工共同的疑问。1977年的氮肥厂厂区,触目是一片暗灰的颜色,围墙、厂房、烟囱、蓄水池……造气车间开工时,蓄水池里那圆柱状的气柜就会上下夯动,收集气体并将气体泵入压缩车间。建厂那年,圆柱体的气柜分明是涂着赭石色,这才两三年时间,就灰得和蓄水池池壁毫无差别,在氮肥厂,这种死灰仿佛可以传染、渗透、蔓延……小丁记得,住在氮肥厂的日子里,顶头上那片天穹大多数时候也成了这种颜色。但天色毕竟灰得轻淡一些,犹如氮肥厂倒扣在一方水面上的镜像。
在这种环境中,老苏脸上的笑容就尤其显得突兀了。他独特的走姿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突兀之感。职工们歇气的时候会走到厂坪里,抽一支没装过滤嘴的纸烟,看看老苏一脸喜色,不晓得应不应该羡慕这个人。老苏时不时会哼哼曲调,用心去听能听出来,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丁有次就说,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呐,毛主席写头稿时有一条“大便下茅坑”,这老苏可从来没把大便对准了茅坑里拉。
小丁这么说,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老苏大便的时候,屁股免不了是要往左边撇的。小丁这么说,是因为他看不惯老苏怎么一天到晚笑呵呵地。1977年的时候,在氮肥厂,似乎谁都没有理由成天到晚地傻乐。
老陈刚调到氮肥厂当厂长不久,通过调研认识到,氮肥厂作为临时政策的产物,投产以来一直都在亏损。—用不着什么调研也能晓得这厂在亏损,其生产成本高于生资公司的牌价。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就犹如老苏两腿都瘸一样,是明摆着的事实。
老陈把小女儿和女婿小丁安插进氮肥厂以后,就着手写文章打报告,摆事实讲道理,请求上级部门酌情关闭氮肥厂,并转产上其他的项目。
如果老陈不是那么急于搞垮氮肥厂,就不会把老苏这个废人弄到厂里来。
老苏原本不是个废人,自从他落成现在这个样,谋生就全搭帮向副县长照应了。
向副县长从前娶了老苏的姐姐,作为姐夫,他有义务给老苏弄碗饭吃。老苏被安排在县政府大院看门。看门就只能看门,扫地的人还得另请。他有一只胳膊也残了,像煮熟的挂面一样成天耷拉在肩膀上,只有一只手能用—其实他看门也看不好,他以半跪的姿势走过去,要拖沓几分钟才能移到门边,用仅有的一只手拉开一扇门,然后再移动着拉开另一扇门。幸好那时车不多,只有上面领导检查工作时才会坐吉普车来到政府大院。佴城的几位正副县长出入大院,一色的二八锰钢单车。
有几次,上面的领导来到门边,左等右等等不及了,烦躁了,就跳下车来帮着老苏打开那两扇门。
老苏很内疚。虽然这样的事,正好凑合领导的随从们写了一篇亲民啊随和啊关爱残疾人啊之类的文章发在地市党报上,老苏心底还是很内疚。他是个蛮有上进心的人,遇到困难,就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排除困难。他脑袋挺灵便。那两天,他始终在纸上画来画去,鬼画桃符,别的人看不出个所以。两天后,他买了几股麻绳、几只定滑轮和一个绞绳的轴把子,用时两个多小时,就把县政府两扇沉重的木门改造成了自动门。摇那轴把子的时候,人感觉不是很费劲,老苏可以一边抽着烟一边把门摇开。当他要关门的时候,就反向摇动那轴把子。
门一旦弄好,各个机关的守门人都跑来睨几眼。不看不晓得,一看都恍然明白过来,妈妈的,原来是这样啊。他们回去折腾一番,把门都折腾得自动起来。
但向副县长一直盘算着要把老苏调走。老陈拿着一沓关于请求关闭氮肥厂的报告去找向副县长时,向副县长就把这层意思讲给老陈。办公室里当然不便说,向副县长拉着老陈去招待所吃饭,碰了两杯,向副县长就说想拿老苏和氮肥厂的门卫对调一下。
……其实,老苏是个蛮好用的人,脑袋里拽得出一把一把鬼主意,人又蛮听话,像给你当崽当孙一样听话。向副县长一派推销员的口气,然后又说,他的情况你晓得,摆开了说,虽然我一个党员不好讲鬼信神,但我这妻弟确实有点霉,有点衰。老陈你晓得的,早几年一帮副县长里头,仿佛我是势头最好的,眼看着……日他妈,自从把老苏带到身边以后……我晓得我晓得。老陈看着向副县长有些伤心了,赶紧举杯过去和他再碰两碰,然后知冷知暖地说,我都晓得。
向副县长追着老陈问,帮不帮我这个忙?要是我能扶正,我肯定投桃报李,帮你关掉那个衰厂。他敲了敲桌子上老陈写的那沓报告。
换就换好了,卵大个事。老陈这往自己口里抹一杯酒,有些解嘲地说,老向你是要运气,我啊,倒正需要点衰气咧。就不晓得老苏这个人到底有多衰。
向副县长说,各取所需,各取所需,呵呵哈哈。两人干掉了剩下的酒。
就这样,老苏从县政府来到氮肥厂。
到氮肥厂没两个月,老苏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快活的人。当氮肥厂的职工们头一次看见老苏一张苦瓜脸挤出笑来的时候,都觉得很稀罕,就像看见了昙花一样。老苏的笑容是很打动人的,试想,老苏这样的人都能对他惨淡的人生报以一笑,那别的人,再垂头丧气的话是不是奢侈了些呢?氮肥厂的职工都从老苏的笑容里得来些感悟。那年头,人们还是蛮愿意在生活里有所感、有所悟的,先进人物报告会时常有得开。但从老苏那里,得来的感悟还更多一些。
再过去几个月,大家看见老苏每天都没完没了地面带微笑,感觉又不一样了。他们想,老苏凭什么笑得这样起劲?老苏的笑,把整个氮肥厂的氛围都改变了。这似乎不太正常。运动时期虽然结束了,人们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觉察到不正常的气味,就免不了去追本溯源。
小丁有时候也会琢磨着老苏的笑容。他对老苏的笑容没有太大热情,也不是漠不关心。有时闲着无聊,比如说骑单车行在一条空旷路上的时候,他偶尔地想,老苏何事这样开心呢,而我何事总也快活不起来?
有时候阳光照在眼前黑油油的沥青路面上,路面泛着幽微的光,映在小丁的眼底。小丁时快时慢地踩着单车,把老苏的笑容回忆得多了,就会得来一阵烦躁。他在心里嘀咕说,先人哎,我四肢健全,老婆蛮漂亮,算得上氮肥厂的厂花,孩子长得跟洋娃娃似的蓬松白净,何事还快活不起来?
有一天一个朋友骑在另一辆单车上从后面追来,和小丁打招呼。他们以前是同学。他的同学问,小丁想什么呢,骑车还走神。小丁一想那同学是在政府工作,就问,老苏你记得不?就是以前在你们政府守门的那个。同学就说,当然认得。怎么啦?小丁说,这个人真是心态奇好,都那个样了,每天有说有笑,开心得不得了。那同学也奇怪了,他说,你说老苏现在有说有笑是吧?他以前在我们那里,可从不这样。我都不晓得他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小丁说,那就更奇怪了。他一转到我们氮肥厂,就像是跨进了共产主义一样,有享不尽的福一样。
那真是怪事。那同学说,改天我去你那里串串,看看老苏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
他说些什么呢?
小丁说,他什么都说,你问他怎么弄瘸的,怎么成了个残废,他也脸上挂笑,一五一十地摆给你听。他讲得蛮生动,像英模作报告一样。
那同学翻翻白眼,说,是吗?以前他可是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呀。你说说,他怎么搞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老苏确实是面带微笑地告诉每一个前来关心他的人,他怎么搞成了现在这样。
早几年他还是个完全健全的人,身体板实,做起活来样样拿手。73年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女朋友。那女的是城郊筌湾村的人……筌湾村?是不是现在被叫做寡妇村了?老苏刚说起这个名字,别的职工就大概明白了,会是怎么一件事情。前几年发生在筌湾村的事,还是尽人皆知的。没想到老苏也掺和进去了。
……对,就是那年秋后的事。老苏舔了舔嘴皮,抽起别人递上来的烟,还用嘴唇把烟杆子濡湿一些。
那年秋后,老苏去找他的未婚妻,正碰上筌湾村的男人们庆丰收,一齐去河湾里炸鱼,闹一闹气氛。
筌湾是个特别小的村落,十几户人家,男人加起来二十几个。那天,几乎所有的成年男人都去了河湾。他们从乡供销社拉关系搞得两坛炸药,拿去炸鱼。第一坛炸药被点燃导火索后放进河湾,等得一刻钟,没有响动。于是他们把第二坛炸药扔进河湾。很快,这一坛炸药在水底下开花了,水汩汩地翻涌上来,很多鱼漂在了河面上。筌湾村的男人们乐开了花,他们一个个脱得精赤,像一条条大白鱼一样钻进水里,捞起炸死或炸昏的鱼,用柳条穿着。
当他们全都潜进水里的时候,刚才哑巴了的那坛炸药,这时突然也开了花。
老苏喷着特别地道的烟圈,说,那天我去晚了些,刚走到她屋里,她就把我推出来,要我去河湾捡鱼。她说她家里就她一个老爹,水性又不蛮好,捡起鱼来肯定要吃亏的。我到地方的时候,别人已经捡了不少。我脱光衣服,刚一入水,那坛炸药就炸了。算好,我还没潜进水底。要是早入水十秒钟,我肯定也死在那里了。
别的职工就说,啧啧,不幸中的大幸,老苏,你还是一个蛮有运气的人。
老苏苦着脸说,这还叫有运气?我入水的地方正好是爆炸的正上方,一股水柱把我掀起来老高,可能有丈把高,搞得我整个人像是飞起来一样,腾云驾雾……那蛮爽的嘛。有人说,老苏那么大的一堆,竟然能够飞起来。啊哈,老苏两只脚一长一短地飞了起来。
老苏辩解地说,不是的。那时候,我的两条腿还一样地长。掉下去以后就昏死了,醒来的时候,人躺在医院里头,手脚都不能动弹了。喏,出院就成了现在这样。
别的职工拍拍老苏的肩头,安慰地说,老苏呵,往好处想,能捡得一条命在,就不错了。
我晓得我晓得。老苏说,我这人,经过这事情特别想得开。李小莲一脚把我蹬了,我眼都不眨一下。老苏吧唧了一大口烟,那烟没有滤嘴,一下子燃到了手指捏着的地方。老苏把手指拿开,还争分夺秒地吸进去两口烟。
别的职工说,老苏你是个角色。我们是不是叫厂长老陈开个英模报告会,抓老苏上去把这些事摆一摆?老苏可是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呵。
老苏就憨厚地说,哪里哪里,别灌我米汤了,我这人呐蛮有自知之明,哪敢跟那个保尔比呢?我比他一根卵毛都比不上。
小丁记得那一年老是停电。前几年停电不是这样频繁,73年氮肥厂建成以后,停电才变成了隔三差五的事。佴城的人都把停电怪罪到氮肥厂头上,说是氮肥厂设备启动时耗电量太大,常常把变压器烧坏。有一次,刚一停电,一帮子人汹涌着往小丁家走来,说是要抓老陈去坐班房。他们有个家属正在做手术,突然停电,导致了病人死亡。
老陈走出来拦在门口,说,你们放屁,医院是一号线的电,跟氮肥厂没关系。
这样,老陈就挨了一顿饱揍,那些人不由分说冲上前来揍了老陈。公安局来了以后,老陈也指认不出是谁。他说,同志,不是一个,是他们一堆。
结果那一堆人都被放走了。
老陈很窝火,他更加坚定了决心要让氮肥厂关张。氮肥厂是当年的政策产物,全凭某个领导一句话。那领导在某个会上学着毛主席的范,大手一挥,跟台底下的人说,每个县都得有小氮肥!这句话一直刷在氮肥厂厂房的一面墙上,用鲜红的油漆写上去,还用黄油漆勾边。但佴城是个缺煤少电的县份,根本不适合搞氮肥。
老陈甚至把转产项目都找好了,他觉得把氮肥厂关闭了以后,可以在原址上办一家烟厂。佴城特产的白肋烟在全国都有名,这就是优势。要搞氮肥,佴城就只有一把把的劣势可言。
但上面管工业的副县长很不同意。这个副县长认为,要是搞氮肥,大家不会偷这东西放屋里去。要是搞卷烟,氮肥厂这帮子烟鬼一边搞生产一边抽不要钱的纸烟,一天抽到晚,那还得了?
氮肥厂的职工几乎都同意老陈的意见,倒并非想抽不要钱的纸烟。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老陈的意见是符合现实情况的,也肯定能扭亏为盈。反对老陈的人,可能只有老苏一个。但他不会表露出来。
老苏知道,如果氮肥厂关闭,烟厂办起来的话,他肯定得卷铺盖走人。老陈把他弄来的用意,他已经听别人说了,是要借他身上的一股衰气尽早地搞垮氮肥厂。一旦烟厂建起来,老陈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比如说,加强保卫工作严防偷盗啊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他踢出去。
老苏现在很留恋氮肥厂,他甚至想如果能老死在这个地方,也蛮不错。
别的职工从老苏脸上永恒的笑容里,逐渐看出些名堂。因为氮肥厂里,近期还有一个人也容光焕发了起来。人们免不了把另一个容光焕发的人和老苏联系了起来,顺着思路理一理,把两人摆在一起作些比对,仿佛就有一些端倪显露了出来。
另一个人是个女人。当然,要是也是个男人,那和老苏摆在一起就没什么戏了。
必须是个女人,她就恰好是个女人。小丁记得那女人滚圆滚圆,像是墙上挂画里的苏联女康拜因手那样壮硕。那年以后,氮肥厂的人们给女人取了个名字,就叫“容光焕发”。这听上去实在不像一个人的绰号。但要知道,当时老苏已经获得了一个绰号叫“防风涂的蜡”。这听上去也不像绰号,两个不像绰号的绰号摆在一起,就全明白了。
容光焕发的脸确实很红,像是永远处在经期一样。老苏的那张脸也是整个氮肥厂里最最黄的,蜡黄蜡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