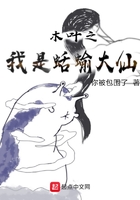她为什么要主动向这个男人献艺?献艺完了又将会是什么呢?枝子不愿意想,不情愿这样残酷地拷问自己。她愿意在心里给自己的自尊留有一点余地。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枝子在心里说。枝子只希望能是她所想要达到的那个。此时她真是觉着自己对这个男人有些过分俯就,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因为照她素常里的做人态度,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而她的鼻孔总是抬得很高,并且,暗中加着千倍的小心,很怕落入某些勾引利用的圈套。如今却这样巴巴地主动送上门来,可真是有些不好对自己的心解释了呢!
管它呢。随它去吧!反正来也是来了,还费力解释它干什么?
拖着长头发的高个男人松泽扎煞着两只手,在枝子身边围前围后转了两转,明白自己也实在帮不上什么。看来枝子对于今天的下厨是有过精心准备的,知道他这个单身汉的厨房里可能会七七八八的不全,所有的素菜、荤菜备料都由她亲自从外面带来。连烧菜用的油和醋等作料,也全被她准备到了。甚至枝子还带来了围裙,柔软的白细棉布套头裙,腰间勒一根细带子,自上而下撒下一捧捧勿忘我的小碎花。
绵软的白裙贴在她身上,正好勾勒出枝子腰条的纤细。枝子的头发本来可以戴上与围裙配套的棉布帽,以免熏进油烟味儿。但她想了想,还是将帽子舍弃,将头发挽了几挽,然后向上用一枚鱼形的发卡松松一别,这样,她乌黑发亮的秀发就尽显在男人松泽的视野。
松泽盯着这个体态窈窕的女人,心里怦怦怦乱动了几动。当然,他是艺术家。艺术家面对美没有不动心的。他和她一直都算得上是很亲密的朋友,亲密的最初原因是枝子出资帮他举办个人画展的成功。从合作的愉快到亲密友好的交往,两人的关系大致上就是走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再友好,他也不敢说是劳动她的大驾来给自己庆贺什么生日,尤其是没想到她还要亲自下厨。这该是出乎意外且又让他承受不起的情分。
能有一个漂亮女人主动来家里给自己过生日,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美事情。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艺术家,总是爱好推陈出新。就在枝子下厨期间,就有三四个女孩子的电话打来,邀他出去派对。他不得不柔声细语轻声回绝。与待在家里传统的吃生日饭相比,当然卡拉OK包间或派对沙龙里搂搂抱抱的扭捏抚摸更能激发创造力。但若从长远的角度看,比起跟那些小女崇拜者玩玩白相,跟女老板的关系处理好对他将来的用途更大一些。男人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从最实利的目的想。所以他决定还是死心塌地,留在家里与女老板亲近感情。
这样心里边一踏实下来,男人也就专注移情于厨房中的枝子身上,渐渐从忙而不乱的枝子身姿当中体味到另一种情致。枝子的动作,熟练而静美,如一朵栀子花儿开放在氤氲的厨房香气中。植物烹炒的香气中夹杂的成熟女人的体香,熏得男人松泽有些想入非非。在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嘴的情况下,他便懒散地一条腿以另一条腿为重心,倚在厨房门框上,一边静待时机,一边向忙碌的枝子身上乱抛多情的眼神。
枝子意识到了男人的注视,略微有些慌乱,不等春风吹绽,便先兀自欢颜,面若桃花的有些气短。她一面竖起耳根,悉心倾听男人粗长的呼吸,一面竭力命令自己镇定,尽量掩饰住狂乱心跳,将身体动作恢复成正常。她所企望的,不就是这个男人的这样一种目光吗?如今已经等到了,那么她还紧张什么?这么想着,她手里切菜的动作就有了几分表演性质。
厨房不大,容不得两人同时在里面转身,只要一动,就势必会发生身体上某些部位的接触。所以他们就在各自位置站着,口里还要间或说上几句哼哼哈哈应酬话,身体里却不免都暗暗生出几分紧张。主要是男主人还没有拿捏得好女老板的意图。松泽虽说已是风情老手,但在从来都很端庄的枝子面前,毕竟也是不敢造次,不知道她想要他做什么,要他做到什么程度。他还时时没有忘记她是投资人。所以他只是听之任之,一边散漫无际地调着情,一边还要暂时做出温文尔雅。这种孤男寡女同一屋檐独处的情境,终归还是需要有一些半真半假调情意味的。不然,艺术家就显得太不艺术,太寡淡无味了些。
而女人枝子也还没想好该如何开始。她也很希望能有一些情调,并且,最好由这情调本身给她一个循序渐进、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她倒是很希望示爱能由松泽一方主动开始。可一旦他真的主动了,说不定她反而会变得厌恶他,拒斥他。
见他站在原地兀自不动,她不禁有些既希望又失望的心理。她看上他,经营他,是看中他的画风里的野气和灵活。后来单相思瞄上他,也是因为在相处过程里发现他已将这野气和灵活全然融合、发挥殆尽,在各种场合都圆熟,灵动,洒脱,很符合她眼里真正艺术家的气质。她以为四周围到处都是被文明过分文明化了的衰人,他的画里有未曾泯灭的人类远古的粗犷之气,还有与神明相通的灵性。而这一切,正是她内心所深深需要的。
在女老板的得力赞助经营下,松泽果然就大获成功且声名远扬。而她则以画推人,认为理所当然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她便因此而爱上了自己的经营品。
两个身体持久的紧张让他们都有些承受不住。枝子在男人松泽的目光里已经汗流浃背。假如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却还要这样无谓地僵持下去,枝子的细腰简直就要绷断了。她不停地用眼角余光扫射着身旁男人,脸蛋儿烧得厉害,肢体以一种柔和的弧度微微向他倾斜过去,那种身段中分明表示着一丝丝鼓励、期盼和犹豫不决。男人在承受温软的肉体倾斜过来的弯度同时也同样是犹疑不定、优柔寡断。他的身体不易察觉地晃了两晃,终于什么也没有能够做得出来。
就这样又沉默了一会,枝子的手指在水盆里游动时漫不经心地挑起“哗哗”的水声,听起来略微显出了一点烦躁。过分的紧张和犹疑终于把松泽自己调情的兴致破坏了,松泽说了一句:“我去布置餐桌。”借机急忙把自己从厨房打发开。
枝子的身体这才有空隙松弛下来,她抬起胳膊肘悄悄抹了一把头上的细汗。松泽到厅里丁零当啷地去拿碗筷,摆酒,布置餐桌。餐桌就由一个矮脚茶几临时串演。
画家的客厅里一切当然都不正规,几个绣着花儿的软垫子散乱地扔在手工绘绣的波斯地毯上,床铺比正常人的矮去半截,只由一层席梦思垫子铺在地上充当。靠墙的一圈转角水牛皮沙发无比宽大,舒适,倒仿佛画家的一切日常活动都要依靠在沙发里展开似的。
松泽把枝子买来的油蜜蜜的生日蛋糕摆在桌子中央。巧克力奶油在灯下沁出浓浓的甜色,样子极其诱人。松泽盯着蛋糕上的奶油想了几想,终究也没想出个子丑寅卯来。到现在为止他的另一股情绪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调动,行动中仍旧有一些惯常与枝子交往时候的应酬色彩。“另一股情绪”当然就是他每每见到来为他献身的崇拜艺术的女孩子时,那种身体内部的骤然启动,那种非要把一个回合进行到底时的狂乱和野性。说来也怪,他这样野气狂生的时候,竟然没有一次是不得逞的。
可现在他的身体里却分明缺乏这种感觉,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呢?
松泽暗暗为自己的身体担忧。他并不明了,一旦有了身份和功利的意念,一切就都不好玩了,连一点点肉体的冲动都不容易发生。松泽坐下来开启酒瓶,同时也散漫地回眼向厨房里打量了一眼。玻璃厨门内的枝子似乎也已料到自己的身影会牵动男人的目光,于是,弯腰投臂的动作都尽力跟他欣赏的趣味相暗合,不慌不忙,舒缓有致。
光与影当中枝子的柔媚影像,正跟厨房的轮廓形成一个妥帖的默契。那一道剪影仿佛是在说:我跟这个厨房是多么鱼水交融啊!厨房因了我这样一个女人才变得生动起来啊!
而松泽眼睛里却始终是莫衷一是的虚无。
太阳这时已经完全落下去了。晚霞收起她最后一轮艳丽,渐渐沉没于幽暗之中。
夜的幕布开启,一切的人与物转眼之间变得朦胧。灶台上的累累成果现在被移到了餐桌上,香气淋漓,色泽也炫目。紧张和等待了大半晌的松泽这会儿真感到体能被消耗得够呛,确实需要补充营养了。可饥饿之后见到琳琅满目的这么一大桌子,却又有了几分惴惴和惶惶,愈发不知嘴从哪里下比较合适。抬眼再望枝子,枝子这会儿已经面目一新地端坐在他对面,脉脉含情地抬头凝望他。忙完了厨房里活计的枝子没忘了到卫生间里隆重地整修了一下自己。她在眼圈周围细心加过了眼影,这样眼中就愈发布满深情。唇线也用唇笔淡描素抹而过。腮红要不要打上橘红呢?枝子思忖了一下,最后决定放弃。等到进入接吻的实质性阶段时,满腮满脸的厮磨,粉影多了容易弄成一团花脸。
脸部修饰完毕,然后枝子又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套真丝晚装,换下了身上一进门来时穿的果绿色白领丽人套服。套服太呆板、僵硬、笨手笨脚、不太使人容易介入,而丝绸可就相对质感,也简捷轻快得多了。这些都是为今晚的爱情特地准备的。虽然烦琐,但在她满心都是甜蜜憧憬之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费周折。
再从房里出来时,枝子就已经是黑色真丝长裙飘逸,身体上最值得称赞的部位—修长的脖颈和光洁的臂膊全都从领口和袖口裸露出来,它们在灯下泛起象牙色的皮肤光泽。而没有裸露出来的部位正包裹在真丝绸的内部炫耀着它们的初始神秘,诱惑着艺术家修长的手指去一点一点开启。
松泽再怎么上不来情绪,也还是不免为枝子的这一身装扮眼皮跳了几跳。饱览美尔后再将其饱尝,本来就是他作为画家的特长。这时的松泽他赶忙表示惊艳,表情夸张地一手扶杯,一手将握着倒酒的瓶子停在半空,眼含赞许地盯住枝子,仿佛喃喃自语地说:“唔,我的上帝!真漂亮,你真漂亮!”
枝子有些激动,又不好意思流露,只很含蓄地说:“谢谢。”说完便用眼光四下里斜了一下,思忖着自己该落座哪儿。松泽正很舒服地陷落在沙发里,把住了桌子的一方。枝子此刻也很想陷到沙发里去坐,跟松泽并排紧挨着……那样就比较方便多了。枝子脸一红,暗中瞬时一转念:可那样是不是显得自己过分主动了呢?她又把眼光偷偷瞟向松泽。可恨松泽那家伙此时并不给她一个在身边坐下的台阶,他若是能拍拍身边的席位,再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上一句:“此处正虚席以待。”那么她也就顺水推舟地坐下来了。可现在他除了假装惊艳,别的一点表示都不呈现。害得她只好溜溜地错过他的身边,绕到对面去,隔着一张桌子,带着好大的失望装出款款落座。
毕竟,在一切没正式开始之前,她不愿意将身份失得太轻率。
红葡萄酒在高脚杯子里幽幽地泛情。顶灯、壁灯、落地灯都被男主人一盏一盏地熄掉,只留下烛台上几支红红的蜡烛闪烁灼灼。隐藏进棚顶四角的音箱放送出柔柔的软歌。那是一种从鼻腔送出来的哼唱,绵绵无骨地含在一管萨克斯里头。枝子姿态软软地给松泽一小块一小块切了生日蛋糕,将带有粉红色玫瑰花的那块儿送进了他的碟子,而自己只留一枚嫩绿色的奶油叶子。祝福的话语一说就落入了俗套,远没有喝酒更能展示出新意。枝子和松泽两人就频频地碰杯,你一杯,我一杯,你再敬我一杯,我再还你一杯。看架势好像都要成心把自己灌醉。
其实枝子才没想把自己灌醉,她只想借酒壮胆,把自己灌出几分将过程进行到底的勇气来。松泽暂时还没有想到那么多,他一边不辜负枝子的手艺,大快朵颐,一边还要腾出嘴,抽空把枝子的手艺表扬。那些称赞的话语落到枝子的耳垂儿上便款款粘住不下,湿乎乎的受用动听。而枝子手中的筷子却难得一动,一来是厨师从来就吃不下经自己手做出的美味佳肴,二来嘛,枝子的心思也完全不在这上头。枝子的眼睛在酒的滋润下,酒汪汪,直勾勾的,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松泽,定定地瞧着他咀嚼时腮帮肌肉的漂亮滚动,看着他对女人说赞美话的时候口吐莲花,满头的艺术家长发一甩一甩地,还有他四十多岁男人刮得铁青的富含魅力的下巴,枝子真是看得又怜又爱,脸蛋儿烧得要起火,连眼珠儿都嗞啦嗞啦地要冒出火星子来。
这个时候的枝子就有些恨,有些爱,有些无奈,有些牙根儿发痒。她就只好又恨又无奈地猛往自己嗓子眼里灌酒。她不知道松泽对她是怎么感觉的,反正,是直到了这会儿他还没有动作。她想他至少应该是提议跳舞,或者是提议做点别的,发挥出这种场合他惯用的技巧和手段。他还要让我怎么样呢?枝子想。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再也越不过我这个年纪的矜持和自尊。她想自己无法保持长久的期待状态,得不到满足期待是持续不下去的。
枝子就愈发独饮自斟,把自己喝得眼神和身态都酒汪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