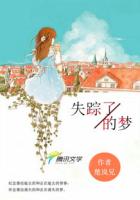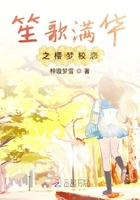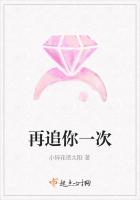学问殿大堂之内,最终选择参加第二关的学子分成了四组,除却白承所在的一组,其他三组皆是各国贵族,无论是当朝三公的两班子弟,还是齐国相后胜这等氏族庶子,唯有白承所在这组最为奇特。
这组可以说是学问殿首个跨越了等级阶级的障碍,而组成的队伍。
魏星祖父乃是战国赫赫四公子,信陵君三代孙,其家门荣光在魏国无人可与之争锋,正八经的王室贵族,魏王旁系。
而项羽虽不是王室子弟,但其祖父项燕,乃是楚国第一名将,一生战七十五,少有败仗,而项氏一族,本身就是楚国项、屈、黄、李四大家族之一,底蕴雄厚,正八经科班出身的三班子弟。
那公孙子龙更不用说了,穿着皆出自纺织名家之手,仪表堂堂,乃是名家当代大家公孙胜之孙,而公孙名家,久居赵国邯郸,正是氏族子弟。
只有白承出身洛阳乡村,庶民阶级。
这样一支队伍,却是汇聚王室子弟,三班子弟,世家子弟以及庶民子弟四个阶级,他们可以放下世族界限,联合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让颜路心中惊讶万分。
儒家虽然倡导有教无类,但在这个乱世,勋贵永远在心底里看不起庶民,这两股势力自古以来就泾渭分明。可是这四个少年,却是打破了这种世族界限,团结在了一起对抗敌人。
这不正是儒家一向倡导的大同理念吗?若得天下兼相爱,甘为源头士与民。
此时子贤等一众考核的儒家二代子弟已经到位,子路在争鸣钟上重重一击,顿时铜钟大吕般的翁鸣之音,震荡在大殿之中。
只听子贤高声喝道:“学问殿第二试争鸣之战,开始——!”
“第一局白承队守,太子秧队攻。”
白承四人闻言,正襟危坐在蒲团之上,在他们对面同样坐着四位少年。
第一人赵良,乃是赵国上大夫赵松之子,才学名动邯郸,小有声望。
第二人严松,乃是齐国三班子弟。
第三人屈平,正是楚国四大世族之中,王族屈氏子弟,项羽说此人好诡辩,颇有公孙名家“白马非马”之说的鬼才。
于是三人齐齐看向了腼腆的公孙子龙,任何诡辩之手,在真正的诡辩佐才公孙名家面前,都要自惭形秽。
第四人也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叫太子秧,却是卫国储君。
别看卫国现下只是一个在战国七雄夹缝之中勉强生存的小国,但太子秧却是卫国励精图治的少年天才,对诸子百家都有涉猎。
于是白承队的布局便如此划分。
第一局,魏星对战赵良。
第二局,项羽对战严松。
第三局,公孙子龙对战屈平。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三局全胜,就不需要白承出手了。
四人决定好,由魏星将对战名单送到了裁决团的手中。
子贤见两方都同意如此对战,便让一旁的子由敲下了争鸣锣。
清脆的锣声一响,子由拉着嗓子大喊道:“第一局,赵国赵良对魏国魏星。攻方赵良出题,魏星答。开始——!”
话音才落,魏星便起身,走到正中,对面的赵良也走到了正中。两人先是对着各自微微一礼,便相对而坐。
这个时候儒家讲究正襟危坐,尤其是对战之时。
何为正襟?
要双腿蜷曲跪坐,保证后脚跟抵在后臀上,同时上身挺直,双手作揖,放在小腹正中。
而儒生衣冠必须保持平整,尤其是头上的冠,必须四方正正,不能歪斜。
此时两人坐好后,白承三人都在想,这个赵良能出何题?
事先白承四人考虑过,因为这次论战主题是儒家孟子的“为政王道”,重点就在于王道二字。
你说何为王道?怎么样执政才是王道?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一旦对方抓住了自己不擅长的一面,扬长避短,那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第一局赵良出题,让白承三人都为魏星捏了一把汗。
只见那赵良穿着赵国特有的国色服饰,显得很是英俊,浑身上下有一股正气。
而国色则代表了一国德行。而按照占星侯家的解释,一个国家与王朝的为政特点,必须或必然的与它的德性相符合,它所崇尚的颜色即国色,也必须与它的德性相符合。惟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在上天佑护下安稳顺畅的运行。
当今七大战国之中,三家分晋,魏国从晋国而出,自认晋国正统,晋恒公当年自认周王族,便举火承袭了周之火德,后来的魏国也就承继火德,旗帜服饰皆尚红色。所以魏国乃是火色!而韩国也出于晋国,但当年韩文侯为了争夺三晋之首,便弃火而推演出木,所以旗帜服饰皆为绿色。最后一家就是赵国,赵武侯为了显示赵国强大,直接将魏之火色,韩之木色,作为国色,以火德为主,木德为辅,木助火性,火德愈烈的火木德定为国色,旗帜也就变成了七分红色三分绿色。
所以此刻赵良的服饰很是讲究,正是七分红色,三分绿色,敝屣上纹有祥龙图案,代表了为国出战的贵族子弟。
这一战已经不是个人之间的荣辱了,更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
而魏星的服饰就是魏国火红的深衣,外加敝屣,典型的中规中矩。
此时赵良看着对面的魏星,嘴角突然扬起了一丝笑意,这笑意看在白承三人眼中,居然如此心惊。
莫非赵良选取的不是魏星擅长的方面?
而魏星也是心底暗暗一惊,他最不擅长的东西?按理说他从小熟读兵法列传,对诸子百家都有涉猎,还真没有什么不擅长的。但赵良的诡谲般笑意,让他心中反倒惴惴不安了。
此时子贤看向赵良,催促道:“请出题。”
赵良点了点头,扬起头,大声朗读道: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赵良开口之后,魏星脸色就变了,这小子居然从《楚辞》入手。而《楚辞》的确是魏人少有知道的东西。
因为昔年魏武侯称霸三晋,将楚国打得连连败北,所以楚国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千年老二”的不雅称号,自此楚魏不合。而魏国自诩天朝大国,不屑学习楚国文化,所以楚辞对于魏人来说,就是一块短板,也可能是唯一一块。
此时白承三人也是为魏星捏了一把汗,早知道他们就应该让楚国项氏一族的少主出战了。这真是失误了。
此时赵良背诵完整首楚辞后,面带笑意的对着魏星问道:“学兄可知这首楚辞?”
魏星面不改色答道:“楚辞,乃是楚国屈原大夫所创造的诗篇。它最先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句式的束缚,使得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
赵良笑得更开心了,说道:“看来,学兄对于楚辞音律很是擅长啊!”
魏星心中更加忐忑起来,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赵良既然敢拿魏人不擅长的楚辞来作为问题,就必然有更为强大的杀手锏,绝对不会单单是考量自己音律。
白承三人也是暗暗心惊。一旁的白承则看了一眼对面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太子秧,暗道此人果然是帅才,统筹大局,运筹帷幄。他一定事先打听过了魏星不擅长什么,所以才会用楚辞入题,显然经过严密的分析与布局才选择让赵良对战魏星的。
此时赵良点了点头,说道:“学兄说得不错,这首《国殇》正是屈原大夫描绘的一副两军对垒,血腥厮杀,一方将军战败被俘,最终英勇就义的场景。屈大夫借此来表达自己心志,荔枝鞠躬尽瘁,宁折不屈。不知学兄可赞同?”
魏星不知道赵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点头认同道:“不错,屈原大夫是楚地妇孺皆知的人物,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的王道志向,现在楚地人民为了纪念大夫,特意举行端午祭祀,来缅怀大夫。”
“好!”赵良当下一喝,让白承等众人暗暗心惊。
白承暗道:杀手锏要来了。
果不其然,只见赵良开始发难,他遥指魏星,问道:“学兄可认为屈原大夫以王道治国?”
魏星只能维持阵脚不乱,以不变应万变,答道:“是。”
赵良嘴角扬起一丝笑意,反问道:“那么学弟问学兄一句,楚国以王道治国,为何屈原大夫反倒最后投了汨罗而亡。如果王道治国,真的可以兴百业,强国基,为何屈原大夫,要在死前留下《离骚》,其中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正是说明大夫自己对王道治国的理想,连他自己都没有探索明白,最后失望至极,而投了汨罗了吗?可见王道治国,不过是小道尔。当今天下东西连成一线,魏、秦、齐三强独大。秦国以法治国,魏国信奉道家老子无为而治,国君垂拱,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齐国则信奉兵家孙武的强兵黩武之策,以战养国。请问学兄,王道治国可是小道尔?就连学兄的母国都不屑用王道治国,学兄还敢扬言王道治国为天下正统吗?”
魏星顿时哑口无言。
赵良一言出,技惊四座,无数儒家弟子在后面听得大动,高声喊道:“赞!大赞!”
赵良看了一眼沉默的魏星,颇为自信的对着后方儒家弟子微微鞠躬。
白承心中也是暗暗叫苦,这赵良心机深沉,先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一通屈原《楚辞》,让魏星不得不承认在诗词造诣方面高深的屈原是一位大英雄,大人物,最后却绝地反击,倒打一耙,将屈原王道治国的理想与他郁郁不得志而投江自杀联系在一起,侧面说明王道治国,不行!最后又举出天下七强其三基本没有王道治国的国家,给了魏星更加沉重的一击。
你所在的魏国都没有信奉王道治国,你还在这里叭叭什么?
这样的强有力打击,瞬间将魏星置之死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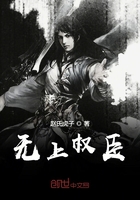
![古埃及[图说天下.世界历史系列]](https://i.dudushu.com/images/book/2019/09/25/1345550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