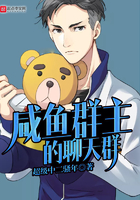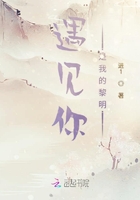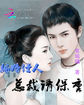母爱啊,是大海,比大海还深;是蓝天,比蓝天还高。但愿天下儿女们永远铭记一句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当我站在梅岭之巅,沐浴在深秋的梅国之中时,我突然感到似乎躺在母亲的怀里,那云朵似的梅林,正变成母亲柔软温馨的胸膛,在呵护着我,抚慰着我饱受磕碰的心扉。我的思绪顺着这条古驿道,仍在苦苦追寻,不寻早已失去的东隅,也不寻稍纵即逝的桑榆,我只要在心中永留寒梅。即使她已化作春泥,我也要在山的深处呼唤,在林的根下搜寻,或者愿和她一起融入大地,将躯体和魂灵翻作来年的新花。
2001年10月21日作于南昌
清风亭记
出靖安县城,南行约二公里,便到了该县的森林公园。进公园大门,迎面有一座雕像,束冠袖手,风骨岸然,乃明代之况钟也。雕像背后,还有他的衣冠墓,依山而建。山不高,石阶小径,弯弯曲曲,直达顶端。拾级而上,便是纪念况钟的一个小亭,名曰:清风亭。
亭子很小,且极简陋。六根水泥仿木柱子,撑着一个伞盖,四围置有石凳,供游人歇息。包围亭子的是一层层郁郁葱葱的树木,把它遮盖得严严实实,委实不起眼。
我的登亭,实出偶然。友人先是领我遍游园中若干景点,诸如古木、古尸、游乐场之类,绕了一大圈,才提议抄近路返回,于是便上了这清风亭。其时我倦意甚浓,便坐于亭中稍歇,谁料这一歇,竟将我疲劳尽扫,兴趣顿生。原来此亭虽陋,却有无价之宝。抬头望去,只见亭沿上有一圈青石,上刻况钟《饯别诗》四首,一遍读后,不禁肃然。兹抄于此:
正统四年冬,考满赴京,七邑耆民饯送者数百里弗绝。作此口占四首,遍贻耆民以致别。
其一曰:
十年鞅掌抚名邦,如水襟怀对大江。无法及民殊自愧,君恩有负每神伤。
其二曰: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渐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泪注如泉。
其三曰:
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其四曰:
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穑艰。
我自然忘了疲劳,仰观其诗,反复吟诵,脑海里竟出现了一幅感人的画图:一个苏州知府,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或地级市长吧,离职赴京之时,除行李一担而外,别无他物,实实在在的两袖清风。而前来送行的老百姓却多达两万余人,扶老携幼,洒泪挽留,乃至道路阻塞,车马不通。当时估计不会有人组织号召,完全是一种依依难舍的自发之情。
小时候就曾看过昆剧《十五贯》,况钟审娄阿鼠的场面记忆犹新,对况大人的印象便也多是“明镜高悬”、为民申冤的一面,今观其诗,考其史实,原来他的为官清廉,竟远高于明察秋毫之绩了。由此推论,又生出两点感受来。一是人心向背,古来分明。在封建社会里,做官便意味着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是常见不鲜的事,然而尽管贪官污吏横行天下,显耀门庭,在老百姓的心中,他们却是狗屎一堆,为人不齿。因为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他们的所得,皆民脂民膏,搜刮而来,这种贪官,自然是反民意而行其道的了。只有像况钟这样的清官,才能深得民心,塞道而留。我想封建朝代之所以一个个垮台,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清官太少,酷吏充斥,不能不说是相当重要的一条。二是为官者究竟应以什么为荣?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自古至今,多少人是不通此道的?有的人贪图金钱,认为有钱才有一切,因而以权捞钱,永无足意;有的人迷恋享乐,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因而尽情占有,欲壑难填;有的人则钟情权力,认为有官才有权,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其实这些人又能横行几时?纵使能一辈子、几辈子享用,殊不知正在挖自己的墙脚,政权正是倒在他们手上。而历代清官廉吏们,虽然在物质上得不到什么,也留不下什么,比如汉之洛阳令董宣,病逝时布被覆尸;晋之彭泽令陶渊明,弃职归隐,甘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宋之殿中侍御史赵忭,为政简朴,廉洁自守,唯一琴一鹤相随;还有明之户部主事海瑞,去世时家贫如洗,无以为葬,等等。可他们风范照耀千古,享受世代颂扬,不是比万两黄金更宝贵千万倍么?且说况钟1443年逝世,距今已五百多年,在这深山僻野,尚有一清风亭纪念,想那些豪强权贵们是望尘莫及的了。由此观之,为官而上不虑国,下不忧民,不念守土有责,不识荣耻之界,是狗官也。然则何留青史?其必深省曰:“去己欲以图天下,施德政以收民心。”
夜宿宾馆,思绪纷繁,为呼吸清新空气,便关了电视,凭窗而立。但见车水马龙,市井繁华。星星点点的霓虹灯发自大街小巷,闪烁不停,卡拉OK之声自大小酒肆传出,不绝于耳。我忽然萌生了想再看看《十五贯》的念头,转而又寻思,现在正时兴狂歌疯舞,谁还愿演那些戏?这个非分之想,怕是一时难以实现的了。于是便拉上窗帘,放倒头,睡我的觉去。
1996年作于靖安
湖口听浪
文人是蛮厉害的,古代文人尤为厉害,往往一句绝唱,声震几千年,硬是炒作出不朽之名山、名楼。譬如南昌的滕王阁,本是纨绔子弟李元婴为逍遥玩乐而建的一个戏楼,经王勃一“序”,便不得了了,数百年来毁了28次,仍那么倔强地挺立在赣江边上。安徽滁州有什么景致?“环滁皆山”,皆光秃秃的山也,自从有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便“醉”出一幅令人向往的山水画来,引无数游客竞折腰。难怪有人说文人就是会吹,死的能吹成活的。再想想,还得感谢文人,要不你到哪儿旅游去?
到湖口看石钟山,最先生发的便是这种感慨。
我登石钟山,正值春夏之交,其时芳菲已尽,绿荫正浓。脚下,长江与鄱阳湖界线分明的水域尽收眼底,恰似一对恋人,相互拥抱着、融合着,温情地飘向远方。这山呢?委实是小,小到几乎一眼可览全貌,一脚可跨两边。我于是想到了苏学士夜探水域之典,想到了诞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一先哲之语的宝地,便向友人提出要听听石钟之浪,心想点到为止,便可班师了。
“你是太不了解石钟山了呢!”友人显然窥到了我的心思,头摇得像拨浪鼓,大有“人不识宝徒自叹”之感。他是湖口县的知名文化人,对石钟山自然情有独钟。他执意要先带我看看别的景点,最后才去听浪。我不能拂了他的好意,便随他绕到了山的东面。
与临湖的西面相比,东面山势较缓,嶙峋怪石不多,倒是在疏林密树之间,错落着一些状态各异的楼台亭阁,甚是别致。友人把我带进一座别墅,乃当年曾国藩的得力部将彭玉麟青年时代攻书之所。穿堂而过,便是后花园,园中小桥流水,鸟语花香。中有一亭,名“且闲亭”。亭的左边有一块一米多高、形似人体的立石,右边有一棵碗口粗细的阔叶树,曰“怕痒树”,看上去是无皮的,人一碰树干,整棵树就摇晃不停。传说古时有一少男,姓冷名云,喜种花草,终日辛劳,养下了一大片名花,感动了上天的花神紫薇仙子,便下凡与他相恋,并结庐石钟山,夫妇种花为业。不料此事惊动了玉皇大帝,遂派天使捉拿归案,紫薇仙子坚留不往,天使无法,扯其衣裙而去。玉帝大怒,将紫薇变成一棵无皮树,将冷云变成一块石头,千百年来相对无语。
我听了感叹不已,心想中国的神话传说怎么都是爱情的悲剧?“天仙配”“梁祝”,还有散落各地的诸如此类传说,总是大同小异,一边是善与美的追求,一边是恶与丑的扼杀,最终只留得撕碎的梦幻,引后人叹惜。
“是呀,何止是神话传说呢?”友人对此也有同感,说着便领我来到一片梅林,那梅林确是壮观,足铺满了一面山坡。倘在冬末春初,那斑斓的花蕊,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不知能醉倒多少情男爱女哩!梅林深处又见一亭,亭沿嵌有“百梅亭”三字牌匾,笔画苍劲,颇有铁梅之风。友人介绍说,这梅林和梅亭,便是彭玉麟将军刻意偿还一位姑娘的情债。原来彭将军在此地苦读之时,结识了一位少女,名叫梅香。梅香长得亭亭玉立,漂亮非常。她爱慕玉麟才貌双全,欲与他结成连理,但玉麟胸怀大志,不愿早婚,便忍痛不辞而别,远走他乡。梅香终日忧郁不已,心想至爱之人既不能得,活着还有何意思?便从石钟山上跳崖自尽。玉麟闻之悲痛万分,发誓要在石钟山栽梅树百棵以表纪念。后来他成就了大业,随曾国藩转战至此,果然遍植梅树,并建了“百梅亭”,亭的形状亦为梅花一朵。
友人一再强调,这个故事不属虚构,是确有其事,我自然是相信的。彭玉麟在清末,尤其在湘军中,是数得上的人物,他为了立志而割舍情爱,恐怕也无可非议,可怜的只有梅香。其实这也是一种扼杀,用所谓的事业扼杀了爱情。我想不通,事业与爱情为什么就不能两全?难道打着事业的幌子去谋求高官厚禄,就可以牺牲珍贵的情感么?
出了梅林,翻过山头,方才攀着石径,下到当年苏东坡考察石钟之处,听着那沉闷的浪击之声,我的思绪宛如进入了时空隧道,沿石钟山的现在走向古时,走到了紫薇仙子和梅香姑娘的身边,恍惚听到了她们正在倾诉,倾诉世道的不公,倾诉善和美的悲惨境遇。面对她们,我无言以对。人类进化了几千年,至今还是好人难做,在封建和世俗的利刃之下,善良和美丽总是被宰割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直等到物换星移,尘埃落定,历史才软弱无力地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于是也才有了后世同类的一掬泪水,几声抽泣。然而,历史却仍在转着圈,导演着同样的悲剧,为再一轮“后来”创造可歌可泣的素材。这究竟是悲还是壮?我不知道,但细想起来,也只有她们,方能使人类在遗传邪恶的时候,还知道有“正义”二字,才产生了同情、支持和抗争,于是,世界在二者的打斗中继续前行。想到这里,我不知是对她们还是对我自己,只迸出一个字:值!
离别石钟山的时候,已是下午五六点钟了。我站在摆渡的船头,远远望去,见石钟山正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波浪拍打着石壁,传来沉浑的钟声。我对这座小山突然敬仰起来,因为它与其他景致不同,虽也依赖文人出名,但毕竟有着自身丰富的内涵,恰如一位多情的少女,浑身透出善和美的灵气—这真的是一座好山。
2000年6月18日作于南昌
寻韵龙虎山
想起写龙虎山,缘于“掉棺”的故事。
江西鹰潭有座龙虎山。龙虎山芦溪河边的悬崖上,到处都是岩洞,岩洞里藏着年代久远的悬棺。那些岩洞高低不一,离水面高的有几百米。山是悬崖峭壁,难以攀爬。古人是怎样把这些棺木放进去的?很多科学家对此进行过考察研究,说法不一。其中有一说就是吊棺,即在山顶上设一支点,安一滑轮,装上绳索,将棺木用船运至岩洞下面,人站在棺木上,一起吊至岩洞边,再荡进洞去。
为了证明这个法子的可行,当地有三兄弟自告奋勇,愿意进行表演。于是在龙虎山的旅游项目中,又增加了吊棺的内容。表演时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好不热闹。兄弟几个每天表演几次,身手敏捷,技巧娴熟,从不失手。
然而有一次表演吊棺的时候,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色灰暗,山雨欲来。正当三兄弟在半空中翻腾得起劲时,吊绳突然断裂,人、棺一齐掉了下来,落入水中。有“高人”说,这是因为观者里边有一贪官,本已贪得无厌,却还想往上爬,因而触怒了上帝,以此戒勉于他。然而这个贪官后来并没有因此反省,最终落得了可悲的下场。这也说明了为官切不可贪得过分,头上三尺有神明,纵使人不怒,也会招致天怨的。所幸那无辜的三兄弟,受此一吓,并没有大碍,只是虚惊一场。打那以后,为趋吉避凶,便把这“吊棺”改称为“升棺”了。
后来一想起这件事,就有了向道的心思。
要我说,古时最聪明的人是和尚道士,你看大凡名山大川,几乎都有释、道二教的道场。早在汉朝时期,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就选择龙虎山炼丹修道,“丹成而龙虎见”,以至此地成为道教的祖庭。道教主张“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寻求的是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神清气爽,长生不老,所以其道观宫殿都建在美妙无比的山水之间。你看这龙虎山,山是丹霞地貌,奇峰异谷;水是深涧清泉,荡漾蜿蜒。游人来至仙水岩后,弃车登舟,便如进入了仙境。那船工一声“坐稳了喂—”,手把竹槁,倾身一撑,小船便分开碧波,飘然洒脱,信步而去。两岸是看不厌的十处景致,俗称“十不得”,比如:仙桃咬不得,莲花坐不得,尼姑背不得,仙女配不得,等等。尤其是那“仙女配不得”,又叫“大地之母”,人称天下第一绝景。河湾之处,有一座石山,就像一块屏风挡在前面,名叫“遮羞石”,绕过石后,便有一条小沟,曲径通幽。幽然之处,一个绝景赫然展现在目。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山型,活像一位女性,曲张着双腿,正在蹲着小解,所有生理结构凸现无遗。女阴上部还隐隐有一丛干枯的茅草,据说以前是有泉水流出的,“文革”时一位小军官看了,也不知出于何因,掏出手枪连开数枪,从此便没有水了。当然这只是传说,仙水怎能被小丑击退?想是生态变差之故,山中无水可流了。不管怎样,每次到此,我都是在惊叹之余,顿生敬畏之心,感念造物之神,根本不会有所邪念。实际上很多人是在这里顶礼膜拜的,一个时期,这里还可看到遍地的鞭炮屑,甚至还有烧香点烛的。善良的人们总是以最虔诚之心,崇拜着伟大的图腾,以感谢上天对人类的恩赐。离此处不远,还有一个绝景,称为“金枪峰”,又叫“金枪刺不得”,也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天地造化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有阴有阳,有正有负,有公有母,才符合宇宙运行之法则。
离了仙水岩,溯河而上,约行十余里,便到了上清宫。
上清宫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紧靠泸溪河。站在河边打眼望去,但见千峰竞秀,万壑争奇,花原斗艳,林海涌潮。那山,分明一边是奔腾之龙,一边是咆哮之虎,真乃龙盘虎踞,风生水起,难怪这里已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的第三十二福地了。据说这里原有大小道教建筑五十余处,蔚为壮观。《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攘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讲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那口曾飞出一百零八将的镇妖井,如今又被盖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古时的众多宫观,因屡遭天灾兵火,大部分已被毁废,今仅存天师府一座,已辟为全国道教重点开放宫观之一,供游人参观。每年秋天,还会举办一次盛大的道教活动,来自海内外的教徒数以百计,热闹非凡。
天师府的规模不算很大,中门四进,左右两排偏殿,却也别具一格,甚为整齐。院内建筑多为近年新建,古物所存寥寥无几。倒是那些参天大树,以它们饱经风霜的枝干和繁茂的叶冠,抚慰着这几经兴废的殿堂,把一个天师府点缀得风韵别致,生机盎然。
天师府两边,沿泸溪河岸,是逶迤而建的上清小镇,一色的吊脚小楼,一色的石板街面,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
小镇上的居民,多是天师府的道教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