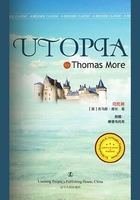去年下雪的日子实是好记,临近过年,正当“大寒”那天,大雪翩然而至。虽顾名思义,下雪的正日子应该是在“大雪”节气,但农历是按照黄河流域的气象、根据太阳和月亮的位置确定节气的,南方的雪比北方迟一点也是顺乎天意地理的。
记得那天凭窗眺望,空中的雪粒连绵不绝地、均匀地散落,好像干燥白纯的面粉。接近地面的雪粒陡然丰满,被东北风扇着斜射成密匝匝的羽阵,像巨大的天鹅抖落漫天羽绒。阳台雨篷上的雪,间或如一只白色鸟义无反顾地急速坠落,在地面敲击出“啪”的一声。树冠上成团成团的白色在滚落,如山崖崩塌,然而洁白可爱。电线杆向东北的一边,被涂上了毛茸茸的一层白。于是电线杆半边白,半边黑;半边干,半边冻;如一幅精致的木刻。停靠在小区围墙边的长排汽车,像盖上了厚厚的棉被,一辆辆被他们的主人抛弃在家,木讷而委屈。偶尔有辆开出去的,地上留下了一个边沿清晰的黑色长方形。雪花还是不停地纷纷扬扬,它们悠闲而雅致地舞动着飘落,于是那汽车蹲过的地面,黑色的长方形边缘逐渐模糊起来,慢慢地竟然有了邮票那样的缺刻,后来更像是残缺的破草席,灰沉沉了。
雪后放晴,层层楼台,处处金色。先是大块的雪从楼顶上崩塌下来,轰隆隆发出巨大的响声。然后终日滴滴答答如骤雨不绝。排在围墙边的汽车显出了真面目,绿的是绿,蓝的是蓝,红的是红,银的是银,白的脱了厚重只显光滑亮洁。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扫起的积雪一堆堆,中间的路面干燥而白亮亮。
屋里的电暖锅热气腾腾,氤氲着家常的温馨。隔着白色的蒸汽,我望见了逝去的岁月,那雪天步行的年轻人隐隐在前,如前世。
想起半个世纪前,我却在寒冬里长途跋涉。我参与创建并任教的大榭中学放寒假了,王校长说,每人发五十斤学校开荒自产的萝卜。那时尚处在困难时期的尾巴,当地又以盛产萝卜干闻名,大家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路远,第二天才走。大清早,却见七顶山雪满山冻不流云,田野上银装素裹一色净,还少有行人的足迹。我穿着薄裤旧棉袄,一根小扁担挑起约莫二十余斤萝卜,赶过渡口,赶到穿山长途汽车站。等了许久,等车的人一个个离去。一位农民说:今天车子不来了,阿拉走吧。我只好挑起扁担就走。经山门,往霞浦,向大碶。公路上铺满了雪,路倒好走,嚓嚓嚓地踩扁碎琼乱玉。只是百步无轻担,扁担压得肩膀疼。革命人不怕肩膀疼,怕的是走得过快担子要摇晃,只好合着节拍不紧不慢地行,想起婶婶常笑话没用的青年人“廿岁英雄,只挑两盏灯笼”,自己就要争争气,不让婶婶笑话。中午经过大碶,碶桥边有一家小店,坐下吃了一碗粉丝,上面竟有几片牛肉,好不兴奋。又上路向山边行走,翻越布阵岭,过小港,渡甬江,看到了镇海鼓楼。进了石框小门到了家,已经下午向晚了。婶婶惊讶地看我放下担子,递过一杯热茶,说大雪天怎么来了。去翻看袋子,见无非是一些萝卜,又抬眼望望我。我八岁慈母见背,婶婶就是我的阿姆。工资早就寄的寄了用的用了,两手空空,再没有什么可以交给阿姆了。
第二天雪过放晴,阿姆交给我一些带鱼票和钞票,叫我去排队买过年小菜,我耐心地去排队,为有事做而高兴。
阿姆已去世多年,随着自己年岁徒增,那场雪拌和着惭愧却在心底里越发清晰起来。我还是盼着下雪,尽管自己的额前已挂霜雪,可我心中的雪总是向年轻的季节飘去,总是见到雪后的风景分外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