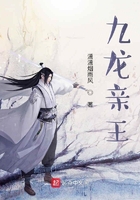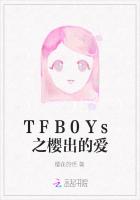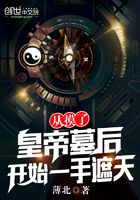6月底,上街时忽然见到十字路口有了红绿灯。马路边黄漆的钢柱坚实地笔直伸起,黄漆的钢臂在行道树的绿荫遮蔽中毅然挥手横出,臂上亮出红、黄、绿三种灯。我说的是北仑区大碶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小镇。但见镇大路、坝头路交叉口,人民路、坝头路交叉口,人民路、镇兴路交叉口,都站立了高大的黄衣交通“裁判”。马路中间也划上了黄色的分道线,交叉口路面上都标上了白色的斑马线。这使人大为兴奋,像城市了。
并非少见多怪,红绿灯谁没有见过?我在市中心溜达,常常宁可走天桥,怕走斑马线,怕不速之客。即使走斑马线,也总是混在一大群过客中穿越,而且步履匆匆,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乡下人。后来,注意到红绿灯转换的间隔,从从容容穿过马路,俨然城里人了。
于是,非常希望居处的小镇街道也有红绿灯,叫那些乱窜的自行车,把拐角处人行道当作田间小道直接抄近路穿过的三轮车也放规矩一些。退一步想想,那些车子也可怜,兴致勃勃地飞滚着轮子,忽然来个就地急刹车——放心!并没出什么事,前边到十字路口了,遇上了地上铁管做的滑溜溜的减速杆,常常瞄准两条杆子相接处几寸宽的豁口穿过去,那高超的车技特叫人赞叹。
我是特地去瞻仰那些红绿灯的,看到每个十字路口的减速杆居然已经挖掉,坦荡荡的马路显出了光洁的面容。街道也显得宽敞了许多,一眼就可以瞥见对面马路人行道边花坛里红的、黄的、紫的花丛。
对面的红灯亮了,在雨天里鲜明而无声,这边的一辆的士、一辆摩托、一辆自行车竟然停了下来,往左右一望,却并无交警。红色的数字递减下来,灯忽地黄了,它们都起步了;灯绿了,车子早穿过马路。灯又红了,横路上车辆如流,这边一辆三轮车载着客也只好停下来。右横路上一个中年妇女骑着自行车忽然小转弯左拐,向停着的那辆三轮车左边擦过,三轮车工人骂了一句:“眼睛瞎了啊!介亮的红灯也没看见!”那妇人竟不敢回嘴,一溜烟走了。
这就是变化啊!我兴奋地想。城市不是由建筑构成的,归根结底是由人构成的,人的素质构成了城市的品位。三轮车工人那句骂尽管粗野,却是交上了一份合格的交通规则的试卷。
这部分街区的居民在安装好红绿灯的那天,也许并没有发觉他们正在经受一场进入城市社会的考试。从此,“走路”这样一件极不起眼的小事,也须遵守社会法则了。
不过,古人早已把“行”字摆在“衣、食、住”后面了。走惯了浪漫的山野小道的乡民,漫不经心走惯了街巷弄堂的小镇居民,现在,连怎样走路也得学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