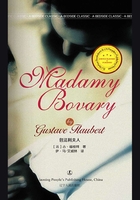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毫不夸张地说,为了今天的远游,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备战备荒为人民一样,自从有了远游的雄心壮志,猫头和我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紧盯着这个目标。
那年夏天,满叔从海南岛回来探亲,有三样东西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黑,满叔说是海南岛的日头晒的,我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狗日的日头是什么东西做的,硬是比我们这里的日头还牛B!二是他带回的几个麻色的球,满叔说这叫椰子,里头有水有肉,水清肉白,水好喝,肉好呷;满叔说:“猫头、猴头,你们两人共一个。”猫头拿了一把柴刀,对我说:“猴头,你扶,我剁!”我双手扶着椰子球,眼睛却望着猫头双手握把、高举过头的柴刀,觉得刀锋贼亮,亮得我头皮发麻,心窝透凉;寒光一闪,刀锋直下,我眼睛一闭,双手不由自主地松开椰子球……只听得噹的一声,心想这下完了,睁开眼睛一看:还好,手在膝盖上,只是有点抖;椰子球在石头骨碌下,打着转转,浑然无事;柴刀缺了一个口子,像一条咬人不着反而受伤的蛇,僵在石头骨碌上。猫头对这个结果似乎有些糊涂,似乎又有些生气,搔了搔板结的头发,说:“狗日的,我就不信,奈你不何。你剁,我扶。”握着柴刀,比划了好几次,我还是不敢下手:虽说我对猫头的头是有些讨厌,但是,我不敢保证,这一刀下去万一剁开的不是椰子球而是猫头的头,自己不会后悔终生,我没有这个把握。猫头却在下面催命:“剁,剁,剁,快点!”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既然你自己不把脑壳当回事,那就怪不得我啦。我将刀把一转,刀口朝上,刀背朝下,闭着眼,使劲地砍了下去。哎哟,听得猫头在底下一叫。我的身子登时软了。“快喝,快喝,水快流完了。”睁开眼,却见猫头捧着一瓣椰子朝我嘴巴边送;我眼睛一热,骂了一句“狗日的,看你硬”,接过那瓣椰子,一口就喝干了。说真的,那水赶不上我们老井头的泉水。它也凉,但是没得老井头的泉水凉得那么冰、那么爽;它也甜,但是不比老井头的泉水甜得那么正宗,有一股腻歪歪的甜味;关键是它少,一口就没了,我们老井头的泉水你只要办肚子来就是,要多少有多少,紧你的量。这就是我们——猫头和我——对椰子的意见,事后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一致通过的。第三桩,是满叔对我们剁椰子的反应。“行,比满叔强,”满叔说,“满叔第一次呷椰子,撵它喊爷。牙齿咬,不行;拳头捶,不行;双手捏,不行;脚揣,不行。后来,捡了块石头,砸;椰子是砸开了,开得四分五裂,水都流尽了,手还砸烂了。”满叔又说:“我第一次呷压缩饼干比呷椰子还狼狈。椰子是海南岛第一次呷,压缩饼干不是海南岛第一次呷……”满叔第一次呷压缩饼干的狼狈相,我们早忘了;但是,那个与压缩饼干同根而生的第一次却让我们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说:“那一天,东方刚白,带队老师手一挥,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举着红旗,我们唱着歌,我们排着纵队;我们一式草绿色军装,我们一式草鞋,我们一式红袖章;我们挂着露珠,我们挂着汗珠,在韶山、在井冈山,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流着泪,流着泪,流着泪,哎呀,还是流着泪!”这次探亲之后不久,部队给我们奶奶送来了一个红本本,满叔再也没有回来了。满叔的长相,一天天地变形了、抽象了、淡漠了;不过,满叔的那番话,却让我和猫头每一念及就流泪、流泪、流泪,哎呀,还是流泪,难以自制。不是你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流泪;每流一次泪,那个念头就在我们的心头坚定几分:什么时候,我们也像满叔那样出发,出发!
“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对猫头说,“我们要准备。”
“准备什么?”猫头一脸傻相。
先要准备钱,我说。我们不比满叔,满叔有压缩饼干发,有火车趴;也不比唐僧,唐僧有缘化,有小龙马骑。我们没有。所以,至少要准备十块钱。
“怎么,要十块?”猫头问这话的时候活像一个猪头。
我给他算帐——我们给大人跑一次腿,从家里到小卖部,一个来回差不多一公里,通常可以赚到两粒糖珠子;两粒糖珠子一分钱,也就是说一分钱一公里;我们准备十块钱,十块钱就是一千分钱,一千分钱就是一千公里;到韶山、到井冈山、到天安门没得千公里,八百公里总有吧?再说哪,我们又不是孙猴子,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八百公里总要有几天。大人一个劳动日差不多五毛钱,我们两个顶一个大人,一天也算五毛钱。十块钱就可以走二十天,一天四十公里;猫头你想啊,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了多久?走了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差不多就是四十公里呢。
“你莫讲了,越讲我越胡糊涂了,依你就是。猴头,不存十块钱我们就不走。”
一个由两个半截合成的竹筒就成了我们的存钱罐。我们把它放在门前大枫树的树洞里,树洞很深,我们不担心别人会发现。第一笔钱是满叔探亲那年秋天存进去的,不过枫叶还没有红。那年,我和猫头放落书包就捡禾线,捡了禾线就给奶奶,奶奶就喂鸡,鸡就生蛋。奶奶不吃鸡蛋。这些蛋除了换回一大家子的油盐外,还能给大家——主要是奶奶的几个孙子孙女们——打打牙祭。奶奶高兴,竟给我和猫头一人一只生鸡蛋。我们拿到了小卖部,积下了我们第一笔存款——一张1972年版的、缺了一小角的、一毛钱纸币。一次能存一角钱,发大财了。
隔一段时间,我们会把楠竹筒拿出来,坐在沙地上,摇一摇,听那个响:然后扭开,把钱倒在地上,清理着我们的收获和喜悦。“三毛八了”;“九毛六了”;“一块零七了”;“哎呀,两块四毛四了”;“不会数错吧,五块七毛二!再数一遍,真是五块七毛二”……我们小声地咬着耳朵,高兴地你捅我一拳,我捶你一下。每一笔钱,我们都清楚地记着它的来历,栩栩如生。比如说,这一分钱——硬币、币面有个小凹点、1974年的——是这样来的:奶奶给我们五分钱,让我们去买两盒火柴;像往常一样,小卖部给我们两盒火柴、两粒糖珠子;我们拼命压下了涌到口腔里的口水,把糖珠子还给了他,要他找一分钱。于是,就有了这一分钱。这五毛钱呢?我和猫头摔了九跤摔来的,他五跤我四跤,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弄到一袋香油籽,五分钱斤、卖给了赤脚医生。这五分钱哦?是莲子给我们的。当然不是白给。莲子在学校得了奖——一个作业本和一盒十二种颜色的蜡笔,莲子妈就给了她一毛钱;莲子来找我们做风车。我们花了老半天才做好的:大中小三层,还带着一个风哨;风车叶子用蜡笔涂成五颜六色,迎风旋转,花作一团,风哨伴舞,抑扬有节。——莲子分给我们五分钱,不冤枉吧?
在准备钱的同时,我们还准备了地图。地图绘在一张牛皮纸上,那些地名都是有来历的。一是我们村子里的,像榨油厂、荒塘冲、胡新屋、刘老屋、清水桥,等等;二是我们亲自去过的,像斗笠冲、仙鹤嘴、万水观、马厂、唐铺,是去我外婆家的必经之地,岔子桥、犀牛湾、石龙口、黄土岭、竹鸡寨,是去猫头外婆家的必经之地;三是满叔那番讲述中提到的,像石子街、新桥、湘潭、韶山、井冈山、长沙、北京、天安门,等等;四是大人们谈天说地时聊到的,像大夫第、荷叶塘、西渡、南岳、南京、美女梳头峰、衡州府、大码头、铜钱渡,等等;五是课文告诉我们的,像沙洲坝、杨家岭、雪山、草地、美帝、苏修、上甘岭、加拿大,等等;六是样板戏告诉我们的,像威虎山、沙家滨,等等;七是小人书告诉我们的,像花果山、野猪林、长坂坡、青松岭,等等;八是……一句话,凡在我们地图上出现的名字都有根有据,不是我和猫头摸脑壳乱编的。
我们以村子为中心,画了一个十字架:最北是北京,最南是南京,最东是天安门,最西是美帝苏修。为了确定这个十字架,我和猫头争论了三天三夜,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北京和天安门。猫头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北京和天安门要在一起,要不都在北边、要不都在东边。”我说:“北京,看名字就晓得在北方;天安门上太阳升,肯定在东方。”猫头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天安门肯定在一起哪。”我说:“你爱上树下河、逃作业看电影,你爱你娘,你爱红烧肉,你爱毛主席,他们都在一起呀?”最终,猫头听了我的。这个十字架的确立,为我们准确标示那些地方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韶山、井冈山、上甘岭、沙洲坝、杨家岭、青松岭、沙家滨、新桥、湘潭肯定都在东边;大夫第、荷叶塘、西渡、威虎山、野猪林、美女梳头峰肯定都在西边;长沙、衡州府、铜钱渡、雪山、草地、加拿大、花果山、长坂坡肯定都在北边;南岳、海南岛肯定都在南边。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让我们难以决断。比如,大码头吧,据大人们讲离衡州府不远,看起来应该在北边了,但是,这个大码头不是个好地方,大人们有时骂我们:“到大码头去砍脑啊!”所以,更有理由在西边,和苏修美帝呆在一起。最后,我和猫头一致同意把“大码头”标在“美女梳女峰”和“西渡”之间。现在,我可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幅地图比我们的更详尽、更准确、更生动直观、更一目了然了。猫头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外婆的家和美帝苏修在一起。我说:“哪要你外婆住西边呢!”不过,猫头后来也想开了:“反正外婆也不在世了。”
我们要准备的还有草鞋、草绿色军装、红袖章、红旗,可多了。草鞋,我们自己晓得编,容易。原以为草绿色军装是难事,好在满叔遗有几套,别人虽然眼红,但是争不过我们,我们是他亲侄子么;长是长了点,大是大了点,但总是正宗的草绿色军装吧。红袖章、红旗可就难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着落。猫头对我说:“猴头,干脆哪天晚上我们去把学校那面红旗偷来算了。”我说:“那可不行,我们不能做贼。”后来,还是我聪明:我对猫头说,我们在学校要表现好,表现好就能入队,入队就有红领巾。果然,不久我们就都有红领巾了,高兴得猫头跳了起来。我说:“莫高兴得太早,还差呢,两面红领巾顶多改成两个红袖章,还差一面红旗。”猫头急了,死劲抓自己板结的头发,说:“猴头,你讲,吗办,吗办?”这个还不好办?我把自己的红领巾藏起来,藏在存钱罐里,哭着对老师说自己的红领巾丢了——就这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有了三面红领巾;两面可以改成红袖章,一面不用改,绑在树枝上,就是小红旗。当然,力还是费了点:对我“丢”掉那面红领巾,老师倒没说什么,我爹在我屁股上用力地打了几巴掌,说是让我以后小心点。
哦,还有一项重要的准备忘记说了,就是唱歌。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五节课。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课:语文、数学;第五节附课:一节体育课、一节美术课、两节劳动课、一节音乐兼德育及班会课。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从课程设计来看,我们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班主任教我们音乐兼德育兼班会课,他比较注重德育,给我们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道理就像唱歌一样,悦耳动听,铿锵有力;教我们音乐的时候反倒有点像讲道理,令人昏昏欲睡。但是,我们既然要远游,就必须像满叔一样唱着歌去。好在我们身边有个现成的老师:莲子。那一年满叔回家探亲,奶奶的意思是让他对一门亲走,托人介绍了一摞子姑娘,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美美丑丑,偏偏都不中满叔的意;满叔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瞒不过我们,我们知道他是看上莲子娘了。在我们看来了,满叔和莲子娘蛮般配。虽说莲子娘有了莲子,但还是和那些没出嫁的大姑娘一样鲜活、水灵。因为我们作不了主,不知道大人们最后是怎么搞的,这个事就拖了下去。那天,部队把变成红本本的满叔送回家,我们发现莲子娘没有多大哭声,但看起来比我们奶奶还伤心。莲子娘是莲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音乐盒,我们要不得那么多,从莲子那里取了几段凑成了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切就绪,像大人老挂在嘴边的那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昨天晚上,我和猫头就着一碗干红辣椒,各扒了两碗饭。往常我们都会去添第三碗,这时,猫头啪地放下筷子,说:“饱啦,饱啦,不呷了。”——他的意思是说,该出发了。
“再呷一碗,就一碗。”——我的意思是说,再等等。
“不呷了。奶奶说满叔一日三餐九饭碗。我们加起来,这餐都四碗了。”——意思是,满叔十七岁时去的韶山去的天安门,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二十多了。
“就一碗,”我向他眨了眨了眼睛,加重了语气,“就一碗。”
“好,就一碗。”他点了点头,懂了。
早上,我和猫头都换上草绿色军装,穿上了草鞋。奶奶说:“呀,怎么换了这身皮?”我们说,学校演节目,我们扮解放军。奶奶“哦”了一声,没有再问什么。嘿嘿,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在大枫树下,我们按计划是要取存钱罐的;不过,莲子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这可是计划中没有的。猫头呆头呆脑要去取存钱罐,我拽了他一把,说:“走哪,要迟到啦。”
快到清水桥边了。这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去我们学校;往东,去我们家;往南,过清水桥,毫无疑问可以直达南京。按照计划,猫头用手捂着肚子,蹲了下来,“哎哟哎哟”地叫。
“怎么啦,猫头哥?”莲子问。
“可能是吃多了,今天早上我说你要少呷一碗,他硬要多呷一碗,”我按计划说,“要迟到了,莲子,你先走,到学校给我们请个假,我陪猫头到赤脚医生那里去。”
“是呀,莲子,要迟到了,你先走,猴头留下来就行了。”猫头也按计划说。
莲子看了看我,看了看猫头,突然“哼”了一声,说:“别以为我不知道。”扭头就走了。
莲子走几步回一下头,走几步回一下头,渐渐地远了,发辫在脑后一上一下,似乎在说:“别以为我不知道,别以为我不知道!”终于,转了一个弯,看不见影儿了。猫头一下子挺直了身子,一把抱着我,蹦着,喊着:“噢!噢!噢!”
按照计划,这时我们应该直接过清水桥,先往南走,然后再折向东边或者北边,我们用刚刚学会的两个词给这个计划取了一名字,叫“声东击西、南辕北辙”。但是,因为莲子在大枫树下出现,我们没能够按计划把存钱罐取出来,把书包存进去,所以不得稍微修正下原计划,往东去,回到大枫树那里。
可是,走了几步,我说:“不行。”猫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分析——我这个人爱分析——道:“我们回去不要紧,万一,不,肯定会碰到大人,那就等于自投罗网,前头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
“怎么办?”猫头问。
“按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计划做,过清水桥!”
“钱呢?”
“不带了,丢掉坛坛罐罐。”
“不白准备了?”
“也不白准备。”我说,“我们带在身上是钱,放在存钱罐里也是钱,反正我们有钱,走到哪里都不慌。”
“红旗红袖章呢?”
“一个打红旗,一个戴红袖章,轮流来,刚好两条红领巾。”
“书包呢,丢了?”
“不能丢,”我说,“满叔他们拉练要打背包呢。”
“听你的,猴头。”猫头说,“你举红旗,我戴红袖章。走。过清水桥。”
晨风吹拂小红旗,初升的太阳照着我们半边面庞,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猫头在后面喊:“唱错啦,唱错啦!”我说:“没错,没错,放开喉咙唱!越过平原,越过高山,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两个人的声音虽说盖不住清水桥下的流水声,但是我们毕竟只有两个人,不是大部队。
翻过天带岭,绕过三十六弯,就进入了我们陌生的领域。真是天遂人愿——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条河,公路顺河而下——所有的河水都向东流,只要我们跟着河水下,“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计划不就实现了吗?这真是一个天才的计划!
这条河,和我们门前那条小河一样;河面不宽,像一条带子;河水浅浅的,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沙、石。突然,猫头说:“热,猴头,你热不热?”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下河去,我的心也痒痒的,说:“狗日的,真热!”
我们把书包扔到河边的草地上,脱掉草鞋,挽起裤脚,跳到了河里。真好!这水也和我们门前那条小河一样,凉爽爽的。你拊我一身水,我拊你一身水,互相追打着,我们的草绿色军装一下子就湿透了。于是,干脆脱了,只穿着短裤下到河里。
猫头竖起一根手指,在嘴边“嘘”了一下,又指了指河水,小声地说:“有鱼。”我低头一看,果然,有几尾小鱼在水里倏忽来去。我说:“是钻子鱼!猫头,你在上头赶,我在下头堵。”这钻子鱼也和门前小河中的一样,跑得贼快;有好几次,我们的手都快抓住它了,不知为什么又让它跑了。猫头气得和着身子扑下去,说:“狗日的,这下总跑不了,这下总跑不了!”可惜,还是让它们跑了。最后,我们实在累了,我说:“算了,猫头,哪天我们办个操罾来。”猫头说:“狗日的,说不定比我们先到天安门!”上得岸来,衣服还没干,河边的青草地看起来又是那么可爱,我们就向天倒在了草地上,看了一会云,聊了几句天,就睡着了。
“火车来了!火车来了……”猫头在梦中喊了起来。
我睁开眼睛,一辆“火车”——我和猫头有时管手扶拖拉机叫“火车”——正突突地向我们开来。
“快,猴头!快……”
我和猫头都是爬手扶拖拉机的好手,转眼间,就都在车子上了。车子一簸一簸的,就像我们的高兴劲儿。
“哎呀,你的鞋呢?”猫头说。
“哎呀,你的书包呢?”我说。
——车子簸了一两里,我们才发现丢东西了:我的草鞋、小红旗,猫头的书包都忘在河边的草地上了。我说,下车去拿;猫头说,算了,好不容易爬上了火车。我想,也是,反正我们打赤脚打惯了,没有草鞋还觉得方便些,并且我们还有一面红领巾,可以改成小红旗,不影响这次远游,也还有一个书包,不影响以后上学。于是,安安心心站在车上,任它颠簸着,拉着我们向远方。
手扶拖拉机在一个镇子上停了下来,司机朝我们喊:“下车,下车,不走了!”
这个镇子依路而建,两边的房子一眼看不到头,看来比我们村子里赶集的集镇要长、要大,比我们公社的也要长、要大。我们一路走过去。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礼堂,礼堂顶上的红旗。太阳斜斜地照着礼堂,把它的影子拖在广场上。看着礼堂,我们大气也不敢出,因为礼堂正面墙壁的上方悬挂着两幅巨大的画像。
“天安门,天安门!”猫头长长地吸了一鼻子气,喃喃地说。
“天安门,天安门!”我也长长地吸了一算子气,喃喃地说。
“毛主席看着我们呢。”猫头说,“他老人家边上是不是副统帅?”
“不会。听说副统帅披着马列的外衣、偷了毛主席三只鸡跑了。”我说,“应该是英明领袖,学校上次敲锣打鼓就接的他。”
“伟大领袖,英明领袖,”猫头自言自语一会,说,“一定是天安门!一定是天安门!猴头,我们要升旗,我们要唱歌,我们……”
这地方,旗杆比较难找。我们在墙壁边上发现一个刷石灰字的扫帚;墙壁上新刷有一条石灰标语——“向二000年进军!”—一个个字,谷箩大,扫帚就在叹号下。猫头把红领巾系在扫帚上,举着;我们并排站着,仰视着礼堂顶上的红旗、红旗下的巨幅画像,开始歌唱:“我爱北京……”
“哪里来的野孩子!”一声暴喝突然从礼堂里响起。
猫头扛着扫帚就跑,我在后面撒开腿就逃,好像身后有一个不可名状的怪物张着血盆大口,只要我们稍微慢一点,就会被一口吞下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再也跑不动了,我们才停下来。这时,我们发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扫帚上的红领巾不知什么时候丢了;另一件事是我们的肚子饿得吐噜吐噜叫了。猫头扔掉扫帚,问:“猴头,你饿不?”
我们鼻子这时已经变得异常灵敏,一绺烤饼香味都让它嗅到了。这使我们的肚子更加饿得慌。我说:“我们有钱,我们买烤饼去。”
循着那一绺香味慢慢过去,在街的尾巴头,我们看到烤饼的炉子,新出炉的烤饼和一个胖胖的大婶。
“大婶,六个,一人三个。”我说。
胖大婶夹起三个烤饼,用一张油腻腻的纸包好。正要递给我们,却又想起什么似的,放了下来。“大婶,我们有钱。”猫头说。
胖大婶不说话,向我们伸出了胖胖的手。
“我们真有钱。”我说,“有十块钱,骗你我们是小狗。”
胖大婶依旧不说话,胖胖的手摊开了胖胖的手指,胖胖的手指一曲一伸动了两下。
“就放在大枫树的树洞里。”猫头说:“昨天我们还数过,十块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要不这样,大婶,”我说,“我们把……把书包押在你这里。明天,最迟后天,我们就拿钱来换书包。不拿钱来,你就不给我们书包。”
大婶点了点头,给了我们烤饼;又摆了摆手,没有要我们的书包。——这个哑巴大婶!
我们边吃烤饼,边往前走;斜阳把我们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出了镇子,烤饼已经干净、彻底、全部填进了我们的肚子。肚子饱了,我们又有了交谈的兴趣。
“幸亏遇到哑巴大婶。”猫头说。
“我没讲错吧,只要我们有钱,放在存钱罐和放在身上是一样的,都是有钱。”我说。
“今天,我们怕是到不了韶山了?”猫头说。
这个问题让我们一时沉默下来,闷闷不乐。我们扯一把路边的树叶,揉一揉,嗅一嗅,扔了;又扯一把树叶,揉一揉,嗅一嗅,又扔了……我们的脚步就像渐渐降临的暮色,越来越沉。
不知在抓第几把树叶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拱形的大门,门上白底黑字的招牌,招牌上方方方正正的几个汉字;我凑近一看,念了出来:“石子街中学。”
“石子街中学!”我又念了一遍,双手抓住猫头,激动地说,“石子街中学!我们到石子街中学了!”
“怎么啦?”猫头不解地望着我,一脸傻相。
“刚才在礼堂的时候,我好像看到‘石子街’几个字,还不敢相信这就是石子街了。”我滔滔地说,“到了石子街就好了!”
猫头一脸迷糊地看着我,没有说话。
“你真是个木脑壳!”我继续说:“你想想看,满叔在哪里读的书?石子街中学!满叔在哪里出的发?石子街中学!还不明白吗?”
“猴头,你莫绕弯子……”
“你还记得满叔是怎么说的不?带队老师手一挥——”我有意把“带队老师”几个字重复一遍,“带—队—老—师—!我们找到了石子街中学,还愁找不到带队老师;找到了带队老师,还愁到不了韶山,到不了北京,到不了天安门!”
“还等什么?猴头,快去找带队老师呀!”猫头边说边跑,早已冲进了拱形校门。
几个老师接待了我们,先让我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大半天,然后低声地咬了一会耳朵,互相点了点头;一个戴眼镜的、与满叔年纪差不多的女老师说:“孩子,你们稍等等,我给你们请校长去。”
“不是校长,是带队老师!”
“是的,我这就去请带队老师来!”女老师抿着嘴微微笑了笑。
不久,一个穿着蓝色中山装、表袋上插着一支自来水笔的中年男老师来了。他冲我们笑了笑,自我介绍说他就是带队老师,然后带着商量的口吻跟我们讲:“孩子们,今天也晚啦。你们先在这里睡一觉,明天我们就去韶山,我亲自带队,好不好?”
“还要去北京!”猫头说。
“还要去天安门!”我说。
“还要坐火车!”我和猫头说。
“好,好,好!”带队老师说一个“好”字,点一下头;最后,很严肃地说,“不过,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谁睡得好,我就带谁去。”
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得特别好,特别香。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我们看到了从门窗中透进来的阳光,然后是穿着中山装的带队老师,然后是我们的奶奶、我爹、猫头的爹,还有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