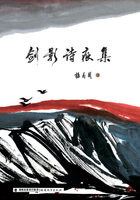午后,在最繁华的市场街登上71号巴士回家去。坐在后头的双人椅上,靠着窗户看街景。同座的黑人下车后,一位白人姑娘趋近,要坐下来,但迟疑着,对我轻声说:“对不起。”我低头一看,是我的夹克的下摆搁在座位上,稍稍越界,她坐下后可能压着,要我把它提起来。我马上回应一句抱歉,照办了。她款款就座。我转头看她一眼,不满20岁,清秀,瘦削,新潮。脸上浓妆,蓝口红加蓝眼影,假睫毛尤其触目,比平常的长了一倍,活像超大的雨蓬。她并无侵略性,文静地坐着,破出气派来的牛仔裤,脱线的裤腿下,露出趾甲涂上彩绘的纤足。我无意于吊膀子,只悠闲地看风景。
“喂,你这呼啦圈好漂亮!”坐在过道另一边的白人青年男子发话了。邻座嫣然一笑,把放在肩膀外侧的彩色呼啦圈拿起来,递给他,男子一手握圈,一手在圈的内侧移动,转圈,笨拙得很,但得意非凡。我纳闷,他的白皮肤干吗变成烟垢般黑?再看他的脸,也黑不溜秋的,胡子兴许今天早上出门前刮过,又长出少许。从下巴到颈项,刻满莫名其妙的黑刺青,和胡子呼应着,予人至少一年没洗澡的印象。可是邻座毫不介意,和他聊得满热络。
“看我。”姑娘要回呼啦圈,用右手一旋,转起来。男子连声叫好。然后,姑娘把呼啦圈压一下,把它变为阿拉伯数字8,再上下并拢,圈小了一倍,她拿在左手,右手在手机上发短信。嘴巴没闲着,和刺青男子说闲话。男子的幽默感终于打动芳心,她把手机关上,视线正对微笑着的男子。男子告诉她,他半年前从亚利桑那州迁来这里,一路坐“灰狗”巴士,其间卖几个关子,镶进笑料,逗得她咯咯地笑。
男子的同座下车,姑娘马上迁移,坐在他身边。他兴致勃勃地打开放在脚下的背囊,掏出一盒不锈钢的首饰,一件件地给姑娘看,边作解释。原来,卖首饰是他的职业,不过并非一般的摊贩,是从特定的非主流首饰设计师那里进的货,再兜卖给品味特别的顾客。我远远看,那些耳环、坠子、胸针、项链,果然奇特。比如,把昆虫标本嵌进透明的橄榄型玻璃容器里,吊在耳下,便颇有非洲土人的野气。姑娘似乎马上成了他的主顾,津津有味地看,比较,试戴。
我下车时,路过这一对,他正在替她戴耳坠,两颗青春的头并在一起。外面是旧金山最寒冷的夏天,公园里的柠檬桉抖索在风卷起的白雾里。
我为这对30分钟前邂逅的男女预划将来。他们可能在下车后分手,各自回归固有生活的轨道;男子可能以“我家里还有许多特别的首饰”为诱饵,请姑娘到他那凌乱简陋的寓所去。若然,往下,可能成就一夜情,也可能成就一月情、一年情,乃至成为情侣,夫妻。青春,意味着前路有众多的可能在等待。
我默默地祝福他们。为了他们给了我对人世的信心。我所目击的,是在人仍旧可以信任陌生人的社会,两位素昧平生者最初的交往,毫无预设条件,任关系自然随意地流动,流到哪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