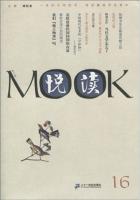在一幅挂在墙上的大地图前,他久久地细细地看着,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
那只是一幅普通的区县地图。我很好奇,走上前问:“您……这是在记什么?”他说:“你看,这上面的地名多有意思!”顺他所指,一连串的地名掠过我的眼帘—罗汉石、望马台、牛角峪、熊耳寨、鱼子山、黑水湾、白云寺……
那是1975年的初春,北京市丰台区“业余文学创作组”的20余人在组长理由的带领下到平谷、密云去采风。这地图就挂在我们住宿的平谷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里,“他”就是我们的组长—理由。当时我被好奇心所牵动,也站在墙边看了许久。看着看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些铅印的字忽然活了起来,开始向外边跳,后来我感觉它们似乎在跟我打招呼,并且想告诉我些什么。我明白了,这就像我从前读的书一样,当你沉浸进去的时候,书中的人物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哭,笑,和你说话。于是我也掏出了笔记本。
理由又说,不仅要留心村名、山名、水名,许多花草树木名和人的名字都很有意思。此后,我的笔记本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地名—秋花峪、山楂峪、鹿角河、望山青、鸡鸣村、柳林水、乌龙铺、白马滩、黑山寺、葫芦溪、西流水;也有花草树木的名—三色堇、鹤望兰、变叶木、仙客来;还有人的姓名—边江涛、金加纳、夏别士、穆加宽、鲁山木、贯云石、柴家燕……
我发觉,只要你去感知,这形形色色的名字,都有灵气,都会让你产生联想或者形成某种形象,甚至会引发你的写作欲望。
一
36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在挤满森林般的水泥建筑的大都市里穿行,或是在各种人事之海的旋涡中沉浮,或是在灯下伏案之余,我的脑际经常会闪现出那张写满了山水村庄名字的地图。这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人,我应该称为“师友”的理由。并非因为他是早已享誉文坛的报告文学作家,而是在那个过去了的特殊年代,我曾是以他为组长的“丰台区业余文学创作组”中的一员。现今忆想起来,才发现当年的那个“小天地”就是我扬起希望风帆并准备起航的港湾,是一个奇特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甚至是隔离在社会之外的“世外桃源”。
相识也是缘。1973年,我从企业基层到学校曾经历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曲折过程,确定到丰台的这个学校也纯属偶然。到学校,结识了与我志趣相投的夏有志的老师;1974年,他介绍我参加了丰台区业余文学创作组。事后想,正是这一系列的戏剧性的曲折和偶然的契机,使我错过了在城区学校任教的机会而在丰台报到,尔后又奇遇到区教育局要人的第十八中学的副校长;这一连串的“巧合”,似乎就是为我此后结识理由及在“文革”结束后被曾经下放到丰台文化馆的老编辑顾行引荐到报社当副刊文学编辑所做的铺垫。
当年的区文化馆坐落在丰台镇一个不甚标准的平房院里。走进朝西的院门,眼见一个空荡荡的大院,其北、东、南各建一排砖砌平房。文化馆负责人的办公室在北面,南屋是美术组,东南角是尘封的图书馆,文学组的办公室在东边的那排房子内。理由的那间很小,里边摆放着两张桌子一张单人床,当是办公室兼宿舍。他那时36岁,按现在的说法还在“青年”的行列,顶多称作“大龄青年”。他不仅个头比较高,而且身材匀称,白净脸,眉清目秀,气质不凡,称得上“美男子”。乍见面,由于他话不多,便会给人一种清高感;但相熟之后会感觉他待人真诚,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温和,那“清高”也就变成了“儒雅”。
从当时右安门内的家或从永定门外大红门附近的学校到丰台镇,有好长一段距离,但我每次骑自行车到文化馆去参加业余文学创作组的活动,都像乡下人去赶集一般欢喜。进了文学组的屋,如同到了“娘家”,客气话不用说,文学组的于公介忙前忙后地搬椅子倒水。我顾不上擦汗喝水,刚一落座就急着从书包里掏习作稿让理由看。如果赶上其他作者也来文化馆,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说自己的写作的情况,或者聊社会上的一些见闻。关上门就是一家人,没什么特别的顾忌,好像风行了多年的“口诛笔伐”“大批判”和“打小报告”并不存在。天气好的时候,在文化馆的院子里摆上乒乓球台子,理由就会一显身手。有一天,我听见南屋里传出了手风琴的声音,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理由在拉琴,这才知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文学组开始活动了,于公介就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室去,让理由给我们讲关于小说创作的事情。
平时话语并不多的理由,谈起小说的话题却是滔滔不绝。他说中国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多以农村题材为主。最著名的小说流派有:“山西派”,也叫“山药蛋派”,代表作家有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等;“陕西派”,代表作家为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他还说近来陕西有个陈忠实,看来很具潜力。这个被理由称为很具潜力的“陈忠实”,就是在二十多年以后以《白鹿原》闻名的陈忠实。理由慧眼独具,由此可见。
理由说,“白洋淀派”,以孙犁为代表;此外还有个被称为“白洋淀派”支派的“运河滩派”,代表作家有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等。“河北派”,以浩然为代表。河南有个李准,大概是因为后继乏人,因此也被称为“绝户派”。上海虽然有写工业题材的胡万春等,但没有形成“流派”。
理由非常赞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他说这篇小说把两个人物各自独立的故事交切在一起,使作品产生了新的意义。他欣赏的短篇小说还有茹志鹃的《百合花》。他说,把《百合花》放在世界短篇小说之林,一点也不逊色。他说小说的结构问题是文学写作者必须考虑的事情,浩然及河北作家的短篇小说常采用“折信封式结构”。所谓“折信封”,就是一张白纸,四边向里折,形成一个信封;这类小说结构好比用纸折信封,故事的首尾向里折,使小说从一开始就进入或靠近事件中心。这样的小说,既容易吸引读者,又节省笔墨。他说马烽的短篇《我的第一个上级》,采用的组织方式为“零起式”。这是从不认识写起,人物概念是“零”。从“零”开始,表面的印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作家欧·亨利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称号,其小说的结尾大多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警察与赞美诗》《最后的藤叶》等,形成了著名的“欧·亨利式结尾”。
理由多次把我们业余创作组的人集合到一起,关在屋子里让每个人谈自己的写作计划,或者讲小说构思,然后由大家评点、讨论。讲短篇小说构思时候,理由要求我们最好能用几句话来表述,时间以不超过5分钟为好。这似乎是个难题,我们多数人以为自己的一个好的构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不清楚,用几句话概括不出来;于是常常罗里罗嗦地说个没完,最后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理由说,好的或比较成熟的构思,也许就是一两句话的事情。它或者是一个特别的细节,或者是一组人物关系,或者是一句带有哲理意味的话,或者是带有生活智慧的简单故事情节。短篇小说的“构思”,要的是一个比较精彩、微妙的“核儿”。说得越多,越说明你并没有理清思路,构思还不成熟。他说,表面的热闹,不一定能够写成一篇小说;简单的几句话,很可能就会发展一篇精彩的小说作品。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似乎有理,但又说不清楚;直到多年以后我当了小说编辑,才真正悟出其中的门道。那时常有一些作者找到编辑部谈想法,说构思,问他讲的故事能不能构成一篇小说。用理由教的方法,从几句话中我就能感觉到一个故事或一个事件是否具有构成小说的元素。我也同样会告诉准备写小说的作者,讲故事梗概一定要简短,只说出一个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核儿”来就行。当然,有了一个好的构思只是一篇小说的基础,作品好坏,还需要语言、细节、结构等多种功力的聚合。
理由说,选好了写作题材,有了艺术构思、确定了一个适合的结构,作品成功了一半;但决定小说是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细节”。细节是表现环境,特别是人物性格、心理、经历并通过外貌、行为、语言所反映出来的细微、独特的细部捕捉和描写。没有一两个特别的细节,小说就不会精彩。理由说,故事好编,细节难找。我们在座的人都会随便讲几个故事,但说出一个有意思或很微妙的细节,可能很难。有了这样的细节,写起小说就会顺畅得多。
理由的这些话,使我联想起地图上的小村庄。那也是一个“细节”,一个体现了理由注重观察、捕捉生活的细节和勤于积累、勤于笔下的“细节”。在为我们讲小说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社会的政治“细节”和个人得失的“细节”—当时的政治环境波涌诡谲,“文革”还在进行中。且不说那些昔日曾被社会尊崇的作家、艺术家和老一代文艺界领导的命运吧;眼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利剑,依然悬在头上啊!被“文化革命旗手”江青所推崇的“样板戏”的“三突出”规律,是当时所有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规则;不遵循它的规则,就会被视为阶级敌对行为……理由所讲的小说创作艺术技巧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作,肯定不合时宜,也肯定违背上边规定下来的创作规则。给讲课的理由上个“纲”、扣个“帽子”,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多年以后,他在《文学这个灰姑娘》一文中写道:“说也奇怪,在这样令人沮丧的情形下自己仍然忍不住要动笔……其间曾几次要折断钢笔,发誓赌咒要洗手不干,决不再受这份洋罪,招惹这份闲气。隔了几天,清早睁开眼睛,又身不由己地趴在桌边,翻翻书,愣愣神,那只手又在划拉着一点儿东西……”
写东西如此,带“文学组”又何不是如此?为了提高大家的文学理论素养,理由还特意将刚刚解放了的大学文学系教师请到丰台讲课;为了开阔视野,他几次带我们到其他区县去参观、访问,交流文学创作经验。为了使业余作者有一个能够发表习作的园地,他与文化馆的同志一道向区里申办了内部刊物,并定名为《丰收》。
听课、讨论、参观、访问,最终还得动笔去写。写出了初稿,我们就交给理由看。理由拿了一摞稿子,找个僻静的地方去修改。我的短篇小说习作《公社新歌》,就是经理由修改、加工之后发表在《丰收》上的。1976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前身)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瑞雪纷飞》,将它收入其中。小说集里的作品,还包括理由的《大路上》(原发表于《北京文艺》1976年1月号)及于公介的《新顾问》。
1976年10月上旬,抓捕“四人帮”的消息开始在社会上传播。我对理由说起胡同里的小孩子们在暗中传说这一消息时相互“咬耳朵”的事情,他当即兴奋地说这是个好细节,有了这个细节,一篇小说就成立了。在理由的启发下,我写了短篇小说《彩色的河流》,经理由修改后发表在《丰收》上。曾有消息说,《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准备选发我的这一小说;虽然最终被放弃了,但理由对细节的捕捉和把握让我非常钦佩。
二
理由说,他此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漫无目的,沉浸其中。他也喜欢体育,那是“为了平衡读书导致的疲惫”。如果不是看书看得头晕眼花,他宁愿埋头不停地看下去。
他的“自觉读书”,是从小学三四年级时开始的。那时候是打基础的阶段,他背诵的是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上了中学,自由度也大了,得天独厚的是他的家离北京图书馆很近。北海旁门的附近,宫殿式建筑,红墙绿瓦,木地板铺陈,真乃一座“精神殿堂”。由于他经常去借书,图书馆的管理员终于注意到这个不大的孩子。他于是有了一种“优惠”,可以把书借回家去,而且一次能抱回一大摞。他一头扎进书海,古希腊神话、传奇小说、俄罗斯文学、发明家传记,都是他徜徉许久的江湖。
书海无涯,读书注定是他永远的嗜好,但在调剂与平衡的娱乐活动中,他接触了当时被称为“国防体育”的项目。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对无线电和航空模型产生浓烈兴趣。他还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自编小话剧,担任导演,投入校园内的各种文艺活动,由此被选入学生会,并担任文艺部长。初中毕业时因成绩优异,他被保送到著名的北京四中读高中。
那时候,他并没有幻想自己成为一名作家,他做的是高远天空上的“蓝色的梦”—1955年,还没等高中毕业他就被国家体委调去接受培训,其后担任航空模型教练;两年以后,他参与筹办北京市少年科技馆。在那里,他把“蓝天梦”,化作了科普文字,并以“李由”“李尤”“礼尤”“理由”署名,刊登在《少年科技之友》《少年科技爱好者》《中学生》《北京日报》等报刊杂志上。
1959年,他写了两首长诗—是为少先队员庆祝新中国国庆十周年集会时用的朗诵诗。这是他最初的“纯文学”创作冲动,也是他童心和爱心的展示。在那一刻,内心深处的文学萌动,开始向他召唤。我们知道,许多作家的文学尝试都起于少年时代或青年时代,这种尝试如同熹微晨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虽然并不强烈耀眼,但却预示了后来的云蒸霞蔚。
这一年,也是他人生重要转折点之一。蓝色飞天梦还没做完,他就被下放到京郊门头沟区斋堂镇的一个村庄,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农村劳动和生活的艰辛。当飞行的翅膀贴靠着大地时,他在焦虑中也得到了风霜雨雪的锤炼;然而现实的人生并没有使他失望——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当教练的日子,特别是没有忘记他教过的孩子们。1960年,当他写的科普小册子《纸模型飞机》得到出版时,他感到了欣慰,还有几分说不出的喜悦。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是他多年爱好、教学实践经验的结晶啊!他的梦,似乎还没有做完。
但那是另一个梦,在匍匐大地时的潜意识中编织着。那冒着袅袅炊烟的村庄,那被耕耘着的土地,那辛勤、善良和淳朴的老乡,在他的身心脑海里绘成了一幅乡土风俗画。即使是远离那里,也挥之不去,甚至愈发清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充裕的时间使他产生了从书本上寻找乡野图画的念想。他重新走进书海,开始了他读书的“第二次浪潮”。这一次,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中国建国后出版的我国当代乡土作家的作品。在《文学这个灰姑娘》一文中,他用“文学语言”说起了他所读小说作品的书目:“我佩服作家们的手笔,作品中的娓娓叙述,有时像山间小溪似的委婉动听,有时像大海的波涛一般汹涌激荡,至今犹如在耳边萦绕。倾听长长的流水觉得陶真养性,面对一束纯洁的百合花禁不住潸然泪下。牵来两匹瘦马,骑上去神游中原。徜徉在白洋淀边,眼前展开一幅幅优美的水彩画。忽入风雪之夜,又遇乡下奇人……”这其中,暗指了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茹志鹃的《百合花》、李准的《两匹瘦马》,孙犁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选集《白洋淀纪事》、王纹石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和欧阳山的短篇小说《乡下奇人》。他在该文中写道:“几年当中,我认真拜读过的短篇小说约摸有数百篇吧,大都随手做过笔记。”文学作品就是他的精神食粮,他说:“生活虽然处于极度的困难状态,但……文学作品留给我的,是美的语言,美的结构,美的个性。”
1967年,他和许多人的命运一样,先是下放到昌平沙河“五七”干校,不久又下放到丰台农村插队。
一到那里,就赶上了“龙口夺粮”的麦收。起早贪黑和洒汗如雨自不必说,但一个月的麦收日子刚过,当地不知从哪儿听到“此人擅长写作”的传闻,他被调到公社去写简报和总结材料,名声传导区里,于是他又被调到区里的宣传部。
又是几个寒来暑往。他面临一次选择的机会—或留在“区革委会”接茬写材料,或到区文化馆去。他先到区文化馆去看了看,一看就不想走了,因为他发现文化馆里有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图书馆里封藏着许多外人不能看到的图书,馆里人自有近水楼台之便。他暗暗欣喜,决定当即就留下。从那以后,没事的时候他就一头扎进图书的海洋,开始了“绿舟之旅”。这一次,是他读书的“第三次浪潮”。他写道:“穿过一条僻静的小巷,打开一把生锈的旧锁,眼前出现一座劫后幸存的黄金屋,装满了古今中外的颜如玉,不由人不再一次坠入情网!那些书,有的久违重逢,有的邂逅相遇。金发的麦琪、高贵的羊脂球、愚蠢的法尼尼、不值钱的宝贝儿、纯洁的珍妮、悲惨的安娜……还有那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这又是他所读小说篇目的散文化或童话的示意—暗含的作品有欧·亨利的短篇名作《麦琪的礼物》、莫泊桑的中篇《羊脂球》、司汤达的短篇《法尼娜·法尼尼》、契诃夫的短篇《宝贝儿》、德莱塞的长篇《珍妮姑娘》、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安娜·卡列尼娜》、茨威格的短篇《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大量欧美经典小说,都成为他的黄金屋中的盛宴佳肴。一些小说,他会读上好几遍—从整体艺术欣赏,到结构解剖,从语言品味,到人物关系的勾连,都要深究细探。
当年的理由,很喜欢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所写的关于文学创作技巧及作家劳动、写作习惯的《金蔷薇》。这部书,也曾强烈地吸引过我。
理由说,他就是一个“读书人”。近些年,他读的大多是有关美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书籍。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谈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哲学著作,现代分析美学,中国传统国学等古今中外名著,摆满了他家中的六层书架。
读书的习惯,早已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如今只不过是“涛声依旧”罢了。理由曾写过一首七言小诗戏言自己对书的痴迷:
文章何来憎命达,胸中有书气自华,
平生只遂逍遥愿,三分问事七分暇。
那“七分暇”,想是用来“泡书”了。
三
我原本以为,在适当的社会气候条件下理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这不仅仅因为他为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小说的事情,而且因为我首先看到了他于1973年年初发表的短篇小说《山丹花》。
这篇小说写的主人公是一位淳朴善良农村大嫂,她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图解式的人为编造人物。当我们了解了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是从作者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理由说,“小说主人公的原形是我曾经在门头沟下放劳动时的房东大娘。从我住进她家第一天起,她就把我当做她的孙子看待。”在理由被派去背负几十公斤的水泥标桩上山时,大娘怕他有什么闪失,一天都吃不下饭,几次去村口张望,眼睛都哭得红红的……其实在任何社会环境中,即使是非常严酷的环境中,民间都会有美丽和闪光的东西存在,既包括爱情、友情、亲情,也包括质朴、善良、关爱他人的人性美。立足或体现了人性美的作品,具有我们可以认定的重要标志。
特殊而严酷的社会环境及为“文革”政治服务的束缚,使那时的“文学作品”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山丹花》却是一个例外。在近年编辑出版的《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纪念的“典藏本”短篇小说卷中,《山丹花》的收录,应该就是一个证明。
理由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说起他在《北京新文艺》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他一直心怀感念。他忘不了当年坐落在西长安街文化局大院里那幢编辑部所在的房子,更忘不了处理他稿件的“老编辑”周雁如。他说,他是“怀着对编辑部神秘的敬畏,也有点儿像进考场前的紧张,更多的则是忐忑”的心情迈进编辑部的门槛的。几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周雁如大姐的音容笑貌。这可以理解,许多写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触。1972年,当我的第一篇似小说又非小说的幼稚小文发表在《北京日报》“工农兵文艺”副刊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至今难忘;对于从来稿堆里选发这一稿件的编辑李凤祥,我一直视为恩师。因为没有这个第一篇和第一步,我可能不会走上致力于文学的路。
《山丹花》并不是理由的“处女作”。他的最早发表的“作品”,是十几年前所写的科普读物,几未公开发表的朗诵诗。1973年,因为写了报告文学《老场长》和《两笔账》,他被借调到当时在崇文门外兴隆街的北京人民出版社,去编题名为《坚定的脚步》的报告文学集。
结识了他所敬佩的周雁如和发表了短篇小说《山丹花》以后,理由与《北京新文艺》和其后的《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年少时便喜爱唐宋词,在此时转化为一种文字的功夫,并表现在他陆续发表的小说作品的三字题名上—《心里美》《大路上》《旱天雷》《清明雨》《坝上石》《白天鹅》《青杉湿》《子爵号》《纸半张》。
但理由却是以报告文学而成名。
理由从写小说到基本上专工报告文学,起因也是出于《北京文学》的资深编辑周雁如。那时他已经调到《光明日报》,周雁如说:“你笔头快,又能跑,去写写报告文学吧。”恭敬不如从命,他果然掉转写作方向。1976年底,他以报告文学《心血的浇注》初露头角。1977年9月,发表在《北京文艺》9月号的记述科学家童第周业绩的报告文学《让我们活得更年轻》使他显示了不凡的手笔;1978年初,记述数学家华罗庚传奇人生的报告文学《高山与平原》,引起中国文坛的注目。如果说理由抛开小说创作转向报告文学写作的初始是出于对周雁如的感恩和尊敬的话,那么他后来奔跑在报告文学之苑已经成为兴趣和自觉。
使他一举成名天下闻的报告文学作品,是记述击剑运动员栾菊杰运动生涯和拼搏精神的《扬眉剑出鞘》。
以这样的诗句为作品的标题,在当时可谓不同凡响,因为它出自1976年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把酒祭豪杰,扬眉剑出鞘!”在“四人帮”的追查令中,它被列为第一号“反动诗”。而发表这一报告文学作品的时候,以悼念周总理为契机的“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得到平反。理由说,当年他写这篇作品时,曾想过许多题目,如:《情理之中的意外》《青春在剑锋上闪光》《倚天抽宝剑》《银剑凝霞光》等。但当《扬眉剑出鞘》这个题目突然冒出来时,他感到了一种特殊的快感。他当然知道这首诗的背景,却毅然抛弃了其他的文题。此文题所寄托的言外之意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曾有人坚决反对;理由认定了它的力度和多意的内涵,执意这个选择。
以《扬眉剑出鞘》为题的报告文学在《人民日报》顺利通过,并于1978年6月11日发表;第二天,也就是6月12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两家中央大报以整版的篇幅相继发表和转载文学作品,在当时可能是破天荒的事情。作品以其主人公的拼搏精神、优异的文笔、独特的结构及与民意相通的标题,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作者理由也由此而名传天下。对于那些慧眼识珠的编辑,理由至今心怀感念。
此后,理由的报告文学作品连连问世—记述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她有多少孩子》,记述著名小麦专家蔡旭教授的《依傍田野的小屋》,记述毛纺织厂女挡车工索桂清的《中年颂》,记述画家袁运生跌宕命运并最体现“小说笔法”的《痴情》,记述人民警察高松龄高超侦察本领的《手眼神通》,记述东风电视机厂厂长黄宗汉拼搏精神和企业家眼光的《希望在人间》,记述植树造林先进人物萧发木感人事迹的《山林狂想曲》,记述1985年5月19日国家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比赛后失利后北京球迷的过激反应及其背后内涵的《倾斜的足球场—5·19之夜》等,给读者带来夏日饮清泉和平地响春雷般的喜悦和震撼。在新时期十年中,他所写的报告文学、散文、随笔、小说,多达百余篇。在1977年至1986年度的四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理由以《扬眉剑出鞘》《中年颂》《希望在人间》《南方大厦》《倾斜的足球场》五篇作品,连续四届获奖。获得这种殊荣的,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应该独属理由。
著名文艺理论家、哲学家泰纳在其名作《艺术哲学》中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但是“精神气候并不产生艺术家;我们先有天才和高手,像先有植物的种子一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的作家帕尔·拉格维斯特说:“作家的任务是要从艺术的观点来阐明他的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表达、透露出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勤奋加才华,融会时代的呼唤和社会精神的需求,应该是造就报告文学作家理由的“理由”。
四
“文革”结束后,在丰台业余文学创作组修炼过的人们开始“出山”,并凭借时代的春风进入创作高潮期。这个群体的成员,渐渐融入“北京作家群”。
我们的组长理由调入《光明日报》后,又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出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香港回归前,他赴港,后从商,近年重返北京文坛。
理由主要著作有:《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报告文学集《扬眉剑出鞘》《痴情》《她有多少孩子》《香港心态录》《倾斜的足球场》《浪迹萍踪》散文集《文学这个灰姑娘》,随笔集《明日酒醒何处》等。
曾下放到丰台区文化馆并在“文学组”工作过的顾行,在粉碎“四人帮”后调回《北京日报》文艺部,后出任复刊的《北京晚报》副总编辑、总编辑。
文化馆“文学组”的另一成员于公介,调到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任编导。
毛志成从丰台区的中学调到大学,成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还以文学多面手和快手而闻名,作品不仅有短、中、长篇小说,还有短诗和长诗问世,后来又以杂文、随笔闻名。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有《乌沙巷春秋》、《杯中异曲》等,杂文代表作有《中国需要权力学》《三国演义五题》等,随笔代表作为《学会沉默》《三世与三界》等。
曾在丰台区中学教书的肖复兴,先后在《新体育》当编辑、任《小说选刊》副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海河边的一间小屋》,获得1983年至1984年间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并著有长篇小说《早恋》及几十部散文和中短篇小说集。他在《重逢的代价,是青春》一文中写道:他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业余时间“参加了丰台区文化馆组织的一个文学小组,组长是后来写报告文学出名的作家理由先生”,“在这个文学小组里,我写了一篇小说《遗忘荒原的红苹果》。”这一作品,写一个印尼归侨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离开中国,后又回国与北大荒恋人重逢的故事。“文革”后,肖复兴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恰逢考题为《重逢》,于是那早已写过的小说便得心应手地进入了他的试卷。
曾与我同校任教的夏有志,以儿童文学进入文坛,后任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编剧,写有长篇儿童小说《三个和一个》《普来维梯彻公司》等几十部儿童文学作品。
宗介华从丰台区的小学调文化部少儿司,并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写有《山猴子》等几十余部儿童文学作品。
受理由教诲很多的我本人,从丰台出来以后,曾在多家报刊任文学编辑,不仅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小说,还出版了文学理论专著《小说结构学》。这一专著,源起于理由当年所讲小说结构的启示。
后来调到报社当编辑、记者或成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的有:王槐一、苏殿远、李保田、孙凤林、赵敬强、秦润华、赵秀云、冯维海、李国琴等。他们都有很多作品问世。
当年参加丰台业余文学创作组活动的骨干成员还有:陈富明、张维安、安伟邦、田学茹、赵文涛、邹红军、张瑞征、郑雍庭、赵美琳、白玉川、何振英等。在丰台师范任教的张维安,曾以文学批评崭露头角,可惜英年早逝。原在红星农场的陈富明调到区文化馆,主持文学组的工作。当年年龄最小的女中专生田学茹,后来成为优秀中学教师;其他成员,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并时有新作发表。
源出于丰台区业余文学创作组的“丰台帮”或“丰台作家群”,并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它的成员,各有其长,作品的笔法和风格也不尽相同,现已星散在北京的四面八方。但我依然不会忘记这个群体,不会忘记当年的带头人—理由。正是他,他的文学素养、创作实践及乐于助人的品质,为许多人的文学发展打下了基础。他的文学活动和他倾注心血所成就的群体,不仅应写入丰台的史志,同时也是研究“北京作家群”形成、发展的史料之一。
这就是理由—成就了一个“作家群”的理由,驰名于报告文学艺苑的理由。我感激他,不仅仅是他的扶植和文学的启示。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当我只囿于家庭和以小小的朋友圈子为避风港湾的时候,当我在苦闷、惶惑、彷徨、失去了追求的目标、没有了梦想、希望和不知未来在哪里的时候,是这个“业余文学创作组”给我带来了朦胧的希望,是它的“带头人”理由使我重新有了梦想和寄托而没有消沉,并使我在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中没有让心灵扭曲。
地图上的小村庄啊,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们在那个梦一般的港湾里乘上青春绿色的小舟,准备解缆扬帆——那些个在丰台业余文学创作组活动的日子,那一次次听理由讲小说的情境,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越来越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