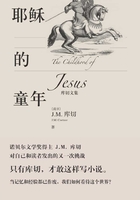离开恺撒后,佩特罗尼乌斯让人把他抬回他在卡利那的家。由于三面有花园环绕,正面还有一个西西里亚小广场,那栋房子避开了火灾。这一次的好运不过是在幸运女神福耳图那对他特别眷顾的名声上又添了一笔罢了。其他的达官贵人都称他是福耳图那的头生子。经过恺撒近期的友好举动,这名声传扬得尤其响亮,并且加剧了其他尼禄近臣们的嫉妒,他们在大火灾中失去的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现在,这个福耳图那的幸运子有了回味他那大家眼中的母亲是多么变化无常的理由;她似乎和吞食掉自己子女的原始创造神克洛诺斯更相像。
“若是我的房子,”他在心中暗想,“和我所有的宝石,艺术品,伊特鲁里亚花瓶,亚历山大玻璃器皿和科林斯铜器一起被烧毁了,尼禄也许会饶了我。以波吕克斯之名起誓,想一想吧,此时此刻,想不想做禁卫军长官完全取决于我。我可以宣布提盖里努斯为纵火犯,实际上他也是,我给他穿上‘耻辱衣’,把他丢给百姓,救下基督徒并重建罗马。谁知道从那以后正直的人会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呢?即使不为别的,我也应该为了维尼奇乌斯那么做。若是这项工作太过费力,我可以把活交给他,让他做禁卫军长官。尼禄不会多事地反对。就让维尼奇乌斯在那之后给所有的禁卫军施洗吧,若是他愿意的话,让他也给恺撒施洗吧。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我有什么要在乎的呢?事实上,一个虔诚、慈悲和有道德的尼禄也许会更有意思些。”
这个念头太有意思了,有意思得他开始微笑,不过他的心思很快转进了另一条通道。突然之间,他好像是依旧在安提乌姆,依旧和保罗争辩着基督教教义,好像那个基督的使者正在以理服人。
“你们管我们叫生活的敌人。”他听到那位传教者说。“但是佩特罗尼乌斯,假使恺撒是一个基督徒,你们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安全,更安定吗?”
“以卡斯托尔之名发誓!”他自己对自己起誓道,“不管他们在这里杀掉了多少基督徒,保罗很快就会补齐这些人数,因为倘若世界无法在恶和罪之上存在,那么他就赢了辩论。但若是世界能存在于恶和罪之上呢?社会败类必然成为了人上人。我在生活中学到了很多,可我却并没有学会怎么做一个苟且偷生的无赖或者大恶棍,那也正是我即将被迫割腕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结局总会是如此,倘若不是这么精确的方式,那就是其他类似的方式,我会失去尤尼斯,当然了,还有我的米列内花瓶,但是尤尼斯是自由人,花瓶也会随我入土,不管发生什么,红铜胡子都不会把它捞到手!我为维尼奇乌斯感到遗憾。他应该得到比他即将得到的更好下场。是啊,最后的几年将会比之前少一些无聊,但是大多数人卑劣至极,不值得去哀掉生命的丧失。一个知道如何生的人该知道如何死。而且即使我是一个达官贵人,我也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更加自由。”
他耸了耸肩,收敛心神想了一会儿他的同僚们。在宫里,他们以为他害怕得两股战战,头发全都在头顶上竖了起来,然而,他却在这里,在回家的路上。他要用散发紫萝兰香气的水洗浴,要让他宠爱的金发尤尼斯为他按摩,然后,在晚饭之后,和她一起聆听嗓音甜美的歌手合唱安忒弥厄斯献给阿波罗的颂歌。
他冥思回想,“我亲口说过,没有必要对死神做任何考虑,因为不管有没有我们的帮助,她都会来拜访我们。”
他想,若是有极乐世界这么个东西,极乐世界里又有徜徉漫步的死者亡魂,那真是太奇妙了。“尤尼斯将及时与我汇合,我们将共同在长着常春花的乐土中漫游。那样的结合定然会比这个世界里好得多。我也会找到比这个世界里好得多的交际圈。这个世界的都是些什么人呀!滑稽演员,小丑,低劣的乡村杂耍艺人,没有丝毫品位、素养、斯文和文化,流着涎水的农民,十个品位裁判官也不能点化那些蒙昧无知的‘特里马奇奥’。以佩耳塞福涅之名发誓!我受够他们了!”
他突然注意到了那些人和他之间的鸿沟。当然了,他对他们知之甚深。他早就明白该如何去评判他们。而现在,他们似乎远远落在了下乘,并且愈发鄙劣无耻了。他想:“我真的受够了!”
但是,接着,他关注起自己的情况来,他的全部敏锐感和经验告诉他,他的厄运大概会被延迟上一阵子。尼禄无法抵制诱惑地说出了一些关于友谊和宽恕的高调言论,而那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他将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借口,而那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首先他会用基督徒来制造出一场奇观。”佩特罗尼乌斯总结道。“只有到了那时他才会扭转心思到我身上。”若是如此,那就没有必要忧心忡忡,没有必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维尼奇乌斯面临的危险更加紧迫。
他决定救救那个年轻人,于是,在余下的回家路途上,他把心思转向维尼奇乌斯。
奴隶们踩着灵活的步伐,扛着他的肩舆,穿过荒凉灰败的卡利那地界,行走在烧焦的瓦砾和烟囱架子间,然而他却命令他们全速奔跑,尽快把他带回家。维尼奇乌斯的家在火灾中被毁,他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好在他呆在家中。
“你今天见过吕基娅了吗?”佩特罗尼乌斯一见到他就问。
“我刚从她那里回来。”
“注意听我将要说出的话,不要浪费时间提问题。我刚刚从恺撒的宫殿回来。他们决定把火焚罗马怪罪到基督徒的头上。那意味着赶尽杀绝;搜捕从现在起任何时候都会开始。带着吕基娅跑吧。往北去,翻过阿尔卑斯山,或者去阿非利加,去哪里无所谓,只要带她离开就行。并且要抓紧!从帕拉丁宫去往台伯河对岸区可比从这里走要近得多。”
维尼奇乌斯的军人习气十足,绝不会问多余的问题。他仔仔细细地听着,全神贯注的脸庞显得紧张和不安,却又平静得没有惧色。显然,他对危险的第一反应是对抗。
“我走了。”他利落地说道。
“还有一句话。带上金子,带上武器,带上几个人手。确定他们都是基督徒。如果需要,为她而战,带她离开!”
维尼奇乌斯已经穿过了中庭的门。“还有,派个奴隶给我报信!”佩特罗尼乌斯在他身后喊。
接着,被独自一人留下的他开始在沿着竖立在中庭院墙的圆柱间踱步,思索着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吕基娅和里努斯已回到台伯河对岸区,回到他们在火灾之前所住的地方,因为那栋房子与大部分城区一样幸免于难,而那又是不幸的。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会困难的多。但是由于在帕拉丁宫里没有人确切了解去哪里找他们,维尼奇乌斯一定可以在禁卫军之前到达那里。他又想到,提盖里努斯会想到通过一次大型行动抓住尽可能多的基督徒,所以他会把他的网撒向全罗马,把他的禁卫军化为一支支小分队。
“倘若他们派去追捕她的人不多于十个,”他寻思,“那个吕基亚大个子一个人就可以把他们所有人的脖子给拧断。更别说还有维尼奇乌斯带着武器去支援了。”
这令他觉得好受了些。诚然,用武力与禁卫军对抗无异于和恺撒分庭抗礼。佩特罗尼乌斯也充分意识到,若是维尼奇乌斯跑掉了,逃脱了恺撒的报复,这份罪责很可能会落到他的头上,但是他最不在乎的就是这了。实际上,替尼禄和提盖里努斯把水给搅浑的想法让他高兴和开心。他决定为了这么个大好目标不吝人力和金钱;又由于塔尔苏斯的保罗劝化了他在安提乌姆的大多数奴隶,他能肯定,为了保卫那个基督徒姑娘,他们会豁出命去战斗。
然而,尤尼斯恰在此时悄悄走进了中庭,他所有的思索和担忧都不见了。他忘记了关于恺撒的一切,忘记他自己失了宠。他不再去想那些不名一文,卑劣无耻的达官贵人,不再去想对基督徒们的拘捕,不再去想吕基娅和维尼奇乌斯。他带着一个鉴赏家的赞赏眼神看着尤尼斯,这个鉴赏家的快乐来自于美;他带着一个爱人的赞赏眼神看着他,这个爱人受到了那份美的滋养。她身穿一件被称作“玉衣”的紫色透明衣衫,透过衣衫,她的身躯恍若一支发着微光的浅色玫瑰;她漂亮得如同一位女神。感觉到他的赞赏,全心全意爱着他并且总是渴望着被他触摸的尤尼斯满脸喜色,就仿佛她是个天真的小姑娘,而非他的侍妾。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吗,我的仙女?”他柔声问道。
“老爷。”她把长着金发的脑袋靠向他。“安忒弥厄斯带了他的歌手来,他想知道今天听他们唱歌是不是您的意思。”
“让他等着。他今天晚上要为我们唱歌。想象一下吧!我们被瓦砾和灰土包围着,然而我们却将要听一首赞美阿波罗的颂歌。”
“啊,老爷!”尤尼斯吸了口气。
“过来,尤尼斯。用你的胳膊搂住我,用你的嘴唇亲吻我……你真的爱我吗?”
“我对宙斯的爱也无法比这更多。”她印上他的双唇,在他的怀中颤抖。
“若是我们不得不分开呢?”
她害怕地瞪视他的双眼。“为什么,老爷?怎么分开?”
“别害怕!也许是我被迫要做一次长途旅行也说不定。”
“那么就带上我一起。”
不过佩特罗尼乌斯突然换了一个话题。“告诉我,我们的花园草坪上有没有常春花?”
“所有的草坪和柏树都被火烧得焦黄,香桃木上一片叶子也没了,花园里一派死气沉沉。”
“整个罗马看着也死气沉沉的,不久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块真正的墓地。很快就会有一道针对基督徒的敕令,随同敕令的还有迫害,数以千计的人将被迫害致死。”
“为什么要惩罚他们,老爷?他们都是善良安分的人。”
“这就是原因。”
“那我们去海边吧。老爷您的双眸不喜欢看到血腥。”
“好呀。但是现在我必须洗个澡。过会儿到涂油膏室去给我的双肩涂上油。啊,以阿弗洛狄忒的紧身内衣起誓!你之前看起来从来没这么美过。我要给你建一座贝壳样式的浴室,你会像一颗宝贵的珍珠那样躺在里面……但是待会儿就来,好吗?”
他去沐浴了。一个小时后,他戴着玫瑰花环,眼中浸润着肉欲的欢乐,和尤尼斯坐在一张布满了金碟的餐桌旁。一群打扮成丘比特的小男孩侍奉着他们,他们一边啜饮着水晶酒杯中的葡萄酒,一边听着安忒弥厄斯的歌手们弹奏竖琴和歌唱。他们凭什么要在意那些围绕着他们,在废墟中若隐若现,处处皆是的烟囱架子呢?或者,他们凭什么要在意把罗马的灰土刮到他们别墅周围的阵阵大风呢?他们沉醉在他们自己的幸福里,心中只有把他们的生活变得如同神仙梦境的爱。
颂歌唱至一个段落结尾之前,一个负责中庭事务的奴隶打断了他们。
“老爷·——”他的声音发颤,又含着一丝担忧——“有一个百夫长和一队士兵在门口。他要求见您。”
歌声立刻停顿,竖琴也没了声音。焦虑掠过每一个人的脸上,因为恺撒很少用禁卫军给朋友们送信。他们的光临通常意味着坏消息,正如现在这般情形。只有佩特罗尼乌斯没有显露出任何愁色。
“他们至少可以让我消停地吃完晚饭。”他用一个经常被打扰的人那种厌烦、疲乏的语气说。接着他对那个门房说道,“让他们进来。”
那个奴隶消失在帷幔之后。过了一会儿,一阵军人沉闷厚重的脚步声传了过来,一个身佩武器的百夫长迈着大步走进屋内。佩特罗尼乌斯认识他。他的名字叫安培尔。他全身披挂,头上还戴着一顶头盔。
“恺撒有一封信给您,大人。”说着,他递出了蜡板。
佩特罗尼乌斯伸出白皙的手臂去取蜡板,看了看蜡板后,他将其传给尤尼斯,仿佛那几块蜡板无足轻重般。
“他今晚要朗诵一首出自他的《特洛伊亚特》里的新歌,并且请我去听。”他说。
“我的工作只是送信。”百夫长说。
“很好。那么就不会有回信了。不过,百夫长,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和我们一起歇歇,饮上一杯葡萄酒呢?”
“谢谢您,尊贵的大人。我很乐意为您的身体康泰干上一杯,但是由于还在当值,我不能久留。”
“他们为什么不派个奴隶,反倒让你来做这个信使?”
“我不知道,大人。可能是因为我顺路什么的吧。我在这儿有差事。”
“我明白。”佩特罗尼乌斯点了点头。“你在追捕基督徒。”
“正是如此,大人。”
“逮捕行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几个分队在中午前就去了台伯河对岸区。”
百夫长晃出几滴酒到地上敬了敬战神,然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愿众神令您诸事顺心,我的大人。”他说道。
“杯子拿去吧。”
百夫长敬了个礼,接着出了屋。佩特罗尼乌斯示意安忒弥厄斯继续演奏。竖琴声又一次弹起。他想,看来红铜胡子在耍弄我和维尼奇乌斯。我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他想通过派百夫长来警告我。他们今晚上会盘问安培尔我的反应。
“不,不,你这只残忍无情的猴子,”他轻轻呢喃,自言自语,“你不会从我的回禀中得到多大的乐趣。我知道你不会忘怀你那受到伤害的虚荣心,我知道我没有好下场,但是若是你以为我会哀求您的恩典,用我的双眼巴巴地求你,或者显露出任何害怕和追悔的神情,那么等待你的将是惊讶。”
“恺撒写的是:‘来亦可,不来亦可’,大人,”尤尼斯说,“你会去吗?”
“我身体舒泰,心情愉快,”佩特罗尼乌斯说。“愉快得甚至可以去听他吟诗。我会去,更何况也是因为维尼奇乌斯去不了。”
实际上,在他们用完晚餐,他也做完例行的餐后散步后,他把自己交给了各个巧手的奴隶姑娘们收拾,她们为他梳头,把他托加上的衣褶整理到位。一个小时后,他乘轿去了帕拉丁宫,风采卓然,犹如一位神祗。
天色已晚,这个傍晚温煦而又静谧,月光皎皎,走在他肩舆前面的掌灯奴熄灭了照明的火把。一群群兴奋的,吃廉价葡萄酒吃醉了的人或是在大街上走的摇摇晃晃,或是在废墟间行的磕磕绊绊,他们头戴常春藤和忍冬树枝编成的头冠,手里挥动着从恺撒的花园里折来的香桃木和月桂树的树枝。充足的免费粮食和对盛大的公共比赛的期待取悦了百姓。人群中,有人手舞足蹈,有人唱着有关这个宜人夜晚——这个似乎是为了他们这些神明寻欢作乐而设的夜晚——的情歌和民谣。有好几次,奴隶们不得不叫喊,叫喊着给尊贵的佩特罗尼乌斯的肩舆让路,于是人群散开并向他们最喜爱的贵戚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