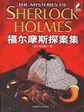尼禄一边弹琴,一边演唱他献给阿弗洛狄忒的颂歌——他亲自作词,亲自编曲的《塞浦路斯女王》。那天他的音喉恰巧状态不错,他感觉他的音乐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涤荡了他们的心灵。这种力量感将他发出的声音转化成了一种更加伟大的东西,使他心中塞满了洋洋得意的敬佩,令他恍若神灵附体。最后,他因情感的彻底释放而面色苍白。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一点不想听到掌声,只是俯身坐在他的齐特琴前,揪着自己的心口。
“我乏了。”他终于说道,猛地站了起来,“我需要空气,我出去时把我的琴弦调好。”
他用一块丝帕裹住喉咙,向坐在角落里的佩特罗尼乌斯和维尼奇乌斯示意。“你们两个跟我来。”他说。“维尼奇乌斯,把你的胳膊给我靠着。我太累了,一点也站不稳。佩特罗尼乌斯,你和我谈谈音乐。”
他们出去,到了外面的宫殿门廊里,里面铺着雪花石膏地板,上面撒着芳香沁脾的藏红花。
“我在这里可以更随意自在地呼吸。”尼禄说。“即使我明白我为你们所弹奏和演唱的这一小段样曲远远不够公开表演的,我还是觉得心中充满了悲伤。等到我把这首曲子带上舞台时,那将是罗马人从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胜利。”
“您可以在这里演出,也可以在罗马和希腊演出”。佩特罗尼乌斯说。“我发自肺腑,出自衷心地敬仰您,圣上。”
“我知道,你才懒得去臆造你没有感觉到的赞美之辞。你和图里乌斯·塞内奇奥一样诚实本分,但是你懂的多得多。说说你对音乐的看法。”
“当我听诗朗诵时,观看你在竞技场上驱使战车时,看见美丽的雕像、庙宇或者图画时,我感觉得到我可以掌握音乐的内涵,感觉得到我的敬仰之情容纳了这些雕像、庙宇或者图画所展现出来的一切。但是,当我听到音乐,尤其是你的音乐时,我的眼前展现出了美和喜悦,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是新的。我追赶它们,品味它们,然而在我消化它们之前又有更多的美和喜悦涌现,就好似海上的波浪一般,一波接着一波,永无止境,永不停歇。所以,我只能这么说,音乐犹如大海。我们立于海岸之上,向着我们面前延伸出去的一望无垠之地看去,但是却永远看不见对岸。”
“啊,你分析得真是深入骨髓!你真是一个鞭辟入里的分析师!”尼禄说。
他们默不作声地沿着走廊走了一些时候,佩特罗尼乌斯在恺撒的一边,维尼奇乌斯在另一边,只有散乱的干藏红花的枝茎在他们的脚下沙沙作响。
“你精准地表达出了我自己的想法。”尼禄最终说道,“所以我才总是说,在罗马,你是惟一能够理解我的人。是的,那是我对音乐的立场。当我弹琴和歌唱时,我见到了在我的帝国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是恺撒!天下是我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而音乐向我展露出新的国度,新的高山和新的大海,向我展露出我从来没有想象到过的新的魅力。连我的思想都无法将它们尽数掌握,我甚至连叫出它们的名目都无法做到,但是我的每个感官都感觉到了它们。我感觉到了众神的存在。我看见了奥林匹斯山,奇怪的风从神乎其神处刮来,将我刮走,透过一层迷雾,我窥见远远的一块明亮的如同日出的广阔地带……我四周的宇宙隆隆颤动。”真切的惊诧感觉使他的声音强烈地颤抖。“我对你说……我,身为神明和皇帝的我,在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微贱得如同一粒尘埃。你能相信吗?”
“相信。”佩特罗尼乌斯说,“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会在他的艺术作品前感觉到渺小。”
“这是一个坦城相待的夜晚。”恺撒对他言道。“所以我像对待朋友那般向你坦露心迹,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事……你是不是曾认为我是笨蛋或者瞎子?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罗马的墙壁上写了什么?以为我不知道他们管我叫弑母犯,杀妻犯,并认为我是一个残忍的怪物,就因为我允许提盖里努斯戕害我的敌人吗?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他们管我叫怪物,我清楚得很!他们几乎已经让我确信我的残忍,残忍到了有时候我自己也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怪物!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残忍的事情并不一定把人变得残忍……啊,没有人知道音乐是如何将我脱胎换骨的。你,我亲爱的朋友,或许也不会相信,当音乐进驻我的内心时,我感到了仿佛孩子在摇篮中被摇晃那样的温柔。我以天上闪烁的星辰向你发誓,我对你说的全是实话。人们不知道我的心中有多少美好,不知道当音乐的门扉打开,并将所有的美好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在心中又发现了多少珍宝。”
佩特罗尼乌斯一丁点儿也不怀疑,此时此刻的尼禄是带着极其恳切的真诚说出这一番言语的。音乐的的确确有着引出他内心被埋葬的最美好部分,那最最美好的部分隐藏在数之不尽的自恋,自我放纵和罪恶的山峦下。
“人们必须像我了解你那样好好地了解你。”佩特罗尼乌斯说。“罗马从来没有能够欣赏你。”
恺撒重重地倚靠着维尼奇乌斯的肩膀,仿佛被严重不公的负重弯了腰。
“提盖里努斯告诉我,他们在元老院里私下说,特尔普努斯和狄奥多鲁斯的齐特琴弹得比我好。就连琴艺他们也不看好我!但是你不说谎。你总是说实话。所以实话告诉我,他们真的和我一样好吗,还是比我更好?”
“差远了。你的指法更柔和,但是却更有力量。在你的指法里,人们听到的是一个艺术家的演奏;而在他们的指法里,人们听到的不过是技巧娴熟的琴师的演奏而已。其实,听到他们的演奏恰恰对理解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了。”
“那么,就让他们活着吧。他们永远不会了解你刚刚为他们做了什么。此外,要是我把他们给杀了,我还不得不另外找人去替代他们。”
“而人们会说你对音乐的爱推动你毁灭了他们。永远不要为了艺术而扼杀艺术,圣上。”
“你和提盖里努斯真是迥然有别!”尼禄说。“但是我是一切事物上的艺术家,你知道,又因为音乐把我带进了我从来不知道的艺术空间,把我领进了我不去统治的境域,并且对我施加了我在普通人中间绝不会发现的威胁,我无法只过俗世的平庸生活。音乐告诉了我,有与众不同的级别的存在,我用众神赐予我的全部力量去寻找它们。我有时候想,为了达到这些新的奥林匹斯高峰,我必须做一些以往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必须跳开寻常人对于善恶的概念,在这两方面超越所有人。我也知道,人们以为我要疯了。但是我不是疯了,我是在寻找!如果我要疯了,那么普通百姓就不必费心,我的急性子也不必让我费心去找我正在寻找的东西了。我寻找,我必须不停地寻找。我知道你明白的,而那就是我之所以必须要比任何人伟大的原因,因为那是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家的唯一途径。”
他将嗓门放低,以至于连维尼奇乌斯都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凑近佩特罗尼乌斯,开始在他的耳际私语。
“那便是我对我的母后和妻子施以极刑的主要原因。”他发出粗嘎地呼吸声。“你知道吗?我想在未知世界的大门前奉上人类所能供奉的最伟大的祭品。我期待在供奉完祭品后发生一些奇遇。我觉得会有一扇门通向某类壮观神秘之所。那要么是了不起地超乎人类的理解,要么便恐怖非常,只要那是不同寻常的,震慑人心的,我便什么也不在乎……但是祭品还不够丰盛。看样子还需要有更多的祭品来叩开那扇玄妙之门……所以,现在就让事情按照它将既定的状态发生吧。”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看见的。你一定会看见的。比你以为的还要快。同时,记住,有两个尼禄,而不是一个尼禄,一个是大家都看见的尼禄,另一个是只有你知晓的艺术家尼禄。如果他像瘟疫那般取人性命,或者像巴库斯那般豪饮狂欢,那是因为他被平常世界里的沉闷、浅薄、平淡无奇所桎梏,他想将这些东西抹杀,像糟粕一样将它们剔除,哪怕那需要用火和铁去做到……啊,等我不在世上了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多么地陈腐、单调、乏味和枯燥哇!没有人,就连你,我亲爱的朋友,你也不了解我是多么货真价实的一个艺术家。还没有了解。然而那正是我为何经受这般磨难,我的灵魂为何像我们眼前这些经受风吹雨打的柏树一般暗沉和孤独。让一个人背负最大的全市和最大的天资是一桩难事。”
“我和你有同感,恺撒。”佩特罗尼乌斯圆滑地说。“大地与海洋,以及天上和水里的所有生灵也都有同感……更不要说像敬仰神诋一样敬仰你的维尼奇乌斯了。”
“我也一直都很喜欢他。”尼禄微笑着摁了摁这个年轻贵族的肩头,“虽然他活跃在战场而非情场上。”
“我倒是认为,他的第一份忠诚献给了阿弗洛狄忒。”佩特罗尼乌斯说。
突然一下子,他决定将他外甥的问题一举解决,并同时解除所有可能威胁他的危险。“他就像爱上了克瑞西达的特洛伊罗斯那样,在爱情中神魂颠倒。请主上恩准他回到罗马,要不然他会害相思病的。那个你赐给他的吕基亚女人质被找到了,你知道,他来安提乌姆时把她交托给了一个叫做里努斯的人照顾,我之前没有提及此事是因为我不想在您创作的过程中,在您于颂歌上下功夫时打扰您的创作,那是优先于一切事务的。实际情况是,维尼奇乌斯本想让她做一个姬妾,但是当她被证明如卢克莱蒂亚一般纯洁无瑕时,维尼奇乌斯因为她的纯洁无瑕爱上了她,并想与她结婚。她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因此,这里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可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叹息,呻吟,相思成疾并奄奄一息,他在等待他的皇帝许可。”
“皇帝不给他的士兵选择妻室。他为什么需要我的许可?”
“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主上,他只是出于对您的敬仰。”
“因而越发要允许他举办婚礼了。我记得,她是个漂亮姑娘,就是屁股太小。波佩娅皇后对我诉苦,说她在御花园里对我们的孩儿下了咒……”
“也许你还记得,正如我对提盖里努斯说的,众神是巫术加害不了的。你记得吧。圣上,他有多么震惊,你喊出“完了”的声音又有多么响,他就像是一个被打得落花流水就差最后一下就完了的角斗士。”
“我记得。”尼禄短暂地点了一下头,他问维尼奇乌斯:“你爱她吗,就像佩特罗尼乌斯说的那样?”
“我爱她,主上!”
“既然如此,我命令你明天返回罗马,立即娶了她,不戴上婚戒不要让我见到你。”
“谢主上!臣感激涕零,铭感五内!”
“啊,让人快乐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恺撒感叹道,大为满足。“我希望一辈子什么都不干就做这个。”
“请再赐我们一个恩典吧,圣上。”佩特罗尼乌斯快速说道。“请当着奥古斯塔的面宣布你的旨意。维尼奇乌斯不敢娶她不待见的人。然而您的一句话将抹去奥古斯塔的疑惑,尤其是在你清楚表明他是在你的直接授意下结婚时。”
“那就这样。”恺撒说,“你和维尼奇乌斯的一切要求我都不会拒绝。”
他转身回到别墅中,另外两人跟随其后,成功的刺激让他们兴奋不已,那个年轻的贵族用尽全部自制力才没让自己感激地扑向佩特罗尼乌斯,因为现在所有的威胁,所有的障碍都似乎清除殆尽了。
涅尔瓦和图里乌斯·塞内尼奥陪着波佩娅在中庭闲谈,而特尔普努斯和狄奥多鲁斯在给齐特琴调音。尼禄迈着大步,径直走向一张嵌饰着龟壳的座椅,并在一个希腊奴隶的耳边低语了几句。这名侍从跑步离开,返回时带来一只金匣,从那只金匣里,尼禄拎出一件抛过光的,光彩夺目的粉色蛋白石项链。
“这里有一些与这个夜晚相配的首饰。”恺撒说。
“它们就如黎明的曙光一般耀眼。”波佩娅评价,笃信那条项链是给她的。
恺撒把那些玫瑰以的大块石子儿赏玩了一阵,将它们举起来对着夜晚的灯光看了看,然后又再次将项链放下,将其递给了维尼奇乌斯。
“代我转送给我命你迎娶的吕基亚公主。”他传谕道。
波佩娅又惊又怒地把目光从他转向维尼奇乌斯,最终冷冷地定在佩特罗尼乌斯身上,可是佩特罗尼乌斯却倚着座椅的扶手,手指拔弄着座椅旁边的竖琴的曲形琴背,仿若是要想敲定头脑中的每一个细节般。
维尼奇乌斯谢过恺撒的赠礼,回到角落里和佩特罗尼乌斯凑到一起,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我该怎么感谢你今天为我所做的一切才好?”他问。
“向音乐缪斯女神供奉一对天鹅,赞颂恺撒的歌曲,对不祥之兆一笑置之,我相信从此刻起,狮子的吼叫声不会再打断你的睡眠,也不会打断你的吕基亚百合花的睡眠了。”
“不会了。”维尼奇乌斯说。“我再也没有担忧了。”
“愿幸运女神向你们二人微笑。不过现在打起精神来,因为恺撒要吹长笛了,摒住你的呼吸,好好地听,做出敬仰得流泪的样子。”
恺撒确实抓着一管长笛,而且抬眼看向了屋顶。屋内所有的说话声都止住了,每个人都像块石头似的坐在那儿。只有特尔普努斯和狄奥多鲁斯躁动不安,他们观察他的唇形,又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后,坐出他一开始吹奏便给他伴奏的架势。
突然叫喊声和奔跑着的脚步声袭进玄关内,恺撒的一个获释奴分开帷幕探了探,列卡尼乌斯元老紧擦着他挤了进来。
尼禄蹙起了眉。
“请恕罪,神圣的恺撒!”那个获释奴叫道,他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带喘。“罗马着火了!城市大部分区域已经烧着了!”
这条消息令所有人都跳了起来。就连波佩娅也站起身,眼神捉摸不定地瞪视着恺撒。
“哦,众神呀!”尼禄感激地说着,他把笛子放到一边。“我就要看到一座燃烧的城池,完成我的《特洛伊亚特》了。”
他转向那个浑身颤栗的元老。“如果我立刻离开,还来不来得及看到大火?”
列卡尼乌斯脸白得和雪花石膏墙壁一样,“主上,”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整座城市一片火海,烟火中窒息的人数以百计,他们在绝望的疯狂中扑向了大伙……罗马完了,主上!”
“不幸的我呀!”维尼奇乌斯突然大叫一声,打破了沉寂,他脱掉托加,只穿了一身托尼就冲出了宫殿。
尼禄抬眼举臂,做出一个演员的姿态,开始宣告:“普里阿摩斯的圣城,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