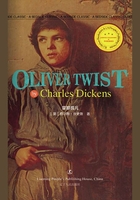就在维尼奇乌斯快把信看完的时候,基隆蹑手蹑脚进了书房,像个影子似的悄无声息,没有经过仆人们的通报,因为阖府上下得到过命令,不管是白日还是夜晚,都要让他自由地出入。
“愿你的祖先埃涅阿斯的神圣母亲维纳斯对你同样照顾有加。”那个希腊人在进门时说道。“就像迈亚神圣的儿子墨丘利对我的照顾一样。”
“这话是什么意思?”维尼奇乌斯从刚才坐着的位置上跳了起来,桌子后面,那个希腊人昂起头,双眼平视着维尼奇乌斯。“我发现了!”他模仿着另一位希腊哲学家发现真理之光时说的话。
那位年轻的贵族心潮澎湃,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你见到她了?”他终于开了口。
“我看见乌尔苏斯了,大人,我还和他说了话呢。”
“那你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吗?”
“不知道,大人。卑鄙之人也许会故作聪明地掩饰自己的身份,但这却让那个吕基亚人猜出了那人知道了他是谁,所以这么做不是让那人被一拳打懵,对接下来的一切一无所知,就是令那个巨人生出疑心,当夜就转移那位姑娘的藏身之地。而这,大人,是我所不为的。对我来说,知道他在集市附近,为一个叫德玛斯的磨坊主打工就足够了。顺便说一句,这个名字和你的一个获释奴一模一样,而这足够了,大人,因为在那个吕基亚人早上下工之后,任何一个被你信任的奴隶都可以跟踪他,并且知道他们藏身之地的确切地址。我只不过是为你带来了你那位天仙般的吕基娅在罗马的证据,因为乌尔苏斯也在这里,而且可以基本确定,她今天晚上会在奥斯特里亚努姆。”
“奥斯特里亚努姆?”维尼奇乌斯打断他的话,像是要准备马上跑去那儿的样子。“在什么地方?”
“那是一块满是老旧的地下墓穴和地窑的地方,在萨拉里亚大道和诺门塔那大道之间。我对你提过的那位大主教现在就在这里,比预期到达的时间提早了很多,他今晚会在那片坟场布道和施洗。虽然没有认定他们是非法之徒的敕令颁布过,他们却必须小心隐秘地集会,因为人民憎恨他们。乌尔苏斯亲口告诉我,他们所有人今天都会在奥斯特里亚努姆集合,去亲眼看看那位先生,亲耳听他讲道。他是他们的基督的大弟子,他们管他叫使徒,或者信仰的传播人。由于他们认为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自由进行各种活动,彭波尼娅可能会是今天晚上唯一一个不去那里的人。奥路斯·普劳提乌斯信仰传统的神明,彭波尼娅无法对他解释她为什么想晚上出门。但是,大人,吕基娅生活在乌尔苏斯和他们的长老们的照应之下,肯定会和其他女人们去那儿。”
维尼奇乌斯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的痛苦生活,惟有希望似乎才能能让他活下去。此刻,看到焕发出新生命的希望,他感觉就像一个走到路的尽头,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的疲惫旅人。
基隆也没有错过看到这些征兆,或者是没有错过从这些征兆中看出谋利的机会。
“的确,”他评论道,“城门是由你的人看着,大人。而那些基督徒们一定知晓了此事。但是他们不需要经过城门,他们可以从台伯河走,即便从台伯河走的那些路距离遥远,可为了去见大使徒,那还是值得一走的。其他穿过城墙的办法也有成百上千个,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走。”
“所以,大人,”他接着说道,提到了关键之处,“在奥斯特里亚努姆你会找到你的吕基娅,万一由于我想象不到的命运的捉弄,她不在那里,那么你也会有乌尔苏斯!他会在那里,因为他要去替我杀了格劳库斯。是的,他就是我们雇的杀手!你明白重点了吗,尊贵的军团司令官?没有?唔,好吧,要么,你亲自跟踪他回家,查出他们住在哪里,要么,把他用杀人犯的罪名抓起来,用各种办法从他口中知道吕基娅的实际下落。”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基隆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他想要的结论上引。“卑鄙一些的人会告诉你,在把乌尔苏斯的秘密掏出来之前,他和乌尔苏斯喝掉了能买下一座葡萄园的上等葡萄酒。一个卑鄙的人会声称,在和乌尔苏斯玩‘十二点’的纸牌,或者骨牌,或者掷骰子时,他输掉了一千塞斯特塞斯;或者说为了得到情报,他花了两倍这么多的钱。我知道你会为此怀疑我并且正这么怀疑我,可是让我在这一辈子里诚实一次……或者,毋宁说,我有生以来就一直是诚实的。我相信你的酬谢将大于我所希望的,大于我所开销的全部,正如同最慷慨的保护人,尊贵的佩特罗尼乌斯提示过的那样。”
维尼奇乌斯是一个军人,习惯了处理各种意外并且反应迅速。基隆满怀希望的总结陈词给了他从脆弱情感中恢复过来的时间。
“你不会对我的酬谢感到失望。”他没什么耐性地厉声说道,“但是首先你要和我一起去奥斯特里亚努姆。”
“我吗,大人?去奥斯特里亚努姆?”基隆的脑子里想都没想过要去那个地方。“我答应过替你找到吕基娅,而不是绑走她。想想吧,大人,如果那头吕基亚大熊发现他刚把格劳库斯给撕成碎片,而他又没有真正的杀人理由。那么我会有什么下场呢?难道他不会在大错铸成的时候,指出我是他犯罪的源头吗?对一个哲学家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和一个傻瓜沟通了,所以,我怎么答得出来他提出的问题呢?”
然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利益都必须得以保全。“但如果你觉得我给你指错了路,至尊至贵的军团司令官大人,那么请在我指出吕基娅藏身之所时再足额付款给我,现在么,你只要稍稍表示你的慷慨大方就行了,以便万一有什么不幸在你身上降临,大人——众神保佑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也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报酬而一无所有。而大人你伟大尊贵的胸怀,也不会允许那种事的发生!”
“这里有一些金币。”维尼奇乌斯扔给他一个装满了小金币的皮囊,金币的面值是第纳里乌斯金币的三分之一。“等我把吕基娅带到家里,你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皮囊,里面装满了第纳里乌斯金币。
“啊,朱庇特呀!”基隆向他致敬,“众神之父,滋养了人类的神!”
可是此刻维尼奇乌斯却皱起眉头,一幅颐指气使的模样,“你在这里吃饭休息,直到天黑为止,想都别想溜出这幢宅子。等到了晚上,你要和我一起去奥斯特里亚努姆。”
“谁能违逆你的意志呢,大人?”他说道,引用了东方的征服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下令把一个埃及祭司抓起来的时候,那个祭司对他说过的话。“领会我们那位伟大的希腊英雄在阿蒙神庙时表现出来的气度吧。没有人能违逆你的意志,所以最好有风度地投降。至于我,你的小金币,”说到这儿,他把那一包金币摇的叮当作响,“能买下我的一切。更别说今晚陪着你了,我很高兴那么做。”
维尼奇乌斯却对文字游戏一点耐心也没有。他又逼问基隆,让他说出详情。乌尔苏斯还说了什么?他说话时什么神态如何?从听到的回话里,他的脑海中冒出两种选择方案,两种选择皆令他期待万分。要么,今天晚上过去之前,他就能知道吕基娅的藏身之所,又或者,在集会结束之后回家的路上,他可以将她逮住带走。想到这儿,强烈的欢乐感袭向他的心头,既然重新得到她似乎颇有可能,所有指向吕基娅的怒火便瞬间弥散。感怀于突然而至的解脱和圆满,他原谅了由吕基娅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和失望之情。他觉得,吕基娅是他唯一珍爱的人,是他离不开的人,就仿佛是他牵挂已久,在一段长途旅行后即将回家的恋人。他有一股命令将府里挂满花环的冲动。他谁也不恨了,就连乌尔苏斯也不用受斥责。他随时都可以原谅任何人做过的任何事情。不管为他做什么都受他鄙视的基隆,现在似乎变得顺眼和有趣起来。他双眼发亮,他的脸上焕发着生机活力,就连他的府宅里的阴影似乎也是欢快明亮的,青春和生命的欢乐在他体内再次苏醒。以往令他丧气的痛苦让他没能对爱恋吕基娅的程度做出全面的判断,只有这时他才明白他在盼望吕基娅回心转意。他要吕基娅,是的,他要吕基娅,但这种要又不一样,它现在是一种希望,类似于寒冬的土壤等候着春天的阳光。终于摆脱了伤害和侮辱的他在剧烈紧迫的情欲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一种更温柔的欢乐,感受到了一种更亲近的情感。他还感受到全身上下充满了能量和体力,他相信,再次见到吕基娅后,没有什么能让他对她放手,无论是全体基督徒世界还是恺撒本人。
这个年轻贵族无边无际,满得要溢出来的欢乐给了基隆某种鼓励,他现在对自己的前程更敢想,也想得更美了。他开始出更多的主意,猎物还没有被收入囊中,他提醒,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多加小心,否则他们就要冒着煞费苦心的全盘计划被毁之一旦的危险。他恳求维尼奇乌斯不要试图在奥斯特里亚努姆抓获吕基娅。
“我们应该戴着兜帽去那里,把我们的脸孔藏起来,呆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观察一切,最稳妥的办法是一旦锁定她的身影,就跟着她回到家,记下她进去之后再也不出来的房子是哪栋,然后让一群奴隶在黎明时分将其围住,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她带走。”
他指出,法律有利于他,吕基娅还是个人质,名义上处于恺撒的监护之下,所以官府不会进行干涉。如果出于什么原因,吕基娅没有出现在奥斯特里亚努姆,他们也可以跟踪乌尔苏斯,以此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们不能带太多人。”基隆警告。“他们只会令那些基督徒产生警觉。然后他们就不得不吹灭烛火,就像他们第一次掳走吕基娅时的那样,消失在黑暗之中,分散到一些只有他们知道的秘密地点。不过,让我们随身带几件武器,再带上一两个壮汉,万一事情不对,我们可以有所倚仗。”
他说什么维尼奇乌斯都赞成。佩特罗尼乌斯的建议提醒了他,他派出奴隶去找克罗顿,而这终于打消了基隆的最后一丝忧虑。这个希腊人认识所有的公众人物,他从来不错过竞技场里的每一场角斗比赛,并且经常叹服于那位着名摔跤手的超人体力。是的,他说,他会去奥斯特里亚努姆。乐意之极!有了克罗顿帮忙,那袋许诺过给他的第纳里乌斯金币的叮当声似乎更响了。
于是,他很快被叫去仆人区的饭桌上,他心情愉快地坐下享用晚餐。饭桌上,他对那些奴隶们尽说些神奇药水的事情。他刚刚卖给他们主人那瓶神奇的魔法药水,那瓶药水只要涂抹在最驽劣的赛马的四蹄上便够用了,他说,那匹驽马会让其他赛马对它望尘莫及。他,基隆,是从一个基督徒那里学会如何配出这种药水的。尽管塞萨利因巫术而出名,但是基督教的长老比塞萨利人还要熟悉奇迹和法术。他们对他非常敬仰,他说,而且毫无保留地信任他,对理解鱼这个符号意义的人来说,这种信任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