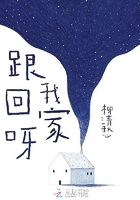民众们开始往恺撒的花园蜂拥而去时,夜幕还不曾降临。他们去时唱着歌,打扮得像去游行一样,头上戴着花环,心情愉快,大多醉醺醺的,聚集起来看一场超级新秀。“半死人!葡萄枝者!”这样的喊叫声响彻忒科塔大道,埃米利安大桥和台伯河对岸,响彻在凯旋路上,从尼禄的圆形露天竞技场里响起,一路响至梵蒂冈山上。罗马以前曾有人被捆在木桩子上烧死,但是人数从来没有这么多。
由于打算彻底结果基督徒,也由于打算终结在全城的监狱里扩散的传染病,恺撒和提盖里努斯命令清空所有的地牢,由此监牢里面只留下了寥寥几个犯人,他们全都注定了现身在竞技比赛的终场演出里。结果就是,当民众们穿过大门,走到花园里面时,他们全都惊呆了。沿着郁郁葱葱的小树林的所有主干道和路径,沿着穿越牧场的道路,以及围绕池塘,人工湖,灌木丛,草坪和花坛旁侧的通道全都密密麻麻地钉满了高高的,涂有沥青的木桩,每个木桩上靠近顶端的部分都绑有一个基督徒。从起起伏伏的一个个小山丘上看过去,视野不受树木遮挡,一列列戴着花环的柱子和人体伸向远处,在山丘和山谷间纵横穿越,点缀在香桃木树叶和常春藤之间。他们延伸得非常远,以至于近处的木桩看起来高如船上的桅杆,而那些远处的木桩又似乎比插在地上的标枪大不了多少。他们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预估;就仿似一个民族被整族绑在了木桩上供恺撒和这个城市取乐。一群群傻子停在一根或者另一根木桩子前,因为蒙冤者的身形,年纪或者性别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瞪视着那些人的脸孔,花环和常春藤头冠,然后继续向前,惊异地问:“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嫌犯?罗马怎么能被刚刚学会走路的稚子烧毁?”这种讶然逐步转变为了不安。
天光入暮。新冒头的几颗星星在天上闪烁着。每个蒙冤者的旁边都立着一个拿着燃烧着的火炬的奴隶,当号角声响遍花园,示意表演开始的时候,他们把每根木桩的底部点燃。藏在花朵下浸了沥青的稻草迅速被点着;火光明亮,在花环间盘旋缭绕,又跃上蒙冤者们的双腿。民众们变得安静下来。花园里回荡着众多长长的呻吟和痛苦的呼叫。有的蒙冤者的眼睛看向星光密布的天空,并开始吟唱歌颂基督的赞歌。公众们呆愣地听着。当从最小的木桩上响起孩子们的尖声嘶叫,“妈妈!妈妈!”听到这些时,就连他们之中心肠最硬的人也恐慌得畏缩起来。看到小小的身体在火焰中挣扎,看到小小的,天真的面孔在痛苦中扭曲,或者被开始使蒙冤者们窒息的烟雾呛住时,醉得最厉害的人也打了个哆嗦。火焰向上蔓延,越烧越朝上,烧掉了更多的常春藤和玫瑰花的花环。
火光在主干道和路径上闪耀;在小树林,牧场和花坛间闪耀。人工湖和池塘里的水如同着了火一般,灌木丛和树叶在反射的火光下变成粉红色,黑夜亮堂得犹如白昼。肉体燃烧的臭味充斥在整个花园里,但在此时,奴隶们开始向散布于木桩与木桩之间的特别气味里挥撒没药和芦荟。百姓中间响起零星的叫喊声,但是很难说他们是在表达同情、敬畏、愉悦还是欣喜。火苗沾上木桩,爬向蒙冤者们的胸口,燎炙他们的头发,覆上他们烧得焦黑的脸庞,并越发往更高处蹿升,仿佛是在肯定那些下令放火烧他们的人的权势和胜利,随着这些,百姓们的情绪高涨起来。
演出一开始,恺撒便驾驶一辆四匹白马拉的豪华赛车出现在他的子民中。他穿着绿队——他和他的朝廷在赛马场上支持的队伍——颜色的竞技场赛车手装束。他后面跟着的是其他载满了衣着富丽堂皇的廷臣,元老,祭司,以及代表巴库司祭品的醉酒裸体女人,她们的头发上全都扎着花环,手里拎着酒壶,她们之中大部分人喝得醉醺醺的,像女鬼一样尖嚎。行驶在他们旁边的是打扮成农牧神和森林神的乐人,他们弹着齐特琴,八弦琴,吹着笛子和号角。罗马上流人物的妻子女儿们驾着另一辆马车,她们全身半裸,和其他人一样酩酊大醉,她们周围环绕着各种跑腿的人:有的摇晃着挂有铃铛和彩带的长旗杆,有的打着长鼓,有的撒着花瓣和花朵。
星光闪耀的车队向前行驶,一边喊着“嚯-嚯!”声——一种宣告巴库司节开幕的欢快呐喊声——一边穿过滚滚浓烟和重重人体火炬,沿着最宽阔的干道奔驰。恺撒驾驶的速度慢如蜗牛;车内,随侍在他左右的是基隆和提盖里努斯,他打算拿那个老希腊人的恐慌来给自己寻开心。他看起来身形巨硕,正一边欣赏着燃烧着的人体,支愣着耳朵听闻叫喊声和喝彩声,一边眨巴着浮肿的双眼。他高高站在自己的镀金赛车上,被望不到边的,弓身拜见的人潮所包围。他还戴着一顶赛车冠军的金冠,像一个可怕的巨人那样,居高临下地面对他的朝廷和群众。他那粗壮多肉的胳膊高高举起,拽着缰绳,就仿若是抬起来祝福他们似的。一抹微笑掠过他的脸庞和他眯成一条缝的眼眸,他的现身如同把光芒洒向他们的太阳,或者,一个位高权重的可怕神祗。
他隔一会儿停一停,好更清楚地观察胸脯在火焰中皱缩的妙龄少女,或是观察一个幼儿扭曲的面孔,然后他继续前行,领着跟在他后面的那支疯狂嚣张的车队。时不时地,他或是威武庄严地对百姓们屈身致意,或是向后仰靠,拉着镀金的缰绳,和提盖里努斯聊天。最后,他把车停在了两条干道交叉口的喷泉旁边,他从马车上走下来,示意他的追随者们聚拢到他的身边,和百姓们打达成一片。
叫喊声震耳欲聋。欢迎他的掌声响起。喝醉的狂欢者、仙女、元老、达官贵人、祭司、农牧神、森林神和禁卫军卫兵们立刻将他围拢起来,形成一个癫狂错乱,兴高采烈的圈子;他和提盖里努斯从一边绕着喷泉走,基隆则从另一边走。喷泉周边点着几十个人体火炬,尼禄在他们每个人面前驻足歇脚,或是对这些蒙冤者品头论足,或是对那个脸上现出绝望至极神情的希腊人冷嘲热讽。
最后,他们来到一个扎着香桃木枝条和藤蔓植物的高高桅杆前。火苗不过才刚刚舔上那个蒙冤者的膝盖,不过,由于被青绿的枝条冒出来的烟雾遮挡,他的脸一开始没有露出来。然而,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缕夜间新刮起的微风将烟雾吹散,露出了一位老者的脑袋,那人有着一把垂到胸前的白胡子。
基隆似乎皱巴蜷缩成了一个受了伤的爬虫。他的嘴巴张着,发出乌鸦叫似的嘶鸣,语气与其说是人的声音,不如说是野兽的声音。
“格劳库斯!”他嘶叫出声。“格劳库斯!”
格劳库斯从熊熊燃烧的木桩上垂眼看他。他还活着。痛苦浮现在他的面庞上,他使劲儿朝前抻,仿佛是要再最后久久地看看他的迫害者——那个出卖了他,抢走他的妻子和孩子,派人刺杀他,而当这一切都被以基督的名义宽恕之后,又再一次地把他交到压迫者的手里的人——最后一眼。从没有人被冤枉得有他这么厉害。从没有人在另一个人手里受到这么残酷的对待。而现在,这个蒙冤者正在一根涂有沥青的木桩子上燃烧,而他的迫害者却站在木桩下。
格劳库斯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基隆的脸。烟雾时不时地遮住他的眼睛,但是每次微风把烟雾吹散,基隆都能看到那两只眼睛在盯着他。他跳起来,尝试着跑走,但是却跑不动。他的双腿突然僵死了一般。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用着超人的力量扼住了他,把他定在了这根火柱前,动弹不得。他变成了石头,害怕得僵住不动。他感觉到——他所能具有的全部感觉是——他的内心有什么在爆发,在撕扯,在退却;有什么东西在涌出,在洒落,在倾泻。他知道,他再也受不了他身边更多的流血和折磨了,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终结,在这个夜晚里,有关他的一切都在随着恺撒,朝廷和所有聚集的百姓消失。他蜷缩在一个无边无际,惊恐万分的黑暗中央,在黑暗中,他只看得见这双殉道者的双眼,这双召唤他接受审判的双眼。
那颗脑袋使劲儿往他的方向凑去,越垂越低,而那双眼睛则一直在看着他。
那些离他们最近的人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达官贵人们向前簇拥,找着乐子,可是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
基隆脸色吓人,在极度的痛苦和恐惧中扭曲着,仿佛火舌正在舔弄他自己的肉身。骤然间,他踉跄着向前,双臂朝前伸向那个受难者,用害怕的,万分恐慌的嗓音尖叫道:
“格劳库斯!以基督的名义!宽恕我!”
众人都没有出声。附近的每个人都打了个寒颤,所有的眼睛都锁住那个木桩子上受难的老人,仿佛所有的眼睛都有了自己的意志和力量。那个殉道者的头微微点了点,或者像是在点头的样子,一声呻吟从桅杆顶端飘落。
“我……宽恕你。”
基隆脸朝下,五体投地,像只野兽般嚎叫,他用双手抓起一把泥土,把土洒在了自己的头顶。与此同时,火焰上蹿,裹住了格劳库斯的胸膛和脸庞,烧断他的香桃木头冠,点着了木桩顶端的彩带,火光突然一下子亮了起来。
当基隆片刻之后站起来时,他的脸色是如此不同,达官贵人们都以为他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双眼燃烧着收到神明启示似的激昂之色。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映照出超凡的力量。前一刻,这个希腊人还一瘸一拐,老态龙钟,现在,他似乎被神魔附体,又或者像是一个祭司,接触到了他的神明,意欲对世界宣告新的真理。
“他怎么了?他疯了!”达官贵人里冒出了几道咆哮。
他背对他们,抬起右手吸引大家注意,然后开始用大得足以令不光光是朝廷大臣们和恺撒,也包括所有的百姓们都听到的声音说话。
“罗马公民们!”他喊道。“我以自己的性命发誓!在这里,被杀死的人是无辜的!放火烧城的人……在那儿!”
他的手指头指向尼禄。
此时的气氛是令人惊悚的,无声无息的寂静。廷臣们直发愣。基隆保持着手臂颤抖着指向恺撒的站立姿势。猛然之间爆发了大混乱。民众们像是被一股骤风刮到似地扑向他,要把他看得更清楚些。有的百姓发出尖厉,嘶哑的呼哨声。“红铜胡子!”他们嚎叫。“弑母犯!纵火犯!”咆哮声时刻在高涨。赤身裸体的酒神女祭司们跑向赛车,尖叫声高得直抵天庭。恰在此时,一批木桩烧尽了,倒在地上,卷起了一阵阵火花,加剧了混乱。稠密拥挤的人群产生了盲目的惊慌,人流冲走了基隆,把他裹进了花园深处。
现在到处都有火炬在倒塌。砸在干道和路径上,使其充斥着火花和烧完的木头与人肉的臭味。担忧,气馁,惊恐的百姓们堵在门口,试图出去。刚刚发生的事情被口口相传,被夸大,被歪曲。有的人说恺撒晕死了过去。有的人称他承认了焚城。还有传闻说他病倒了,被像个死人似的甩进了他的黄金赛车。
零零星星地,开始有带着同情的声音议论起基督徒。“他们没有火烧罗马,是吧?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鲜血,折磨和冤屈呢?众神会受不了的。他们肯定想着报仇雪恨,现在,什么样的祭品会使他们平息呢?”
越来越多的说起了“稚子何辜”。女人们深深地怜悯所有被扔给野兽,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地狱般的花园里被烧死的孩子们。接着,她们的怜悯变成了冲向恺撒和提盖里努斯的激烈咒骂。
还有人在匆匆疾奔时突然停下,或是问自己,或是问别人:“面对死亡时给了如此勇气的神是什么样的?让人们对磨难无动于衷的是何许人物?”
他们若有所思地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