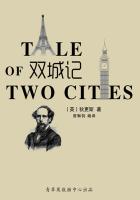隔了两天,司仪正在家里陪司念打球,司玲风风火火找上门来。一进门就嚷:司仪,我发现这个时代唯有你一个人还有心思陪小孩玩耍,真是纯洁得可爱啊!
司仪不高兴,她最看不惯姐姐这种打扮这种口气了,仿佛她自己是全能冠军的博士生导师似的。她只淡淡地说,有事吗?儿子猛地掷过来一个球,司仪一分心没接好,被儿子嘲笑一番:妈妈越来越不行,再不用心我就罚你下场!
下场下场!大姨来了你们还打什么鬼球!司玲不高兴地大声嚷嚷。
妈妈下场!让大姨上!司念大声命令着。
司玲忍俊不禁,高声说:嗨呀!念念,你就别为难你大姨了。我这样子能打球吗?
司念一瞥司玲:长裙曳地,钢笔那样长的高跟鞋……司念说,快点去换嘛。
你就饶了我吧。司玲说,换了我也不行,我根本就没打过。
司念将球往家门前的台阶上一掷,赌气说:算了算了,你们滚蛋!
司玲便做个鬼脸,讨好地说:小念,你出去玩,大姨给你钱。便打开小包,抽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给司念递过去。
乌啦!大姨万岁!司念欢呼一声正要冲出院门,被司仪喊住:司念!别跑远了,到电影院前去跳蹦蹦床,小心点!
行了行啦!我妈真不爽快,老跟我罗嗦,在爸爸面前却不这样。大姨从不对晨晨姐罗嗦,你怎么不学点?司念一边走一边大声说。
姐妹俩都笑起来。
司玲径直往屋里走,一进门便说:司仪,我碰到麻烦了。司仪漠然地问:什么麻烦?一边拿了玻璃杯去茶几上的饮水机下接水,她家上半年开始使用纯净水,很卫生的。
我看中了一个男人。司玲毫无顾忌,见司仪没反应,只顾自己喝水,就说,你怎么只顾你自己喝,也不给我来一杯。
你自己倒嘛。司仪一屁股坐下,哦,我累啦,今天陪念念玩了一个多小时的球呢。
你真悠闲自在呢!你也该管管罗舜!这个年代男人不管紧点,就会采野花。
算了吧,姐,你别教训我了,还是管管你自己吧。司仪不冷不热地说,你这两个月回双溪镇去过吗?
我就是跟你讲这事!司玲说,要你帮我拿主意。
司仪不解,望着司玲,司玲从茶几上拿起一瓶健力宝,扯开盖就喝,说:我上半年认识了一个男人,他叫丁文,很能干的,我想嫁给他。
司仪张大嘴巴,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姐?
司玲不耐烦,大声说:我想嫁人?你是不是聋了?
什么什么?你想嫁人?司仪站起来,你这不是有家有男人么?
不错!要不,我怎么来找你呀!你当我头脑简单吗?司玲似乎还颇有理,毫不遮掩。
好哇!你把姐夫把小晨都丢开不管啦?你发财成了富婆就另攀高枝啦你有脸没有?
我哪说我不管啦?我哪里是攀高枝啦?不了解就别发言嘛。司玲质问起司仪来。
吊颈鬼倒发强。我还要找你的理!司仪沉着脸说。我不管了,你爱怎样就怎样吧。当初又不是我叫你嫁龚佳奇的。说爱就爱,说离就离,你倒好爽快!你心里还有孩子没有?
司玲便软下来,好言说:司仪,我是你姐,你总不能看着我痛苦吧?我才三十几岁,还有大半辈子呢。龚佳奇已经那么老了,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这不是理由!司仪毫不妥协,人都有老的时候。
司玲便不说话,一时冷场。
过了好一会儿,司玲打开包,掏出一张照片:喏,你看,这是他的照片,他才三十二岁,很可爱的,保准你一见他也会喜欢的,他丝毫不比罗舜逊色。
你还有脸这样讲!司仪打开司玲的手,仍是气咻咻地。
司玲厚着脸皮把照片放在司仪面前的茶几上,便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司仪瞥了一眼照片上的那个年轻男人:一张含情的眼睛闪着挑逗的光彩,那是司玲这样的女人无法拒绝的一种笑态。这张光洁的额头脸颊,酷似毛宁的那种神采,确实令任何女人都无法讨厌起来。
司仪心下思忖:姐姐啊!你的劫难又开始了。浅薄的人都会被表象吸引,浅薄的女人喜欢年轻的男人也如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一样,心态应该基本上是相同的。司仪这样想着,便说:姐,不是我不支持你,实际上是为你着想,女人的青春有几何?一旦你红颜褪尽,你能保证他还喜欢你吗?
司玲也平静下来,说,正因为青春短暂,我才要抓紧时机浪漫几年,不然,这一生不是太亏了么?你不看龚佳奇那个熊样?能力没能力,风度没风度,甚至那方面也不行了。司玲说着说着越发坦然起来。
你能肯定那丁文是真心爱你而不是看中了你的口袋?
看中了口袋又怎么样?只要他能满足我。跟他在一起同跟龚佳奇在一起时感觉就不一样!
你跟他同居了?
不跟他同居了怎么知道?司玲反问,倒弄得司仪自己不好意思起来,半天才低声说:司玲,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才几个月啊,你就这么开放了!
你别一副正人君子模样!你以为你很纯洁不是?你以为你是含苞未放的花朵不是?你和罗舜在床上难道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司玲火了,站起来大声说,男人女人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张结婚证只不过是公开的性伴侣关系,人家不指责罢了。至于你在床上实质上不都是在做爱么?你能否认?你的儿子是怎么来的?不是做爱后的副产品么?
司玲一直问到司仪脸上来,司仪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所有在大学课本上学的知识全苍白无影了。司玲所言全在司仪心中盘桓过,纠缠过,只不过司玲坦率地说了出来,而司仪却只是深藏于心底罢了。这便是文化层次不同的区别么?亚当与夏娃当初就是如此。一个声音在心底咕哝。司仪摇摇头,低声说:我被你搞糊涂了。司玲,你让我冷静地想一想。
司玲象小痞子得意而夸张地点头,退一边去仰靠在长沙发上,翻一本《警探》。
也许过了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姊妹俩谁也不说话。罗舜回来了,一进门便惊异地问:哟!今日怎么这么乖?象高考考场上似的。
司玲蹦起来回答:罗舜,你别乱吵了,你烧饭去吧。我们还考虑国家大事呢!
罗舜就打趣,国家大事谈不上,恐怕是终身大事吧?
你发狠烧饭,打个番茄汤。呆会儿我再跟你讲。司玲一副大姐派头,平时开玩笑惯了,老是一到一块就打嘴官司。
好吧好吧,两个女人考虑国家大事,让一个男人进厨房烧饭。罗舜一边进厨房一边叽咕个不停。司玲望着他的背影丢过去几句“还是勤快点好,勤快点长寿又讨女人喜欢。”
罗舜拧开水龙头一边洗手一边朝外叫:女人三十烂豆渣,男人三十一枝花。谁还要讨女人喜欢?这世道早反过来了,男人是花,女人是蜂蝶,蝶恋花,你会不会唱?
司玲便气得翻白眼,说:你听听,司仪,你该不该管管他,哪天被蜂蝶采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司仪便笑:会说的人不会干,要干的人不会说。这就象狗咬人一样的道理——爱叫的狗不咬人,只有不叫的狗才会冷不防咬你一口。
好啦好啦。你别不识好歹,一钉耙打一串。司玲气嘟嘟地骂:一个被子不睡两样的人,一点不错。
可是龚佳奇跟你共盖了一二十年的被子,怎么你们一点不象呢?司仪讥讽起来,一字一句缓缓地说。
就是嘛!这是命中注定,所以我才下决心跟他分手了。司玲又顺着司仪的话接下去,一点不觉尴尬。
嘿!司玲你说得真轻松!罗舜手拿锅铲从厨房探出头来插一句:跟龚老师分手?你跟谁?看上我啦?
去去去!一边去!谁跟你讲了?司玲斜着眼撇他。
罗舜作个鬼脸,又缩回厨房去。
司仪不答理罗舜与司玲的口仗。这样的对话以往她听得太多了,年纪本就相仿,没大没小惯了。但今天听起来,却有些说不清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