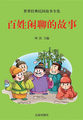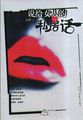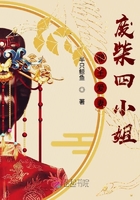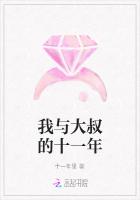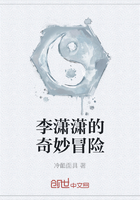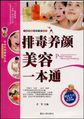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研究比较文学?如何加强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对话?如何在比较中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经过多年的探索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们从古人的智慧中寻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和而不同”。发现让人如获至宝,大家似乎可以凭借这一条一往无前。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的同仁对许多观点都可以批评、可以质疑、可以说三道四,唯独这是个例外。究其根源,正是缺乏问题意识使然。
什么是比较文学中的“和而不同”?有学者指出:“比较文学由于其性质所规定,它首先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提倡在差异中反映自己,加深对自己的认识,使一种文化或文学在与不同文化或文学的差异和反观中得到发展和更新。与此同时,比较文学也十分重视发掘不同文化或文学中人类共同的基因,正是这些共同基因使人类有互相理解和沟通的可能。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原则。”“和而不同”原则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晏婴和齐侯就“和”与“同”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次对话。齐侯对晏婴说:“惟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侯侍臣梁丘据。)晏婴则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晏婴的意思是说,“和”就如同做菜一样,把油盐酱醋这些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才能做出菜肴来,给人口福之享;“和”也如同音乐,五音调配、相成相济,才能构成美妙的乐章,让人感受到旋律之美。因此晏婴认为,梁丘据对齐侯的态度不是“和”,而是“同”,他说,“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梁丘据这种与齐侯随声附和的情势,就好比做菜只用水,谱曲只用一个音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如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若是。”可见,“不同”是“和”的基础和前提,几样事物相异相关,才可能达成一种“和谐”。晏婴之后,孔子又将这种“和而不同”的观念从言说君臣关系扩大为言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主张。《国语·郑语》记载了周代史官伯阳回答桓公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又将“和而不同”看作事物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和而不同”这一语词在儒家经典中的频繁出现,加上后继大儒们的不断阐发和历代统治者的认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之一。
“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曾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在当今文明冲突时代,一些学者重提“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显然是看到了这种思想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所构成的与西方文化和文明不太一致、相互补充的思维取向。当今之世,西方文化仍然在全球化浪潮裹挟之下在向非西方国家倾覆,这正导致着世界文化日益趋同和日益单调,这些学者标举“和而不同”的大旗,是有着渴望以此来扭转世界文化形态日益单一化这一不正常状况的良苦用心的。
从世界角度而言,各国既要保存自身的民族个性,又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而不同”的确不失为一种可能实现这种愿望的良策。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互相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在某些方面达成一些共识,本着求同存异的平等原则,既保留各自的特色,又在某种意义上达成“认同”。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明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相借鉴、互相阐发推动双方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这也许正是“和”的作用。我国一些学者反复宣讲“和而不同”的国际意义,大概用意在此。然而,也正是这些学者,没有认识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与谁不同?谁跟你和?”换句话说,倡导“和而不同“的一些学者,并没有认识到“和”的前提是“不同”,而我们当前的文论话语并没有什么与西方“不同”之处,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没有多少与西方不同之处。“和而不同”需要有“不同”作基础,在“不同”之后才有“和”的问题。盘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现状,我们不觉会生出叹惋:因为近百年来一直在追摹西方文化,所以其自身拥有的文化特色正在逐步地消殒。既然没有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在当下的理论话语与文化形态的绝大多数层面都与西方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拿什么跟人家“不同”,进而要求人家“和”呢?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文化尤其是文论也没有幸免于西方文化的侵袭。自“五四”以来的近百年历程中,我们更多地注重于对外来文明的借鉴,而且有时借鉴甚至变成了借用,变成了放弃主体意识的胡乱引进和盲目照搬,却忽视了对中华文明自身个性的承续和开拓。文明的深层差异与对事物的言说方式密切相关,甚至深深根植于语言的语法结构中。许多当代学者已经看到,“五四”以来对白话的选择和使用不只是语言形式问题,白话实际上是一种启蒙性的语言,其中包容着来自西方的、全新的启蒙精神;现代文学是以翻译体白话为基点成长起来的,现代学术话语更积极主动地采纳了西方的逻辑语势,而弃绝了我国古代的话语言说理路。总之,我们未能及时检点民族文化特征的西化式现代化历程,最终导致了文化建构思路和学术言说方式的全面西化。应当承认,以学习西方为主的现代化历程在不少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它使中国在经济上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逐步融入世界大家庭中,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一员。但这一过程使中国当代的文化文论在抛弃古代话语言说理路的同时,也疏离了自己的文明本源,从而在西方文化面前丧失了自己明朗的个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建构上的失误。
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转型历程中,也有些学者曾经提出过很好的建议,用以实现既保留中华文明的传统,又能成功地借鉴西方文化的伟大目标。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被称为“哈佛三杰”的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曾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国粹和新知并不冲突,是可以共同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的。国粹和新知相辅相成,互相参佐,国粹给新知的吸纳以一个合理的参照,而新知又为国粹的昌明提供有效的资源。应该说这些学者提出的这种建议是很有道理的,可惜的是,由于中国近代的衰弱给了文化激进主义更充分的合法性,吴宓等学者的观点因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的采纳。不仅国粹未能被昌明,新知由于没有国粹的土壤,因而无法在民族文化中融而化之,只能强行地植入中国文化与文论的肌体之中,由此,西方文明整体性地置换了传统文化和文论的质态,导致了中国文论的“失语”和文化的“失家”。没有了自己的文明个性,我们的现代文化尤其是现代文论只能是与西方趋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没有与西方的“不同”,西方学者也自然对你的东西不屑一顾,不会也不可能与你“和”。在这种背景下来谈论“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只能陷入尴尬的境地。
学衡派主将之一吴芳吉在《再论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化观》一文中写道:“复古固为无用,欧化亦属徒劳。不有创新,终难继起,然而,创新之道,乃在复古欧化之外。”现在倡导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其实正是倡导“不同”;我们强调“失语”,正是为了建立“不同”的话语;我们提出的跨文明研究,希望通过此种研究重建中国文化规范和文论话语,目的就在于将中国传统文明和文论进行现代转化,让它们恢复生机和活力,重新参与我们的思维重建,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这种传统文明和文论的现代转化,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欧化”,而是于“复古”与“欧化”之外,又不脱离古代传统和西方资源的理论创造。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拿出实绩来”,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自己富有独特个性和价值的文化体系和文论话语,西方学人才可能对你刮目相看,而我们也才可能将“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真正转化为现实。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