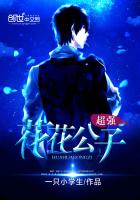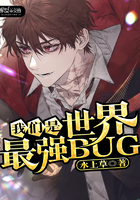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1993年抛出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讨伐之声此起彼伏。但自“9·11”事件之后,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世界各地的销量持续攀升,“9·11”事件似乎成了“文明冲突论”的最佳注脚。在现实中,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在交往中的不和谐之声也时有所闻,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力。
其实,至今仍焕发出生机、显示出生命力的全球主要文明样态,归根结底是异质性的。东方文明也好,西方文明也罢,毕竟都有其独特的生成基础和发展历程,每一种文明的有效性,首先是建立在这种文明内部长时期形成的价值理念、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基础之上。这种独特性决定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差异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因此,不同文明之间人们的交往必然具有冲突的性质,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从这种意义上说,文明之间的交流,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只不过冲突的方式有所不同,有时表现得剧烈,有时表现得缓和。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文化碰撞和文明冲突尤其不可避免。
“文明冲突论”产生于后现代社会背景之中。后殖民主义兴起,一系列新兴国家独立后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一些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方文明曾幻想让非西方国家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逐步西化,从而与西方文明认同。但事与愿违,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表现出更迫切的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随着国力上升,也越来越极力复兴本土文化。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强调其民族统一性时,把本族语定为国语;与西方关系密切的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语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从学者到政治家,以丰厚的文化资源运思,主张“和而不同”,强调世界的多样性,提倡不同文明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而这恰恰被西方认为是非西方文明的自我伸张,对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相对而言,西方文明在衰落。面对这种现实,西方文明中有人难免心中焦虑,并进而产生了一种再也不能控制世界秩序的恐惧感,“文明冲突论”就是这种焦虑和恐惧心态的直接反映。
异质文明之间的交往必定在融会、碰撞和冲突中进行,特别是在中西文明之间。自近代西方文明以强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因痛感国运衰弱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中西之争就成了一百多年来经久弥新的话题。中西文明冲突,在众多的学者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和西,也成了一种固定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近年来,学界不乏有识之士,试图超越这种西方影响和决定中国的僵化思维模式。刘禾先生认为,在“跨语际实践”中主方语言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主体性,并对客方语言的权威地位进行着颠覆,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陈思和先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观点,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接受”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内部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完整的体系足以揭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化、否认西方现代性观念的优越地位及其对中国的支配性影响。
在“文明冲突”的语境里,比较文学学者对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僵化思维模式的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跨语际实践中话语和范畴对原有知识系统的“超越”,毕竟摆脱不了它与这些知识系统的关系。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获得也一定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和融会的结果,而且也要在这种交流之中产生意义。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更与西方文明这一“他者”的存在密切相关,因为这一“他者”既是促使中国文学现代转化的动力,也是转化的重要内容。历时地梳理我们的民族文学,离不开对“他者”的横向考察。这也是比较文学大有可为的领域。异质文明之间文学的交流、融会和冲突已经发生过,并且仍在发生。回避这种事实,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比较文学的新跨越新发展。“文明冲突论”之所以影响广泛,正在于它触及了新世纪伊始的时代命脉。在新的世纪之交,西方文明的影响力在衰落,非西方文明大有东山再起之势,文化冲突正在日益增多,新一轮文化较量悄然兴起。当今各种主要文明,虽无一例外都含有一些普适性成分,但世界上毕竟还没有单一样态的普适性文明,文明的冲突和融会仍是人类当下所要面对的主旋律,在新一轮文明碰撞和融会之中,世界各国的文化影响力此消彼长,边缘和中心正在重新界定,用某一种价值理念一统全球的想法越来越显得天真,新的文化转型期正在形成。文学,作为文化的前沿,是文明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冲突”的现实和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文化转型,必将对比较文学产生决定性影响,使比较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跨文明研究。
回顾一百多年的学科历史,比较文学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危机重重。当初“比较文学”一词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欧洲时,就遭到了种种非难。法国学派对此及时地作出了回应,奠定了比较文学坚实的学科地位。但后来法国学派对文学性的偏离和对文学“外贸关系”的实证性考察,背离了“世界文学”的理念,使学科处境岌岌可危,陷于一潭死水。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比较文学在内外争论中继续显示了生机。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立论在东西方同时出现,有学者竟然宣布了比较文学的“过时”和“消亡”。文化研究的冲击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学科内部的问题更为关键。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式旨在综合文学的普遍性规律,这与其研究现状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因为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毕竟仅拘囿于西方文明之内,在大量非西方文学“缺失”的情况下,文学规律的“普遍性”受到了质疑。面对异质文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在犹豫、徘徊,难以突破西方文明的边界,有人甚至认为东西方文学之间因厚重的异质性而不可能进行比较研究。可见,法国的“影响研究”模式,在影响事实的探寻中偏离了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和学科目标,而未能把非西方文明的文学纳入研究视阈,又使意在综合的美国“平行研究”范式陷于尴尬境地。异质文明交往越来越频繁的今天,过于注重求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面临着突破,比较文学必须从学科内部推动战略性转变,这种转变就是跨文明研究,唯有如此,拥有世界胸怀的比较文学才会再一次化危机为动力,迎来学科发展的新辉煌。
中国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基于自身实践,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鲜明地提出跨文明研究,既是对“文明冲突”时代课题的回应,又摆脱了学科内部新的危机,并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思路,必将成为比较文学新阶段的标志性特征。西方文明内部的比较文学研究,给予了同源性和类同性更多的关注,这种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在西方文明内部得到了证明。但推而广之,当把这种研究范式应用于异质文明的文学研究中时,却遇到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为数众多,但文明的异质性形成的深层差异往往更具有决定性。鉴于此,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把对不同文明之间文学异质性的探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表面上看,比较文学对相似性的追寻与对异质性的强调是矛盾的,其实,对于同源性和类同性的研究目的在于不同文学之间的互释和互证,而探寻不同文学之间的异质性是为了互补,在更高层次上与前者是辩证统一的。异质文明之间的文学书写及其规律的总结不可能完全对等,每一种民族文学必然具备鲜明的个性。在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异质性的凸显,在于彰显民族文学的特色,这种特色正是探求普遍性文学规律的基础。每一种民族文学均以其鲜明的特色得到世界的认可,从而获得世界性的特点,世界文学绝不会是单一的模式,而正是各种民族文学鲜明特色相融会而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性,各民族文学中的空白也可以借“他山之石”以适当的形式加以填补。
综观历史,从冲突到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旋律,是不同文明交流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汇和碰撞,往往是促进文明发展的直接动力。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对于各民族文学独特价值的强调,必然导致跨文明的文学交流具有“冲突”的性质,文学对话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沟通和交融的使命,为解决不同文明所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提供有创见的视角和思路。事实表明,异质性“他者”的观照有助于发现深层的联系。各民族文学之间在许多层面上是不对等的,西方文明中某种鲜明的文学现象在非西方文明的文学中却常常表现为缺失;在单一的文明内部,特定的文化资源有时也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和认识需要,不得不诉求于“他者”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在跨文明的文学交流与对话中,文学新质往往会转换生成。异质文明的文学之间,只有在互为主观、互为他者的状况下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自身、认识对方、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比较文学从跨文明的视野,通过异域间的考察论证,或着眼于文学比较中的价值与功能评判,或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概括出普遍的文学规律,从而在文学所及的范围内促进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沟通和交融,起到加强相互理解、缓和文明冲突的作用。
在跨文明交往的时代,各民族文学已经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综合体,而且世界各种文学之间共时性的影响力无所不及。那么,跨文明的比较文学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已有学者呼吁关注非西方文明中的各种文学样态,主张在使用“世界文学”、“文学规律”等词语时,给予非西方文学以足够的重视。然而,跨文明比较文学也面临着障碍。西方文明中顽固抱定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仍大有人在,他们认定非西方文学中除少数几部作品外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非西方文学来说,清理文明内部的文学流变进行更好的理论总结更为急迫。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有“好篱造好邻”的诗句,或许更适合今天的文学交流。只有首先耕作好自己的庄园,只有当各国文学以鲜明的特性赫然呈于世界面前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对话始可开展,歌德和马克思“世界文学”的理想才会离我们更近一步。
(原载《学术月刊》2003年5月,《新华文摘》2003年10月全文转载;此文与王敬民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