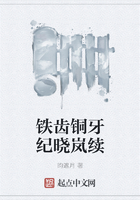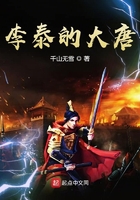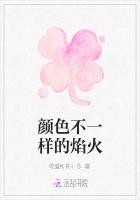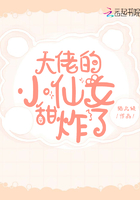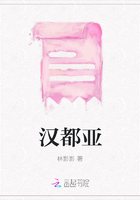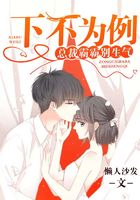孔子于是出发了,陈蔡两国的大夫就紧张了,互相商量:“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讽的正都是诸侯列国的病症。他在咱们陈蔡两国好几年,咱们这些卿大夫所干的,都不是合孔子之意的(可见,孔子的政治之道主要是帮着国君,而跟这些图私家利益、欺负蒙蔽国君的卿大夫过不去)。如果他去了楚国那里当了大官,楚国是咱的主子国,他一定挟楚国之力,把咱们这些在陈蔡用事(执政、管事)的卿大夫们给驱逐了,咱们不就完了吗?不能让他走。”
于是一起带着兵,去追孔子,把孔子在野外包围起来了。孔子又是冲突不出去,粮食也没了。他的徒弟们全病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就孔子体格好,照样讲课弹琴,吟诵弦歌之声不衰。子路气得要命,怒冲冲来见孔子,说:“君子,也会穷吗?”这个穷,不是现在的贫穷的意思,而是走投无路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孔乙己引用过的话了,意思是,君子穷了,会能安分地受穷,在困极无聊下,不会怎样,但是小人走投无路了,那就滥干了。子路怒冲冲地来对孔子说话,是嫌老师把自己和同学们领上了绝路,浪费了这么多青春,啥官也没当上,啥成绩也没干出来。孔子说,小人穷了,就斯滥了。那就是比如像你这样敢对老师乱吠,一点礼都没有了。
孔子被围了,没办法了,最后让能说会道的子贡溜出重围,跑去了楚国,向楚昭王陈说,我们来上岗的路上,被人围住了。楚昭王当即派兵去营救孔子,孔子这帮人才摇摇晃晃地支撑着饿病了的身子,去到了楚国。
楚昭王见到大贤孔子,分外高兴,觉得这贤人来我们蛮夷之国来支边,那得好好酬报啊。于是,打算把七百个里(里是居民小区,大约二十五家为一个里)的民户封给孔子,作为封地食邑。楚国令尹子西作为本地卿大夫的首领,一样不愿意有保皇派来帮着国君,制裁我们这些卿大夫,于是对楚昭王说:“你的使者们,有比子贡更能说会道的吗?肯定没有,他们连华夏话都到不了六级。您的辅政大臣们有高尚有如颜回的吗?肯定也没有。你的将军里边,有子路那个水平的吗?肯定还是没有。你的官吏有宰我这样的吗?也是没有。从前,周文王周武王,不过一百里的土地,最后却王了天下。如果孔子借据我们楚国,有这么厉害的徒弟为辅佐,那不是楚国的福啊!”(意思是,孔子凭着他那七百个里,也非成其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气候,把咱楚国全夺去了。)
楚昭王想想,也就罢休了。不说给孔子封地命官的事了。
这也未必是楚昭王很赞同子西的话,堂堂楚国几千里,能怕孔子这一小撮流浪汉会鸠占鹊巢吗?大约不过是令尹子西很有势力,从前楚昭王亡国,被吴王阖庐打得丢了都城,全是子西等人主持着,最终复了国,既然子西不愿意用孔子,他也只好给子西面子,不用了。
孔子在楚国这里的遭遇,和在中原列国的遭遇,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君主喜欢他那一套学说,而臣子不让君主用这套办法跟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过不去。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卿族上干君权,贵族政治秩序颠倒,已是普遍现象,孔子非要给纠正回周初周文王周武王那时候的样子,是无法得逞的。
刚好这年秋天,楚昭王又死掉了。
孔子呆在郢都闲着,这一天坐车上街,又遇上一个疯子,这个人也没个名字,不过他朝孔子的车走来,接近了孔子的舆(车),于是,记录的人就管他叫“接舆”,他走过来,对孔子唱到:“凤啊凤啊,你的德为什么这么衰落啊(意思是你错了,你不应该出来当官)。你以往犯的错误已经过去了就算了(以往总想当官),未来还是来得及纠正的(赶紧离开楚国,别总想在这里找官做了)。算了算了,现在从政的都没好人,你不要跟他们掺合了。”
孔子赶紧下车,想向他辩论和解释几句,但是这狂人偏不给他说的机会,撒腿跑了。
孔子跑到各国乃至楚国想当官,行自己的道(恢复过去的好秩序和好政治),但是“接舆”劝他,现在没好人,你别干了。不过孔子想跟他辩论,意思是还是并不认同接舆的观念。
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是形势还是没给他机会,新的楚王继位,是个小孩,更没有用孔子的意思,于是孔子只好离开楚国,第五次回到卫国。这时孔子六十三岁,而鲁哀公已经在位六年。
孔子之所以一再呆在卫国,大约是卫国多贤人,比如蘧伯玉、孔文子、祝鮀、王孙贾什么的,既然贤人多,也就是卿大夫们不是很坏,对政治破坏的不是很厉害,所以孔子还愿意在这里多呆呆,几乎成了他国外的唯一据点,第二故乡了。孔子的很多弟子,也都在卫国找到了官做。比如子路随后就做了蒲城大夫(看来这个造反宣布脱离卫国的蒲城,还是又复归卫国了),所谓蒲城大夫,那就是蒲城都归他管,随后又改做了卫国大夫孔悝的家宰,即最大的家臣,负责家族封邑等内外政务。
又过了四年,冉求自从回到鲁国后,就做了季康子的季孙家的大家臣,做了季氏宰,这一年,他替季氏带兵,出去跟齐国人交战,大胜。回来之后,季肥(季康子,现任鲁国执政卿)问他:“你这打仗的本事,也是学的吗?还是本来就会。”
冉求说:“是我和孔夫子学的。”(孔子看来确实会打仗,但当时就是不教卫灵公。)
季肥说:“那我把孔老师召回来,你觉得怎么样?”
冉求说:“召他回来可以,但是来了以后,不要叫小人掣肘他,就好了。”
于是,季肥派人去卫国召孔子回来。孔子正好也在卫国混不下去了,卫国的卿卫文子(就是被孔子说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因此被谥为文的那个)要跟另一个卿打内战,要攻击卫国大夫太叔疾,问孔子怎么打好。孔子心说你至于为这事打架吗?那太叔疾本来有个媳妇,还随嫁了一个妹妹,但是媳妇的爸爸犯了错误,出逃了,孔文子就让太叔疾休了自己的媳妇,娶了孔文子的女儿,不料,太叔疾还跟前妻那个随嫁的妹妹藕断丝连,给这妻妹妹修了个宫室,整天在一起,孔文子大怒,因此要举兵打太叔疾,替自己的闺女争子。孔子心说你为了私斗的事向我请教主意,这不是污辱我吗?于是,就说:“我对这个不懂。不知道。”然后,孔子召集徒弟,就要离开卫国,说:“鸟可以选树林,焉有树林选鸟的。”喻自己为鸟。要飞走。
孔文子赶紧过来道歉,反复拉孔子留下。孔子是像鸟一样敏感的,你干一点坏事,我就要离开你。孔文子也是主卫国政事的诸卿之一。
正在这儿拉拉扯扯呢,孔子正犹豫要不要留下,这时候,鲁国季肥派来的请孔子回国的使者到了,孔子见状,更不想留了,于是,离开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结束了十四年的周游漂泊,回到了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
孔子回去以后,并没有被授予官职,大约因为太老了--他一切的从政,不过就是从前做过三年大司寇的经历。但是,鲁国人把他当国老对待,就是退休的老干部,他也是曾经为官的,所以,也接受对为政之道的咨询,发挥老干部的余光余热。
鲁哀公跑来,向他问如何为政。其实鲁哀公也不用问(他后来是被季肥驱逐了,客死越国),他也没啥政事可为。孔子说:“为政就在选臣。”这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选的都是三桓家族的季肥这帮人,没有忠于你的能人,还能做什么呢?
季肥(季康子)作为执政卿,也跑来问如何为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政,就是正啊。你带头正,谁敢不正呢?
那就是季肥不正,决策净为本家族考虑,而不是为国家考虑,自己都图私误国,下面还不都跟着。总之,算是没表扬季肥。
鲁国这时盗贼也多,季肥很为此发愁,于是又跑来问孔子,怎么对付盗贼。孔子说:“只要你不多贪欲,那么这些老百姓,你就是赏着让他们去盗,他们也不去盗。”
那意思是,你自己贪,贪图扩大家族势力和财富,下面也跟着图私,为自己捞好处,能有势力的,就抢,没有势力的,就当盗贼去劫掠和偷。都是你不正,下面人跟着学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