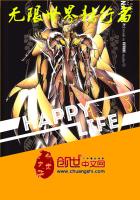马在十丈外停下,常昊王驻首遥望,隔着距离与我对视,给予安定的力量,“悦容,你没事吧。”
我冷着脸怒道:“你来这里干什么,给我走!”
他一怔,并不在意,笑道:“来救我的妻子。”
跳下马背,走了几步,又突然停下来,沉默稍许。
地下簌簌作响,骤然有无树支竹箭破土而出,他一跃往后退开。
经天子嗤笑:“子都,朕的好堂弟,接着往前走吧,让朕看看你对这个女人到底爱得有多深。”手指划过我的脸颊,冰冷的唇亲吻耳廓,我愤愤别过脸,又被他捏着下巴扳回,发狠吻住了嘴,挑衅般朝常昊王看去,眼含威胁。
常昊王面无表情,细微眯起眼睛,怒气已在双眼凝聚,一字字道:“不许你碰她!”
垂发被风遥遥吹高,翻滚的宽袖衣角,如烟波浩渺的姿态,他再度跨入阵地,任竹箭一根根刺穿他的脚掌,眉眼不眨,走出一条长长的血路。
利刃刺进了拔出,拔出了又刺进,反反复复是多么锥心的痛?为什么还能面无表情地忍下,为什么明知是刀山火海,还要义无反顾地朝我走来?
是了,这一直都是他爱我的方式。
我颤抖着,喉咙发不出一丝声响,俯下脸,再度抬头已经换上一张冷漠的表情,“赵子都,你少自作多情,我从来都不爱你,你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被我爱过的只有那双眼睛!”他错愕看我,漆黑双目忧思悲伤。我忍下心痛,冷笑道:“因为那眼睛像极了萧晚月,我心里爱的一直只有他!”所以,快走吧,离开吧,别为了我罔顾生命了。
“你说谎。”他怒挥衣袖,微红的脸庞撇转,愤怒的表情又一点一滴柔软下去,“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悦容,请你别用这样泪眼无助的表情说出好么,教我怎么相信?”
我回神,才惊觉脸上早已满是泪水。
幽柔的声音再度传来:“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也没关系,我一直都知道你心里有个人,可你知不知道,我又是怎么想的?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一个人,宠着她由着她任她予取予求,把所有最好的都捧到她面前,只恨不得连心都挖出。我就是不信,这么对一个人好,还会让她觉得有什么胜过眼前这个说爱她的人。如果……如果付出了一切,你还是念着别人,我能怎样?我还能怎样?那你就爱着他吧,就让我来爱你。”言语间,已走到我的面前,默默相望。
那耳畔的风声,悠悠似梦里的爱语,即使尝尽辛酸的滋味,也要融为一体,纵使在温情的更深处,安抚也只能带来痛楚,仍要命运狠狠相连。
泪水已模糊我的双眼,只看得见那张无怨无悔的脸。我一遍遍叫着他的名,说着对不起。
他想为我拭泪,一把剑抵在他的肩上,他却看也不看一眼,一步向前,任剑刺穿肩骨,不过是痛彻心扉,任血染红衣袍,只是开出朵朵深情的红花,也要捏起袖角,温柔地为我擦去眼泪。
“快别哭了,要知道为了让你笑,我每天要花多大的心思。”
经天子冷着脸,抽剑而出,最后抵上的是他的心窝,“多情的告别仪式结束了,再见了,赵子都。”
“不——”我厉声尖叫。
他却视死如归,星眸里带着滚烫的感动,看着我的惊慌而快乐着,笑道:“还说你不爱我,我的好悦容,你还敢说你不爱我?”
眼见剑端即将刺入,剑身却呛然两断,所有人惊住了。
偏头看去,却见云盖先生笑道:“这俩孩子的情义太让人感动了,怎舍得就这么让他们死了?棒打鸳鸯是要遭雷轰的啊!”看向经天子,请求道:“圣上,还是您牺牲吧,一个人死好过死两个。”
“什……什么?”经天子已被封了穴道,怒道:“蔺云盖,你在做什么!”
情形急转而下,让人措手不及。
云盖先生笑道:“圣上,您的戏演得那么好,怎看不出老夫演的是哪一出?”
经天子冷静下来,嘲讽道:“博取大司马信任,再将你引荐来朕的身边出谋划策,原来早就是一场阴谋,赵子都,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
常昊王却皱眉,眼中藏有不解,“他不是我的人。”
云盖先生摆袖道:“自然,凭这臭小子,还不够资格让老夫效力。”
经天子恨恨而视,一场算计到头成空,怎能不恨?就算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指使你的人是谁!”
云盖先生没有马上回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了八个字:“文武冠冕,天下无双。”
常昊王浑身一震,似受不小的惊吓,经天子竟怒极呕出一口血来,仰天大笑,嘶声喊道:“萧晚风!萧晚风!”
声音穿透天际,惊起满山飞禽,是失败的不甘,是命运的无奈,是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一个君王的悲哀。
闭目,一滴泪溅落:“到最后,朕也只能是个失败者吗?”
云盖先生开口,淡淡几句,道尽他毕生堪舆:“若在盛世,你可为一代明君,只是可惜了,生不逢时。”
他的一生,只换得一句生不逢时,何堪?
非生者无能,是苍天无情。万物皆为刍狗,何至于一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