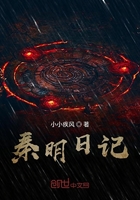相濡以沫
1953年,46岁的吴作人先生以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勘察团团长的官员身份,来到甘肃天水,来到“望之团团”、“状如积麦之垛”的麦积山石窟。这是他继考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后对西北石窟的再次考察。当然,此行也得力于“陇上文宗”冯国瑞先生的极力促成。正是冯先生热血沸腾的奔走相告,勘察团才得已抵临,麦积山石窟才有了历史上第一次详细的勘察、临摹、石模翻版等研究工作。历时月余之后,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报告》出炉,再次证实此次勘察实力雄厚,声势浩荡,堪称沉寂多年的麦积山石窟的一次复生。
其实,单从勘察团的成员名单就可知晓,此次考察可谓群贤毕至,才俊大聚,实乃麦积山石窟之大幸也。名单上分别是王朝闻、罗工柳、李瑞年等15人,其中,还有吴作人的夫人萧淑芳女士。
1953年,画家与学者兼于一身的吴作人,早已名满天下,且身兼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和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显赫身份。而1953年的萧淑芳也是声名远扬。1911年生于天津的她,自幼即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天赋。其家学深厚,他的父亲请来艺术大师齐白石先生为她治印;15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她,经其叔父、我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萧友梅推荐,进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三年时间里,她还作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在徐悲鸿工作室学习油画和素描,且时时处处得到汪慎生、汤定之和陈少鹿三位名师的指点。1937年至1940年,她远赴瑞士、英国、法国学习油画和雕塑。在这期间,她把中西方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融会贯通,兼容并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绘画技巧。回国后,即1947年起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一直在国画系任教,直至退休。
如此一位经历丰富画艺卓越的女画家,和吴作人结为夫妻,实在是天作之合,琴瑟之配。
而此良缘,却始于1946年的一次画展。
早在她师从徐悲鸿的时候,她和吴作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同班同学,那时的吴作人给萧淑芳的印象,是既腼腆又高傲,所以交往不多,仅属认识。不久,两人各自远赴国外负笈求学,天各一方,杳无音信。直到1946年,在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的一次画展的开幕式上,吴作人作为组织者迎接参展画家时,才与当时在上海市立专科学校担任美术教师的萧淑芳再次相见。经历了17年风风雨雨之后,两位老同学偶然见面,倍感亲切,说东道西,两颗心灵也随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不擅赋诗的吴作人,还欣然写了一首题为《胜利重见沪上》的五言绝句:“三月烟花乱,江南春色深。相逢情转怯,未语泪沾襟。”情深而至怯,泪流沾于襟。曾经经历了妻子产后病故的吴作人,被同样才华横溢的萧淑芳深深地打动了。
两年后,在经过一段时间充满诗情画意的心灵碰撞之后,他们在人届不惑之年终于同舟共渡,并于1948年6月5日举行了婚礼。婚礼上恭请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光临,徐悲鸿不仅担任他们的证婚人,还画了一幅《双骥图》的水墨画,当作贺礼。据资料介绍,“《双骥图》的画面上是一对昂首飞奔的骏马,翘首顾盼,腾空飞跃,寓意二人在今后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比肩奋进。”事实上,他们从1948年到1997年共同走过的半个世纪里,几乎就是在一所艺术的房间里,恩爱有加,相敬如宾。
这次,能够看到这张吴作人萧淑芳夫妇在麦积山大佛前临摹的老照片,纯属偶然。照片中的他们,风采奕奕,神情飞扬。衣着朴素的吴作人,站立,左手持画夹,右手正在描摹。另一侧,萧淑芳径直坐在栈道一角,低头临摹。齐耳的短发,渗透出一份淡定和贤惠来。他们的身边,就是麦积山石窟的东崖大佛。——我不知道,当麦积山的夏风吹到他们的身边时,他们感受到一丝清凉没有,但我知道,这风永远也不会吹散他们之间恩爱有加举案齐眉的真挚情感——后来,在萧淑芳40余载的教书生涯中,她和丈夫吴作人一起,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画坛英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但萧淑芳作为画家,她在一个伟大的男人面前,没有迷失自己,反而独自绽放出自己的光芒,这实在是一个奇迹。所以,一个柔弱女子,却能够两度作为石窟考察团中的唯一女性,远赴风沙弥漫的甘肃,在炳灵寺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临风摹佛,潜心研究。其实,何止这些呢,她甚至为了创作出以煤矿工人生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还多次深入到煤矿巷道体验生活。
他们,常常能让人想起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与张兆和、萧乾与文洁若……
手艺人的黄昏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批量生产的时代,也是一个加速度的时代,更是一个手艺之光黯然失色的时代——甚至说,这是一个舍弃心灵与灵魂的时代。在复制阔步行进在流水线作业的大道上时,想象力、个性以及独特的品质开始集体消隐和撤退。所以,当我面对这张照片时,如沐春风,如浴秋雨,仿佛回到了一个清新可爱的时代。
照片中的长髯老者,是天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雕漆技师郭力学。如今,他已驾鹤西去,魂归九泉,但1972年的他,却是多么清矍有神、慈祥和蔼。围在他身边的三位学生,想必现在也跨入耄耋之年的门槛了,但那时却正当风华正茂的年龄。齐耳的短发,朴素的花布棉袄,都是那个时代的影子。我最喜欢那三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仅暗藏了对身怀绝技的师长的尊崇,还有着一份在手艺面前应有的仰慕和谦卑。他们在一起,和谐,自然,仿佛一户贫寒人家的兄妹——就在这种耳濡目染的情景下,在老人一点一画举一反三不厌其烦的示范下,一门有着皇皇历史的手艺,传承了下来,如同一条涓涓流淌生生不息的河。
早在《诗经·秦风》里,就有“阪有漆”之说。阪者,陇坂,今天水也;漆者,漆木,一种可产漆的树木。而雕漆者,雕为手法,漆为原料。早在汉代,甘肃的天水及武都一带,就是中国雕漆的主产地之一。天水雕漆始于秦汉,既继承了古代雕漆工艺的传统,又从雕塑和绘画中吸取了营养。好多次,我在天水的深巷老街和古旧人家里,见到过一些镂雕精细的雕漆产品。年代的久远,已经让厚厚的尘土替它们发言了。而这张照片,却让我仿佛逆水而行,一脚踏进了一条涓涓不息的雕漆之河!
郭力学老人,就是这条河流里令人敬重的“水手”之一。
1972年,他一定照常去他的单位上班,照常以一位技师的身份,每天穿行于他熟悉的厂区,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毫无保留地传承下来。尽管这也是他的工作之一。早在20年前,他就在政府的支持下,和郭炳学、巨珍等27人组成了“天水市雕漆生产合作社”;1957年,又去闽、渝等地学习制漆与装饰工艺;同年8月,天水漆器第一次走出国门,从而揭开了天水雕漆史上出口的伟大篇章——如果把时间上溯四五十年甚至60年的话,正是一个个像郭力学一样的手艺人,让天水雕漆这门手艺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可是后来,为什么这条原本流之汤汤的河流日渐枯竭了?一朵花埋首于土地,它的凋零是为了重新开放。而天水雕漆呢?莫非,它也是为了脱胎换骨,为了另一种崭新的生长?但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身边,像郭力学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能够像那三个年轻学徒一样能够谦虚迷恋于一门手艺的人,就更少了,少得几近绝迹。再后来,一提到技师,人们的嘴角都会露出不屑一顾的鄙视表情。
如果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那么,人心的浮躁与功利更是每一种手艺的巨大悲哀。天水雕漆的日渐式微,常常令人不禁想起这座有着2800多年建城史的老城里业已失传的另外一些手艺,比如茜毡,比如丝织。一朵朵朴素的手艺之花在工业时代的大风中凋谢了,一个个细心而认真的养花人远去了,大地,已经是一片空寂得只剩下欲望的大地了呀!
回头一望——上世纪70年代——这段并不遥远的时光,居然是悄然降临于我们身边的一个手艺的黄昏!手艺的黄昏,是江南诗人车前子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我顺手拿来用在这里,是觉着这张照片就像是手艺人的黄昏,既有挽歌的凄清,亦有我对那个时代里为了秉承一门手艺而孜孜以求的人们的深深敬意。
是的,我多么希望这个黄昏能够停下来,像一块坏掉的钟表,永远不要滑入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