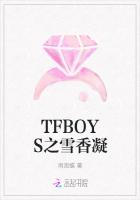一磨坊不在黄泥岗的南边,而在黄泥岗的北边老牛道尽头的一块土坎上。原来王爷在周围有好几个磨坊,黄泥岗这个磨坊处在最南面的位置上,所以被命名为南磨房。黄九经清楚地记着,南磨房原来很整齐,是全村最好的房子之一。那时三大间宽宽的西厢房,从朝向看,在这座朝东开门的院子里应该是正房,还有两间不大的北房。院子里有棵槐树,树下卧着一盘石碾。原来北房住着一位看门的老头,黄九经只知道叫瞎二,后来使劲回忆也不知道他的正式名字叫什么。瞎二在的时候磨坊那里也是一个中心,一到月圆之时几乎整夜都有磨面的人。有人说瞎二是个孤儿,年轻时就在磨坊,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就静悄悄地蒸发了,是有生产队的时候还是石磨换成电磨的时候?黄泥岗的村民在记忆里唯独没有记载这个角落里的人物。瞎二年轻时也看不出年轻来,佝偻着身子,脸上瘦瘦的,老是胡子拉碴,但多少年来他也总是那个样子。他老是睡眼惺忪的模样,没事就坐在门墩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后来生产队那会儿槐树的下面临时搭了一架牲口棚,养着一头大黑驴,瞎二负责喂喂黑驴,打扫一下卫生。在这之前没有黑驴,瞎二就靠人家磨完面挖上一瓢留下来生活。
后来磨坊那座露了窟窿的房子已经塌了的时候,黄九经又特意拜访了那里。当初那里的欢快回想起来,最先记起的就是有个叫袁龙的汉子。在黄九经看来那个袁龙是数得着的像样的汉子,在记忆里如果给所有的男人打个分,这个袁龙应该是满分。正经的劳力,身大力不亏,八尺的大汉,照时下的算法也有一百八十公分,四方大脸,眉重眼大,鼻直口宽,黑红脸膛,身上肌肉发达,手掌铁板一样。一想到他就联想到菊子姑娘。反正退休了,有时间慢慢地再回顾一下黄泥岗的旧景轶事。
眼前这处房子几乎不在人们的视野里,对这一代黄泥岗人来说,黄泥岗也只是个名字而已。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变化,这边除了满园的蒿草,没有邻近的房子,许多新盖的红砖瓦房就建在平整过的高地上。这些高地原来围着老牛道,大家争着发展经济的年代,黄泥岗得天独厚的物产资源帮了大忙,靠着老牛道的高坡上建了一溜烧砖厂,每日几口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几百号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倒,热火朝天地干,成了远近百里的建材基地,北京城九十年代盖的那些六层砖混楼的砖许多就是从这里运去的。从南磨房到老砖窑,到处都晃动着袁龙油亮的膀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袁龙的父亲老早就把他带到了黄泥岗,是解放的前一两年到的,黄九经清楚地记得这一点。老袁是外地人,生活靠在周围打短工维系,走到哪儿,吃住到哪儿,最后落户在了黄泥岗。他们一直在黄福贵家里干活,那片烧砖的大窑就是黄福贵的产业。老袁给黄九经的田里打过一季的短工,因妹夫麻黑子与村北的黄福贵并地的缘故,他见到老袁父子的机会多一些。后来大窑归了公,父子两个就住在土窑棚里。一天老袁一觉睡死了,就剩下了袁龙一个人。那时袁龙十七八岁,已经显出一个壮劳动力的架势,论干活,在黄泥岗村算是出了名的。这孩子平时话不多。早先这一带土地温润,到了麦收的时候,农民们都是将麦子连根拔起,拢上一撮向外一甩,土花四溅。一到这时袁龙就显得突出起来,一溜二十几个汉子一字排开,大家的身躯交换着猫下去挺起来,只一根烟的工夫,前后的位置就错开了。最后能够跟在袁龙前后的也就两个人。与他并排不远的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黑爷们,两个人之间有几垄的间距,双方较上劲儿,一左一右。那汉子正好右手得势,就使劲儿向他这边甩出泥土,哗哗的土块落在袁龙的头上和膀子上。这时后面打捆的女人们开始停下手里的活将目光放到前面竞赛的两个人身上。也有落在后面的男人叫喊:“大个子,反击!别太悚喽。”
袁龙的火气被挑逗起来,改为左手拔甩,一下子将土块甩到了那爷们的身上。前面金黄色的麦穗在微风中舞动,后面一片欢声笑语。在欢声笑语里偶然有一个声音很特别:“大龙使劲!”大家在欣赏竞技的同时,耳朵里也注意到了这个尖利的声音。有女人注意捜索声音的来源,才知道是从站在麦垛上不住地跺脚的菊子那里发出来的声音。毕竟大个子袁龙有后劲,不长的时间就拉开了与那汉子的距离。那些年每到这时几乎都是看袁龙表演的季节。慢慢地菊子走了心,一天要是看不见袁龙心里就慌得痛。一开始只是设法离他距离近一点看着他,后来,就翻箱倒柜,找出过年才穿的红布上衣。菊子娘见她翻腾就唠叨:“这个臭丫头,你翻腾什么。你就那么一件像样的衣服,留着串门穿,干活穿咋不惹人眼。”
菊子也有些不耐烦:“您啥都管,人家想穿穿这件衣服了。”
菊子有点撒娇的语调让母亲也自豪地微笑起来。菊子换上新衣左照照右照照,看到镜子里的红艳娇女,重新对自己进行了评价。她走到公众面前,尤其走到姐妹们的面前,穿惯了干活时的那身浅蓝色旧衣服,猛地穿上了鲜红的上衣,连她自己也觉得唐突。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办法,将那件红装套在旧衣服里,这样就穿了出去。虽然套在里面,还是被姐姐妹妹们看出来,这个说:“瞧瞧!菊子怎么了,这是要相亲呀。”那个说:“看上谁了?”
这时,留着两个小辫的菊子一扭脑袋:“不相亲就不能穿好一点的衣服?”微黑的脸蛋一下子就泛开了红晕。
“看看脸都红了,心里准是有事。”姑娘们在一起咯咯地笑开了。其实,她们心里也在猜测,村上的那些年轻人当中菊子看上谁了?不管怎么说,那时已经不像从前黄老师年轻时只由媒婆在两边传话撮合,最后结婚时好歹就要认命了。那时,至少男女如果看上了对方可以相互有机会接近。不过,还是要有一定的距离,远远地关注对方就够了。那时候就是菊子没和袁龙在一起干活,也要等午休的时候跑到袁龙干活的麦田看上他两眼。姑娘姐们儿问她去哪儿了,她就推说:“到那边找点野菜。”
后来菊子终于有机会和袁龙接近了。她被安排早晨起来熬粥,然后将两桶粥放到独轮车上送到麦田的另一头,等麦子拔到那里时打歇,加点餐,喝上两碗粥,然后再干活就有劲了。菊子老早就踏着一脚的露水赶到了田头,靠在道边的树上看着走在最前头的袁龙。这时她就有意识把崭新的红上衣露出来,老远看去那块红点极耀眼,似乎对赶在前面的袁龙也是一种激励。他很快就将手里的麦子七卷八甩地撂倒窜到了路边。他挺直了身子,两手叉腰,回头望望,那些伙计们离得还老远,就解下系在腰上的白布坎随意地擦擦汗。
“大龙,快喝粥吧,等他们赶上来也就凉了。”菊子说话的时侯故意把眼神转移到别处去。袁龙也没有在意,走向粥桶从车上小笸箩里取出白边碗就盛。这时菊子赶忙提醒道:“把勺子沉沉底,红小豆在桶底。”
袁龙依样做了,还真是如此,心里甚喜。喝了一口粥,才安静下来,发现菊子的红衣很扎眼:“嗬!衣服真红,剌眼。”
“是吗?好看吗?”菊子歪了一下头问他。只要她有一点笑,两颊的酒窝就出来,一脸的朴实和天真,黑眸子清澈见底。
“嗯!好看!”袁龙差点噎着。
她看着人们陆续赶到了眼前,就不由自主套上了旧上衣,嘴里哼唱着:“人说山西好风光……”
这时身后一阵喧闹将她的目光吸引过去,原来是几个老娘们围着要给妇女队长“看瓜”(农村的土话,意为扒裤子)。那个叫王秀兰的黑娘们儿张开嘴,露着吸烟熏得满嘴的黑牙根尤其叫得欢:“看看有没有毛,听说她是白虎。”
这个角落的欢闹吸引了一个叫“大扁脸”的青年农民,他的正式名字叫王大成。其他男性农民也注意到了那群老娘儿们在做什么游戏,只是围在一起嬉笑一番,他们知道这是需要回避的事。而王大成却迈着脚步向这边走来。有一个女人尖叫:“别过来!”
“干啥呢,看看新鲜。”王大成回答,眼睛笑眯眯的。
王秀兰急了:“什么都看!滚回去!看瞎了眼。”
那王秀兰还有个外号叫母老虎,性情泼辣,人们都知道她的那个老爷们被她管教得服服帖帖,王大成必有耳闻,一下就给震慑住了,脚步停在了原地。那群欢乐游戏的女人们也收了手,妇女队长站起来半带玩笑地说:“别笑闹了,看见没有,大成都急了。”她一边说一边系裤子,又不住地掸身上的土。
一场田野里的欢乐就这样被大成搅黄了。菊子见这阵势早掩面离开了,回到她的小车旁。临走时,她又向人群投出捜寻的目光,看看袁龙在哪儿,而袁龙正在目送自己。因为有相当长的距离,不必将视线移开,她走几步就下意识地回一下头,直到人群和麦田都成了视野里的一片色块。这时她才停下来,看着头顶上的白云慢悠悠地在湛蓝的天空中游荡,心里愉悦得很。
农业时代的麦收季节,农民们通常起得早,在地里干一个来回就收活了,那时也就到了正午时分。当袁龙再返回地头时,他感到了疲劳,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他还纳闷:“平时这点活不算什么,也没有觉出累来,今天是怎么啦?”
他不由得注视一下后面的道路,顺着道路寻找过去,树林间一架牛车正慢悠悠地穿行其间,远远地飘来甩鞭花的声音,车慢慢地变小,消失在绿荫里。他意识到,那是菊子留下影子的地方。当他将目光投向前面,眼前只剩下一垄摇晃的麦子,其他的社员都开始往家里赶,谁也没有兴趣去关注袁龙如何落到了最后。
那年,在菊子的人生履历上是重要的一页,在她的记忆里标上了鲜明的彩色符号。当一个女孩爱上一个男人,虽说最后也可以说出许多理由,但最初只能靠感觉,她无异于用这样的感觉为自己的命运下了一个赌注,因为世界上的母性天生就具有依赖更强的力量作为自己的坚强依靠的本能。菊子的神经正好运行在这个感觉阶段,她是朴实的,这样的身体优势在以后的日子里足以抵消生计的问题,甚至使她隐隐地觉得将来自己的孩子也会那样强壮吧?这一阵子,菊子就是在快乐的遐想中度过的。
不过袁龙还没有那样的感觉,他只是注意一下她,之后就回到他的窑棚,打开封好的小煤炉用铁锅熬上两碗粥,喝过之后,洗洗脚就上炕睡觉了。不过觉过半夜一片红钻进了他的眼里,他却始终没看到着一身红衣的女人的脸,只是觉得那红袖子不停撩拂而过,又窜出一阵嘲笑。于是他费力去抓,终究没有抓到。那团红一直飘到高空就不见了。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他总感觉有件事没弄清楚。通常一个人要是有心思,生活就不会如常推进。果然,在完成半天的活计时,他没有像通常那样最先到达地块的边沿。事实上他在向前面的道路上巡视,然而没有看到那片鲜红色彩,午休的粥是一位中年妇女送来的。他失望了,只是草草地喝了一碗就倒在麦垛上休息了。就连有麻雀在他的旁边啄食麦穗他也无心去理。
菊子病了,她感到头很沉,就没有到大柳树下集中。虽然病了,但这一夜的美梦使她有时间在家里躺着慢慢地回味。娘那时并不老,一直就在揣摩自己的女儿有什么心事,也不断地盘算着该给女儿找个主嫁出去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老话吗:“女孩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她特地给女儿做了一碗鸡蛋汤,临上工之前特别嘱咐躺在床上的菊子醒来时把它吃掉,告诉她:“如果觉得不好就去看看大夫。”
她哪里知道女儿做的梦,醒来时,这个梦的回味远胜于鸡蛋汤的味道。“那个救了小兔的人是谁呢?”她在努力回想梦的情节。
“真有意思,我到底是兔子还是我有一只兔子?”她禁不住自语。
于是她又从消失的梦境里找了一遍:“起风了,我是一片云,落到地上飘忽忽地滚动,怀里抱着一只雪白的兔子。不知从哪里追出一个蓬头垢面一身黑衣的魔鬼,那个魔鬼好高大,一直就跟在旁边,用利爪抓我,只差那么一点,好害怕。就是一个巨大的影子,闪过去,还能见到一丝光线,一会儿就又淹在魔影里。身上汗津津的,努力甩开魔影,身子在被子里蜷缩着。就要落入魔掌的时候,前面遇上一棵树,也是巨大的树,是一个屏障,飘忽的云。在它的前面我就变成了一只小精灵般的兔子,那魔影不断地企图抓住小兔子。就在小兔子焦急万分的时候,从树上伸出一只手,将它装进树洞里。魔影没了,心里踏实了许多。”
女人的心细,她能够想出一些特有的方式抓住梦想。
那一年的好收成就要到手的最后几天,袁龙知道,过了这几天自己又要回到窑上孤独地挖坯子,他希望麦收的时间再长一点。当他一大早站在麦垄前,真是不愿意很快就让漂浮的金黄色希望倒下。
当远方的红点在绿色的背景下跳动,就像火种投向干柴,烈焰怦然腾起。袁龙甩开膀子,心底里憋足了劲儿,闷着头加快了左右手甩动的频率,但见土花翻飞,片刻工夫就蹿上去了。这样的节奏就是那些男人们看着也具有魅力,何况对于女人,一定吸引了她们的眼球。大家注视着他,这时候有人发现前面鲜亮的红色,就有人说:“菊子在前头等着他。“也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他没家没业的,菊子能看上他?准是为了先捞到桶底的红小豆。”
不管怎样,就在大家分心去议论袁龙的时候,袁龙早就跑到了地头。心里太爽快了,回头看看,别人还差得远。当他习惯地用小帆布挂坎擦汗时,菊子的脸不由地红了,她将事先准备好的毛巾递了过去。袁龙愣了一下:“不用了,先喝点粥吧。”
“看你那劲儿,干活像野马似的,擦汗倒像刺猬那样缩起来了,又不要你钱。”菊子数落一通。
话赶上了只好照办,于是就擦了,袁龙的嗅觉里充满浓浓的香气:“这是用了多少香皂哇!”
他比画一下,不忍心让一身臭汗气污染了那块香毛巾,就还给了菊子。菊子心里也快活起来。
后来大家围上来,不知谁冒出一句:“哥哥妹妹好开心。”
“别瞎说,瞎说小心大耳光子扇你。”袁龙看菊子羞臊地躲到了一边就警告着,也就没人敢再冒犯了。不过,这句话使他在菊子心里又加重了砝码。
那一年是个好年景,每个家庭都分到了很多的小麦,于是,南磨房出奇地忙碌。那时这里才通了电,晚上在十五瓦的灯泡下整宿都有人在磨面。公家就分配一头驴为农民磨面,当然是要排队的。正好轮上菊子家用驴子,黄九经排在她家后面,吃力地推着磨。那时孩子还小不顶用,开国还拿着一个柳条玩游戏,把他爹当牲口赶,顾小慧就不断地提醒:“别在这儿捣乱,干不了活就别添乱。”
黄九经一直在农村教书,就算也经常干点农活,力气也小得多,所以,没有持久力,绕几圈就要歇一会儿。这时老婆又要唠叨了:“干脆改天叫黑子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