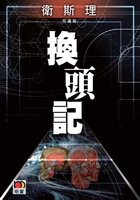处女地上的耕作人
太阳升起来了,它金黄灿白、狗红。他叫它我的雄鹰,我叫它我的太阳。他叫它我的松柏,我叫它我的喷泉;他叫它我的钟乳,我叫它我的岩浆。他使我在凉爽的天气灼热,他使我不生病时眩晕,他使我幸福时体验死亡。他教我画出一个男人,又教我画出一个女人;他教我体验一个男人,又教我学会做一个女人。他使我懂得了那一个幽谷之深,懂得了那寻求充满、再充满的要求。他使我知道了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死亡的深渊,一个美丽的陷阱;每一个男人都会在那深谷前变得勇于探索勇于献身,即使那是一座坟墓,也会不惜一切。他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自身。
我以为那就是爱情,我并不知道那其实不只是爱情。那是什么,我后来才知道。
春天来了,群燕已从南国向着北方飞翔,它们的峰影在蓝天上飘移、浮动,我痴痴地望着,望着,在纸上画出了一幅画:
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
春天是性感的季节,尼姑庵里的老树又开始吐叶伸枝了。那些嫩缴的小树叶像一只只舌头在粗壮的枝桠上唱歌。唱来了齊多许多的小鸟,唱来了浓浓的绿色。
我和母亲依旧在庭院西南角的小屋过着幽静而有秩序的生活。搿天,她一清早伴着邻居家半导体收音机发出的七点整的鸣声去上班。我由于所就读的中学离家不远,所以每天比母亲迟半点钟去上学。马上就要高考了,我除了背书还是背书,每一天都是一级战斗准备,应付那无尽无休的预考。烦躁、紧张、疲倦、按部就班。我只是一架复印机,顽强地把这一天和接下来的一天复印得惟妙惟肖。
是我母亲最先打破了我们古井无波的日子的。一天,母亲回到家眼睛红红的,她不看我,一边吃晚饭一边沉浸在心思里。天暖了,庭院里一片野草的清香,庵堂里浓浓的潮气呼出来,院子里的空气又湿又重。我和母亲也学着邻居把小饭桌挪到院子里。往常,两家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这是一天里我惟一放松的时刻。
那一天,母亲不说话,我想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小声问:“妈妈,出了什么事?”母亲没吱声,晚饭吃得没滋没味,冷冷清清收了场。
夜间,母亲和我都上了自己的床,熄了灯,月亮把房子外边的一根电线或是一根晒衣服的绳子投影到房间的墙壁上,我看着它晃呀晃,晃得我昏昏欲睡。
在我刚要把一只脚迈进梦里,母亲就在她的床上出了声。“今天我碰到一个人。”
我想,我母亲在说使她眼睛哭红了的事情了,就问:“谁?”
“你不认识。在你出生之前,应该说在认识你父亲之前,我们认识的。”
“是好朋友吗?”
那边迟疑了一会儿,“就算是。”
“他什么样?”
“早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名外交官,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蔼然可亲。他的俄语说得比汉语还好。”
“为什么?”
“他出生在苏联,是一个混血儿,九岁回到中国后才学着说汉语。六十年代初他被定为特务,然后就没了音信,一直到今天。我以为他早死了,可忽然……像是从天边地角冒出来的。”
我在心里想着,这里边一定有许多许多的故事,也许与爱情有关。总之,一个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了许多经历的人,对我来讲充满了魅力。我很想陪伴母亲长长地聊下去,在这个把白天里枯燥紧张的背书生活覆盖得一丝不剩的寂天寞地的夜晚,我下定决心陪母亲聊整整一夜。可是,这个念头产生的第二分钟,我就什么也不知道地睡着了。那时候的睡眠年轻得要命,说睡就睡着了,睡着了就又沉又香。那一夜,我母亲说了很久很久,说了什么我自然没听见。我后来想,我母亲其实也不一定需要我听着,她陷入了深深的往昔回忆之中。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一天比一天回家晚了。晚饭的时候到了,她没有回来;天上挂满星星,幽蓝苍穹昏昏欲睡了,她没有回来;我坐在庭院里等呀等,天空已经快使人想起《半夜鸡叫》的电影了,母亲还没有回来。
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常常打架,那女人的叫声传过来震耳欲聋。然后是摔东西的声音。最初,那女人总是拣茶杯、饭碗等便宜且破碎声大的东西摔,渐渐地这些东西就摔得所剩无几,于是摔的东西日日升级,由花盆、暖水瓶到搪瓷汤盆,由小闹钟到大衣柜镜子。随着摔东西的爆破声,紧接着就是那小儿子撕人心肝的哭叫声,然后女人抱起吓破胆的小儿子,夺门而出,以一声山崩地裂的甩门声宣告这一场战争的结束。她抱了孩子回娘家去了。
这个程序是我听了多少遍之后总结出来的。他们的战争每每唤起我经历过的家庭战争的记忆。
他的女人一日一日不回家,我的母亲也是左等右等不回来。于是,他开始邀请我到他的饭桌上吃晚饭。我心里不痛快,头痛、烦闷,一丁点食欲也没有,几乎是拒绝吃什么东西。正是夏天的傍晚,吃饭前他就把背心脱了,光着上身,只穿一条运动短裤。他的上身看上去光滑而结实,肩膀很宽,胸肌发达,凸显出来,下边是平坦的腹部。我忽然觉得那平坦的腹部是一片杳无人烟的空地,是一片供人休息的地方,是一片辽阔的发源地,那辽阔使我感动。看着他把小盆那样大的满满一碗面条不知不觉间全倒进了肚子里,真是令我吃惊。男人竟是这么大的饭量。再身他的赝部;仍像什么东西邰没吃一样平坦而辽阔。我想,那些面条都吃到哪里去了呢?
他吃完了面条站进米,说:“你怎么像一只小病猫一样,什么东西都不吃呢?”他捏丁魏的脖颈,又说:“看看,我稍稍使点劲简直可以把你的脖子捏断了。”然后他又在我的脖颈上捏了好几下。
这下我遇到魔力了。本来我的头一直隐隐地在疼,连带眼眶也是沉沉的,有一种张不开眼睛的感觉。可是,忽然之间,他的那只在我后脖颈上的手便把这一切不适感带走了。我一下子清爽起来。我看着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这时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了以后,有一次我问了他,他说这其实并不是魔力,那是穴位的缘故。他是医生,当然懂得这些。在我那个年龄,他简直是一座丰富的矿藏。
他的房间里有不少医书。那时,我正犯着痛经的毛病。
我大着胆子向他借来一些妇科医书。那些书里有许多许多插图,全是妇科学里女人的身体部位。书里还有许多性知识,那些名词我还不大懂得,但我觉得比起历史课本里的枯燥无味的名词好记得多。那些名词使我紧张又兴奋,使我躁动不安。人们都说小时候记忆力好,小时候背下的诗文终生不忘。这真是经验之谈。因为那时候,在强烈的剌激中记下的名词,我至今记忆犹新,且会没齿不忘。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在谈论个性这个话题时,曾经指出我个性上的一个缺陷,他说我是一个严重的思想大于行动的人,我的思想永远激进活跃地走在前边,而行动却迟迟不来。他总是能够把具体提炼成抽象,令我自愧弗如,令我迷恋。可是,他不知道,我的这个特点也是与生俱来一一在我的性经验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我的性知识已经可以编写婚前手册了。
在那个时候,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在等待我呼唤我,这个世界是他给予我的。最使我感到一种“交流”的,是书上涂满了他的痕迹一些小字,诸如临床表现、药物服量等等注释。这些小字使我觉得异样的亲切。那是一种不言而喻、秘而不宣的交流,一种心领神会、心到神知的默契。一种隐秘的东西在我和他之间诞生了。
那样一个似乎觉醒而又没有完全觉醒的少女,孤寂从来都是她的伴侣。现在,一种新的求知欲望又向她袭来。缱绻燠热的夏季的空气像水一样裹着她的身体,她感到潮湿的气流在她的体内遨游,那气流使她变得迟钝木讷,使她停止思索。那气流变得有声有色、有形有量,那气流在她的身外身内身上身下绵绵爬行。她想象那气流是手,是肌肤,是嘴,是头发,是呼吸是体重……夏季,庭院里绿色的风也变得懒散,土地变得饥渴。在那个废弃了的尼姑庵里,在那个隐藏在一株株阔大茂密的老树荫下的小西南屋里,她毫不留情地把自己脱得寸丝不挂。她像一条瘦伶伶鲜嫩嫩的光滑的鱼,被晒在金黄灿灿的沙滩上,远离供给她食物和生命的海水。她躺在被汗水浸湿的床上,拿着一面镜子对照着妇科书认识自己。镜子上上下下移动,她的手指在身体上代表着另外一个手。她不认识这柔软的手,这烧红的面颊;她不认识这光滑的肌肤,流泪的眼睛,胸壁上绽开的坚实的乳房。
她就那样孤零零躺在床上,她不认识这柔弱绵软的身体,她不知道自己在认识什么……
这个比我大将近二十岁的男人,忽然之间在我眼里英俊挺拔起来。
周末,无论他的女人是否和他有战争,她都是要抱着小儿子回娘家去的;周末,母亲肯定是要在“半夜鸡叫”以后才回来;周末,我们这些面临高考的书本的苦役犯,肯定是要放假整整一个晚上的。
有一个周末,晚饭后我来到他的房间看电视。我们并肩坐在一只长沙发上,我穿着一条月白色的柔姿纱花纹长裙,他把电扇调到最低档,徐徐的风在我和他的身上流连忘返、荡来漾去,我的裙子便在身体上鼓荡翻飞。平时,我很不喜欢电风扇,那种人造风使我全身发紧,头疼而烦躁。但是,这一天晚上,柔软的长裙在我身体上像一只最轻柔的手臂,我觉得惬意无比。为了避免蚊子,他熄灭了房间里的灯,只有电视屏幕上五颜六色的光在我们身上和空气中闪烁不定,左右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