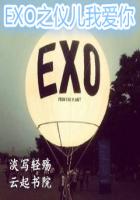黛二小姐心中忽然升起一片温情,这情感像一道光芒,使她的理智欲从身体里退出,使之像一只虫子那样从她那沉寂的脚底脱离出去。她仿佛站在远远的地方,注视自己,她看到自己始终是一面空窗子,永远孤零零地敞开着,曾经有人沉入过那面窗子,但那种沉入使她无所适从,比没人沉入更为孤寂,于是她便坚定地摆脱了它;现在,终于有一个她渴望的人伫立窗前了,正向那面窗子里边窥望,这忽然降临的一切使黛二小姐内心盈满起来。这时,黛二似乎听到上方一种模模糊糊的声音在召唤她,同时她切身感到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上。这只手真实的触摸,立刻改变了局势,把她彻底拉出了理智之外的真实。黛二忽然觉得自己是个病弱无助的小女孩,正软弱无力地渴求着气功师那散发着阳光的身体进入她的显得阴郁的身体,进入她颤抖湿润的呼吸,进入她的企盼色彩的魂灵;她渴望他用心灵的手臂将她紧紧抱住,引导她飞翔,整日整夜地飞翔。她终干把他的手向自己拉了过来……黛二闭上了眼睛。
气功师开始解她的外衣和裙带,然后是她的内衣、内裤。黛二没有反抗。一切在缓慢地进行。当她那由于痩削而显得缺乏松软的皎白光滑的肢体赤裸地躺在他眼萷的一瞬间,她几乎把自己封闭了许多年的心灵也交付出来,赤裸出来。这种突然而来的全身心的投降与缴械之感立刻将她吞没……
黛二小姐起来的时候,惫志重新回到她身上,她的脸上透出淡淡的羞涩。她想把话题引开去,引到她感兴趣的关于宇宙间神秘力量上边去,远离刚才那种令人难为情的事情。可气功师却神秘莫测地在一旁暗自发笑,并不想谈什么。
黛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你不想跟我谈谈吗?”
“我们谈什么?”
“比如气功。比如很多。”黛二低下头。“当然。你,嗯,是个可爱的姑娘。可是,很遗憾,我必须先……嗯,我也许不该告诉你,我的,嗯,实验成功了。”
“什么实验?”
“刚才的事情。有关中枢神经系统和某个穴位的发现……还有,嗯,某种诱导的传递……”
黛二小姐愣住了,然后她的脸颊红涨起来,她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半天没出声。然后,她慢慢站起来,走过去,走到气功师面前:“这么说,我该祝贺你了?”黛二的眼里射出冷冷的光芒。她很想在他的脸上来一个耳光,说一句“请接受我的祝贺!”然后离开。但那张脸颊对着她充满了温情与愧疚,她从未见过一张这样打动她的脸。黛二望着他,她无法抵抗他的魅力。黛二转身向房门走去。
“请别走!”气功师艰难地出了声,“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嗯,我们可以谈谈吗?如果你允许我重新开始。”
黛二转回身,看着他。半天,她说:“重新什么?实验?做爱?”
“别想得那么糟。你需要帮助。这种头疼不像拔掉—颗坏牙那么简单。你同时还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忧虑、多思,学会放松,不能总心事重重。生活嘛,往往……”
“好了,我知道怎样生活。我很好。再见。”
黛二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午日的阳光像一头猛兽,一下子把黛二小姐光秃秃地亮在空旷里。清晨那温情、虚幻的薄雾遁去了。肮脏的街赤裸裸地平躺在阳光里。黛二仰起头,空中的高压线、电线以及从楼群的窗子里像一只只手臂倾斜伸出的众多的电话线,密密麻麻地在城市的上空铺展开一张罗网,高大的楼群像一个个巨人傲慢地高出这张罗网,低垂着头颜俯视着它。黛二小姐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城市若这般发展下去,再过几年,当有人从楼顶纵身眺下来想结束她年轻或年迈的生命时,恐怕难以实现她的夙愿了―自杀者的身体会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从楼顶滑落下来,然后一头撞在罗网上,一股强大的向下压力和脆弱的向上弹力抗衡了一下,罗网便被冲破了,自杀者被反作用力缓冲了一下,然后不重地落在大地上,她的身子扭曲地滚动一阵,然后像个失败者一样爬起来走掉。黛二小姐不知为何忽然想象出这样一个场面。
她拐进一条静僻的荒径,这荒径的一侧满是野草、垃圾和废弃的铁板;另一侧是稀稀落落的几间破败的平房,似乎是民工们的集本宿舍或堆放工具的仓库。一条弯曲别样的铁轨向着小径深处爬去。面对眼前这种荒漠孤寂、忧心忡忡的景致,面对这种最易使人的内心陷入回忆,又的情调,黛二没有像以往那样习惯性地沉浸到悲观^,躬是嘲讽地对自己笑了一下。
黛二小姐为自己这呰日子以来充满想象的荒废日子感到好笑。当她平展肢体仰卧在气功师充满魔力的注视之下叫,他的声音,他的气息,他的诱导几乎把她的精神和肉体佥邹调动起来,她甚至觉得儿年来苦苦寻索的东西终〒魔幻般岀现了。她几乎把这种获得视为一种信仰的获得。可是忽然之间,那一切就崩溃了,像一声冷笑从脸上悠然滑落,散去,那感觉瞬息之间便轰然丧失。她又成了一个人。
黛二小姐的胃部剧烈抽动了一下,然后是一声细微的空鸣。她想起自己从昨天晚饭后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饥饿感提醒她已是午饭时候了。然而,黛二却没有一点吃东西的欲望,她迅速登上一辆通往市中心的汽车,向墨非那个报社驶去。黛二去找副社长老刘了。
黛二带着一股愤怒的微笑,朝报社大门口荷枪而立的门卫打招呼,她把自己调整到相当随便和熟悉的神态,仿佛是每天出出进进的工作人员或宿舍家属,这样可以免去麻烦的登记。然而,黛二并没能蒙混过去,门卫把她从出出进进的几个人中一眼识出来,叫住。于是,黛二便只好乖乖登记,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大名和副社长老刘的大名分别写在“来访者”和“探望人”两个栏目里。进了大门,黛二就后悔起来,怎么那么听话呢?又不查证件,写个什么名字不行!她一边想着一边敲响了老刘的房门。
老刘见了黛二自是一番长辈亲情,先回忆了与黛教授生前的莫逆之情,然后是一番人生苦短、好人命薄的感叹,再然后落到黛二的工作问题上,人毕竟不是棋子,墨非这盘棋的谋划未能顺利如愿,堵塞胶滞当然出现在中间环节正社长身上。至今,副社长老刘并没有收到正社长转推过来的黛二的材料。黛二觉得不对,那边说转交了,这边说并没收到,这里边有一个人在说I荒。这时,老刘说,兴许正社长给“谁谁”通了信儿以后,就把这信压在抽屉里忘了。黛二望望老刘,觉得他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于是,她请老刘想办法从侧面启发一下正社长,可老刘说不行。他说正社长风里来雨里去,革命经验相当丰富,嗅觉灵敏之极,任何一种不触痛痒的侧面启发,都会立刻弓I起正社长的警觉,从而识破老刘与黛二早已暗中勾结,只是想拿他正社长当眺板的诡计。黛二对老刘说,干脆别绕圈子了,您就直接自荐自批得了,我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只想要一份工作。老刘立刻面带难色,支支吾吾重新说起他在社里能够立得住脚全仗那个法宝的道理。老刘给黛二出了个主意,他让黛二打着“谁谁”的旗号去正社长家探望,送一份礼物就说是“谁谁”让带给他的。这事肯定就行了。黛二这才猛然想起来,“谁谁”的家还欠着一次“探望”呢。于是,她点了点头,谢了老刘走了出来。
一出报社大门,黛二小姐就望见一群人围观着一只漂亮的长毛黄狗。街上人头攒动,川流不息。黛二想,人们活得真是越来越聪明了,未来的日子养狗的也会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学会喂养各式各样的狗了^无所事事的狗,肥头大耳的狗,满腹经纶的狗,唯命是听的狗,狗仗人势的狗……
老实说,黛二小姐并不想要什么工作,她正在做着与本性相悖的又一次努力。她只是想挣钱从而获得生活的独立;只是想向别人证明她并不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而处处都逃跑;证明她也具有一个被社会认同的女子的社会价值。她知道只要她活着,就得靣对这一切,无处可逃,也无处告别。
空气沉闷起来。街道两侧的白杨树高得有些触目惊心,从很高的上空洒下被风撒动的叶子的刷刷声,那声音高深莫测,仿佛使人感到这个世界危机四伏,许多潜在的危险随时会从头顶倾压下来。
一阵猛烈的抽痛从黛二小姐的胃部散射出来。她被疼痛压迫得踉踉跄跄,远远看上去俨然一个病弱的老妪。路旁正有一个电话亭,黛二吃力地溜进去。“我找墨非。”
“躲总。”
“喂,谁呀?喂?”
“喂,说话?”
“墨非,你还想带汉出去玩吗?”黛二忽然哽咽起来,她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上云淥往常一样。
“噢,黛二。那还用问!已经等你几年了。”
“……”统二的眼泪抑餿不住地流下来。“喂,到底梅呀?是黛二吗?”
“恩……”
“喂,你在干什么,黛二怎么了?”
“墨非……我累极了,饿极了。我觉得……没意思了。”
“黛二,我给你写了封长信,我们需要谈谈,你不能再这样东跑西逃了,我也不能再过这种日子了,我得和你在一起,你需要帮助。”
“黛二,你在听吗?我去接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她挂断了电话。
终于下雨了,霏霏细雨顷刻间把街面浸得湿漉漉的。初夏的洒满雨泪的街上只剩下链二小姐像一条瘦憐嶙的鱼儿踟蹰而行。她的头发淋湿了,忧郁的黑色风衣裹在她的身上。黛二弯曲着腰,把头软弱无力地歪靠在自己一侧的肩上,筋疲力尽。刚才,街上还是人影憧憧,喧闹嘈杂,忽然之间只留下黛二小姐独自倾听自己脚下的踏踏声,一股曲尽人散的荒寂和着凉凉的雨水浸透了黛二小姐的全身。
她独自在雨街走着,她把自己几年来积蓄的各种毁灭感一件一件细细数来。这种细数和品味使她感到一种自虐的快感。她在这种愉快中,一方面体味着孤独的自由,又一方面感受到不可遏制的空虚。她没有哀伤,也没有悲叹。她知道自己永远处在与世告别的恍惚之中。然而却永远无处告别;她知道己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
无论如何黛二小姐得往前走。路面上的雨水在她脚下慢慢腾起,飞溅的水珠像一只只银鸟在她脚前脚后飞舞。在雨雾中,黛二小姐仿佛远远地看到多少年以后的一个凄凉的清晨的场景:卜.早班的路人围在街角隐蔽处的一株高大苍老、绽满粉红色花朵的榕树旁,人们看到黛二小姐把自己安详地吊挂在树枝上,她那瘦瘦的肢体看上去只剩下裹在身上的黑风衣在晨风里摇摇飘荡……那是最后的充满尊严的逃亡地。
黛二小姐没有掉转身,她沿着雨街一直向前走下去。闹对自己那种满怀自怜的想象,她的嘴角卷起一丝嘲讽的微笑。
被这久违的光滑如绸的晨风一吹,裹在身上整整一个夏天的温温吞吞的汗渍忽然就干了。
清晨,首先是我的脸孔醒过来,然后我感到一些碎玻璃似的亮片剌在眼孔上。我睁大眼睛,发现亮脆而饱满的阳光已经穿过窗棂,透过习习浮动的白纱帘,把大朵大朵的不知叫做什么花的古怪图像投射到地毯上。我在床上伸了伸懶腰,把自己蜷缩了一夜的肢体像一匹布料那样展平,然后起身下地。
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转了一圈,浑身清爽,觉得今天将会有好心情。然后我就朝窗外一转身,一瞬之间,我看见了秋天。
我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怅然若失的感觉,但很快,那种抽象的空落之感就被另外一种具体然而并不清晰的欣慰之情所取代。现在,我坐在桌前,拿着笔,我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拿起笔写,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或者说严重一点,这就是我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方式。
早已过了立秋八月,但是在今天之前,整个S城就如同一座过于勤奋而不肯关门欵息的浴池,湿闷、燠热、嘈杂。三个多月以来,一条杀彩旗一样的真丝半长短裤,在我的喜欢赤裸的瘦长猫上,轮番披拴,使我看上去像一个外交事务繁忙的城市,旗杆上不断变躲异域城邦的旗帜。湿热让人无法穿上饩裙或长裤。所以,我一直拒绝日历上宣布的秋天已经到来这个规律性的说法。
直到今天早晨,我才从窗外吹落到地毯上的噼噼剥剥的阳光花身上看到了秋天。
在那一瞬间,我所以忽生一阵失落,是因为我听说地球在未来的岁月中将越来越热,热到人类无法承受,纷纷逃离,飞上其他星体,地球最终走向燃烧、毁灭。我对于这一观测充满兴奋,我渴望变化,无论往好还是往坏,变化就行。
但是,在我还没有感到如科学仪器所预测的那么炎热时,夏季就这样马马虎虎、不痛不瘅地结束了,我心里不免有点落空。而后产生的那种仿佛是近在身旁却依然模糊不清的欣慰感,也许后边我能说清。
我想我先坐在那儿,拿起笔,写什么再想。也许只要摆出写字的姿势,就能写起来,一满页一满页哗哗啦啦写下去,想停都停不住。就像你有时候并不感到饿,但你吃起来,吃着吃着你就觉得饿了,觉得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真是活得没有一点预感了。
本来睡醒觉,我想给谁打一个电话,想了想给谁,没有想准。我的目的是想约一个比较随便轻松的旧友,来家聊聊,一起做顿晚饭,喝点黑米酒,然后在一起听歌看看录像什么的。我很怕见了面就讨论哲学或艺术的人。哲学留给自己去想就够了。至于艺术,没什么可想的,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本性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朋友聚会就是为了放払、愉快的。这一时想不好给谁打电话,就耽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