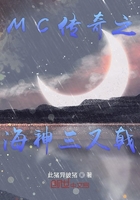少年时候,有过对于每一次学业毕业的感伤。
那时候以为离别会苦,苦到会填满这一生所有看过的海。那时世界观都很小,以为那就是我们此生全部的感情与不舍,以为会带着这样的念想过一生。而后来,发觉它渺小到不值一提,在这之后遇到的各种组织庞大的生离死别面前,毕业,甚至羞涩得抬不起头来。
但毕竟,岁月渐长,在经久的阅历里我们再也不会对离别怀有那样伤感而又虔诚的敬意了。
在一个小镇念完小学到初中。那里有一座桥,串联起每天上学必经之路。每到下雨天,前段路就会布满泥泞凹洼。而每当晴好天气,路边也是满眼绿茫茫的青草,或是田地里开满香气沁入心脾的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孤独的少年总是背着朴素的书包一个人走路上学、回家,也不怎么说话。而那时候的田间小路、石桥、街道,好似都很漫长。
如同对于年少时候友谊的小心翼翼。那是对于这个人世除了亲缘关系之外的人际亲密,最初的拾得与丢失。小时候,每当班上有同学转学走了都会怀念好久,哪怕与他并不是多么要好的玩伴,大家课间一起谈起他时还会觉得那个人好,也会在脸上挂满留恋的笑容,也会怅然若失好多天,仿佛那已经是多么深刻的再无重逢的告别。
毕业时已经开始时兴写留言册,花花绿绿硬面抄的那种一大本,在彼此的行页里,用孩童认真的字体写满幼稚而真挚的祝福、玩笑与大人们的联系方式。也会各自珍藏好多年,然后在一次又一次搬家后,发现早已无迹可寻。而那些看似漫长的田间小路、石桥、街道,在回过头去看时,也都好短好短,才拐了个弯,走了几步,就走到了尽头。
成年后回去过两次小镇,那时的小伙伴,也早已不知去往何方。
高中时随家人迁徙到县城。陌生的环境,生疏的同伴,自幼又不是善于表达自己、交往朋友的孩子,留在掌心的不过二三个朋友。后来各自南辕北辙去读大学、工作、婚娶、成家,真是《那些花儿》里唱的那样,各自奔天涯,不知道开在哪儿呀。
但清楚记得高三毕业后的那个漫长的夏天,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去远方,还是常常骑着脚踏车回到高三的旧学校操场,看着空荡荡的教室与水泥路,忽然就无限伤感与难过起来。
难过到不只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一段生命。
回来后写过一篇长长的文章用以怀念,那也是对此生永失的少年时代的祭奠。
会记得大学或许是至今最好的时光。如清亮的月,并不圆满,却曾照耀过内心。去往南京一所三流大学,是自己一直向往的城市,高中时参加省级的作文竞赛来过这儿两次,爱上她陈旧沉淀之中却又自有安稳姿态的味道,如同在泛黄的扉页上写出崭新的长句,又如同在枯丫的旧枝上开出嫩绿的初叶。这是这座城市的美,也是我的大学的原罪。
如果四年的时光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未演一场杀青戏,那么离别将不是所有文章惯用的伏笔。
那天,从某个应聘的专场出来,已是下午五点。辗转四班巴士,站了近三个小时的车程,回校,去校址附近一家酒店吃散伙饭。
算是没能赶上,到场的时候已近尾声,每张桌上都堆满残羹冷炙。
有点小饿,兑了果汁与啤酒,坐到有阴影的背光角落,就看着人群开始沸腾。有满场飞着找人舌吻的,有举着相机恨不得给每个人拍写真的,有醉酒泼骂的,有女生站在外面的广场上抱在一起哭。看着彼时喜欢着或喜欢过的人,不说话,总是静静地望着。
出来后一行人去练歌房唱通宵。三五成群松散走在夜色的街道,对着马路唱陈奕迅烂大街的口水歌《十年》。夜晚的风并不凉,有街景与路灯,倒映出斑驳的人影与脚步声。天空浮过深黑色的烟云,聚拢,又吹散,像我们停泊的四年。
而其实,与众人散伙,都不足够触及与一人离别伤心的十万分之一。这与孩童时混沌完整的离别之伤是不同的,残缺的、专注性的、指向更明确的不舍,只向一人开。于是在宽敞的KTV包厢里,离别的不舍化作词人写出来的一行行屏幕上的唱句,心心念念要在落幕时独唱给懂得那些对偶与韵脚的心上人听。莫文蔚的歌声一直一直在耳边回响:“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还说再见。”而身后众人,皆似电影场景里常用的蒙太奇技术一样,通通沦为布景与润饰。留下各怀心事的两三个当事人,谱写着“与君对唱三万场,不诉离伤”的绝世画面。顶壁上有旋转的霓虹灯,在我们的侧脸上打出流动着的明明灭灭的光。直至那光,最终式微,熄灭。
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毕业,才是成年人的告别。开始学会遗忘、将就、敷衍,欺骗和被欺骗,接受所有不圆满,并熟视无睹。
如同手指裂开的一道伤口,沾了水,洇红了肉,越发隐隐地不停歇地疼,仿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疤。
但所幸,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从来都是强大的,任何感情,任何离别,任何你在当时以为这路途好漫长的亲历过程,都会愈合,都会复原出崭新的光滑的表皮来。
由此,我们都变得强韧而空洞,隐忍而百毒不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