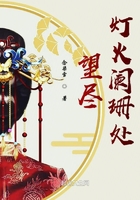翌口,一大早我就被保姆叫醒。那时我睡意正浓。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我钻在被窝里不高兴地说。
“昨晚下雪了。”
“下了?” “是呀。还在下呢。”我陡然兴奋大作,睡意顷刻间荡然无存。这时,我顾不着体面了,裹着被跳下床,小狗般欢蹦乱跳地走到窗台前。
果然,窗外大雪漫天飞扬。我的目光顺着雪花向大地飘落而去。地上已积丁一层厚厚的雪,树裹银装。一切都是白的,真别有一番风景,令我们这些南方人叹为观止。
“多美的雪景!”我不禁感叹唏嘘,“真是难得一遇。瑞雪兆丰年那!”
“这在我们老家箅是最小的雪了。”
“难得一见,哪怕再小的雪也是最精彩的。”
我驻足久久观赏。俯瞰洁白、鲜光的大地,我心豁然开朗,一片纯净。
“珍儿是否也在看下雪?”我心想,“不会那么巧两个地方同时在下雪吧。而这个季节里下雪的地方是很多的,也不无可能。对,不如打个电话问问。”
我在床头柜子上拿来电话,站在原地打。
“喂,是谁?”
“是我,珍儿。我在看下雪,你在干什么?”
“我在走山路。你说上海也下雪了?”
“对,一场好大的雪。真是太美了。你哪边呢?”
“也在下雪。”
“下雪天走山路感觉一定不错吧?”
“你在取笑我,还是什么?”
“那你干吗要在雪天走山路?”
“我得赶中午十二点的长途汽车。”
“你今天回上海?”
“是。我昨天给你打手机,想告诉你的。可没人接。”
“我昨天出去了,忘了带手机。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到上海?”
“下雪天车子可能会慢一点。估计明天凌晨三点可以!
“这样,我开车过来接你。长途汽车停在什么地方?”
“谢谢了。不用麻烦你。”
“这算什么话?”
“事先已联系好了。”
“有人接了?”
“嗯。”
“那晚上我为你接风吧。”
“晚上不是小燕子说好要聚聚吗?”
“对对,我差点给忘了。为她饯行。”
“她要出去吗?”
“她投对你说?”
“她没说,只说聚聚。好了,见了面再聊。”
“祝你一路顺风。”
我回到床上睡回笼觉,暖烘烘、懒洋洋,还有迷醉感,叉力,更有趣的是你在被窝里尽可胡思乱想。这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想象着与珍儿一起走山路的情景。
起伏的山峦,茫茫的林海,逶迤的山路,笼罩在一片白色中。
这样的白色才是原色的,自然、纯净、安详而又宁静。
下雪的时候那风是软软的,雪花无声地纷纷飘扬,又轻轻兰在仿佛酣睡的大地上,四周静谧极了。
只有我们俩踩雪的脚步声,吱咯吱咯,仿佛是大地的呓语。
我们时不时躬身抓一把雪,捏成雪团,然后冷不防往对方:扔,看雪花散开,甭提有多欢乐。笑声荡漾开来,仿佛是大地梦里的笑。
我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我迷失在一片广袤无垠的雪原,我拼命地走啊走,而雪原变得越来越大,四周除了雪还是雪。我仿佛觉得我是世界上惟一的生命。我走了一圈又一圈,到头来还是回到原地。
我想我是必死无疑。我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生的信心。我不想再走了,就原地坐下,死了也要坐直。
“你不能坐下。你必须永往直前。”当我紧闭双眼等待死神降临时,有个声音在我耳畔同荡。
我睁眼一看,在我前面有个柔美的女子身影,她是浮在雪地上面的。她手执火把。
“起来,跟着火把走。”
我没有犹豫,不由自主随她而去。
一路上,凡走过的地方,不足变成了莽莽草原,就是变成了茂密森林。我还能听到鸟语嗅到花香。但我始终没能看清她的容颜。
当走到一处满是花果的山坡上时,我忍不住问她:“你是谁?”
瞬间,我又回到了过去。
就此,我突然醒了过来。我摸了摸脸腮,证明我现在是在现实世界;接着我开始冥思浮想,找寻这梦的答案,结果一无所获。
我把被褥往下拉,我的头露了出来。
卧房里充满了阳光。阳光里飘浮着数不清的细小绒毛,丝丝闪着银光。
“雪停了。”我伸展懒腰,自言白语,“我该起来了。”
我身穿睡衣走出卧房。保姆见我先问好,接着告诉我说:“小燕子来过电活,让你醒来后给她回电。”
“几点了。”我边问边走向沙发。
“十点三刻。”
我慢悠悠地坐下,并没马上打电话,而是思索着给她打手机还是打电话。我不清楚她今天是不是去了公司。我想她后天就要离开上海,应该住家准备行装才是。最后,我还是决定打她手机。然而手机怎么也打不通,总占线。
“怎么同事。”我说着,就站起身来,准备去梳洗。可没等我离开几步电话铃声响了。“喂。”“懒虫。起床了吗?”“刚起床。”我说着带着一个长长的哈欠。“我刚打过你手机,总占线。”
“我也存打你电话。我十分种后在公寓楼下等你。”
“有什么事吗?”
“我得买一只旅行包,我要你陪我挑选。”
我爽快答应了她。最后,我突然想起起本《挪威的森林》。
“我一直没时问看。”
“那你把它带过来。
“我想带到重庆去看。”
她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想随便她还不还我,大不了我再去买一本得了。那天我在新华书店叉买了一本,顺便还买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最新作品《海边的卡夫卡》。
我陪她一连走了几家商店,最后总算在一家专卖店一眼看中了一只,款式新颖,色泽典雅,质地一流,但价格不菲小燕子俨然是行家里手,与店主讨价还价,我则在一旁说一些鼓动性的话,至于说了些什么,我已无从忆起。
小燕子丽对这只带有轮子的旅行包真是喜不胜收。一路拖着一路夸它不止。我为了取悦于她,也一个劲地称好。当然,所有的 好也莫过于我说“你的眼力真是一绝”这一句话,我见她听了后喜样子。我从未见她如此高兴过。 而她要了牛肉面。彼此都吃得津津有味。
马路上的积雪融化得很快,零星的雪堆像似大地的疙瘩。树枝还是那么光秃秃、干巴巴,迎着寒风摇曳不止。
这里门庭若市,但很有秩序,不见繁杂、喧哗。
我们还要了两杯热可可,在那里闲聊开来。
“不知道重庆那边的天气怎么样?”我不无担心地问。
“我看过天气预报,和上海差不多。不过即便再糟也无所谓,反正到了那边也不怎么往外跑,办事处设在一个高级写字楼内,空调总还是有的。我去半个月就回上海。我们是打头阵,做做准备工作,真正运作那是过了年的事。”
“我现在最担心你在那边吃住不习惯。”
“我最喜欢吃川菜。”
“那是难得吃一次。”
“这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大不了自己做饭,辛苦点而已。
你还没吃过我做的饭荣吧。”
“你省省吧。你就是什么都乐观。”
“人生短暂,何苦悲观。我以为活着就得惟乐,当然对我们女人而言惟美才是最主要的。”
“人们说,上海的空气是最滋润温和的,这对你们女人的皮肤有好处。”
“重庆也可以呀。我发现重庆小姐的皮肤也很光泽滋润的,绝不亚于上海小姐。”“反正我是没见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