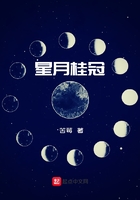屋里。
福晋展臂,垂眼看着朔雪替自己换上单衣。却听见外面一阵动静,主仆两人相视一眼,福晋对着外面扬了扬下巴,朔雪会意,出去见是苏培盛的徒弟小喜子。朔雪只道是四阿哥要来福晋这里,先是喜上眉梢,未说话先带了三分笑。
小喜子一望便知她会错了意,只能苦笑着喘道:“朔雪姐姐,四爷吩咐……”
福晋在里间听得不甚分明,不一会儿见朔雪进了来,面色间似有为难,福晋奇道:“怎么了?外面谁?”,朔雪低声道:“福晋,武格格生病了,贝勒爷让现在就开库房,说是……拿药材。”安嬷嬷开了库房,拿了药材,让小喜子捧了去,武宁屋子里安静得一丝声响也无,珠棋送出了宗大夫,又回身催着下面小太监去膳房看着药,想想还是不放心,又叫着清明、荷田跟了去。
武宁躺在床帐中,宗大夫道只是寻常的风寒发热,几服药下去也就好了,那病初时并未觉怎样,发起来却是头晕得厉害。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
四阿哥让苏培盛将前院书房里没看完的文卷拿了来,俯在武宁房里桌案上看着。他怕扰了武宁休息,只点了暗暗的一盏纱灯,一只窗缝里飞进的小飞虫绕着那纱灯打了打转儿,落在了纸上,正被四阿哥提笔的墨点溶了。
武宁自梦里醒过来,便看见四阿哥坐在窗下桌前,桌上幽幽萤灯,背影挺直。武宁微微动了动身子,珠棋原是守在床尾的,见武宁欲要起身,连忙上前道:“主子再躺躺,药一会就送到、”四阿哥听见动静,也放下笔,走过来弯腰将额头与武宁碰了碰,柔声道:“总是要受个两三天的罪的,越是许久没病,越是发得厉害。”,武宁看了他一眼,心道这算是什么安慰?伸手想要掀开身上被子,四阿哥连忙按住,道:“做甚么?”
武宁抬手擦了擦额上的汗,道:“太厚了,快热死了。”,四阿哥重新将她按下,又覆好被子道:“发了汗才好。”不一会儿药果然送来了,珠棋举了托盘送上,四阿哥亲手端了药碗,扶起武宁,让她靠在自己怀里。
武宁自四阿哥怀里直起身来,垂眼道:“我自己来。”,四阿哥却似没听见一般,舀了一勺药送到嘴边,轻轻吹了气,不容置喙地送到武宁唇边,见她果然满头是汗,连脖子上都湿滑得尽是冷汗珠子,便接了热手巾帮她细细擦了,武宁喝了药,刚要躺下,那药味极苦地从胸腔中冲出,武宁立刻捂住了嘴,珠棋见状,赶紧送上铜盆,武宁连连推着四阿哥走开,意思是不想让他看到自己丑态,四阿哥轻轻抚拍着她后背,道:“吐出来舒服些。”,武宁强忍着不适,低声道:“爷出去吧。”
四阿哥无奈,只得起身,珠棋蹲身道:“奴才定好好照顾主子,请贝勒爷放心!”,四阿哥这才去了。到了前院,想了想,却让苏培盛将那膳房给武宁做点心的师傅叫了来。
苏培盛急忙去了,那膳房点心师傅听闻是贝勒爷叫唤,不敢丝毫怠慢,起了身就随着苏培盛到了前院,四阿哥细细问了他武氏这几日饮食。点心师傅来时已听闻苏培盛道武氏急病一事,又想起这一晚武氏的贴身婢女珠棋的确是在自己这里拿了许多甜点心,还笑言道主子只爱吃点心,连正经饭菜都不好好用了。一时额头微汗,战战兢兢地说不出话来,四阿哥不管问什么,他只一味道“是。”
四阿哥默不作声,端详他神色良久,兴味索然地摆了摆手,道:“起来罢。”,那点心师傅才站起身,仍是不敢直腰,偷偷抬眼见四阿哥已经翻起桌案上书卷,一旁苏培盛对着他猛使眼色,这才告退了溜着墙边出去,方抬手长喘出了一口气,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武宁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四阿哥从此以后,却是在膳房中直接定了人,拨给了武宁自己的小厨房,让他们专门服侍着武氏这一位主子。
康熙四十七年,夏。
福晋的院子门口,一左一右地站了两个小太监,正拿着竹竿子去粘那树上的知了,白光光的太阳晒得地皮滚烫,一脚踩上去都能感受到热意。
屋里怔忪摆了一座三足铜鼎,冰山凉气森森。
四阿哥抬脚一进门,先往冰山边站了一会儿,福晋还在午睡,却是没料到这位稀客,慌慌张张地整了装出来,连脸上的香粉都没有擦匀,带了一身的脂粉香味。四阿哥也不点破,自拣了张椅子坐下,低头啜了一口茶,随意将茶盏搁在冰山边的八角案上,方道:“在抄经?”
福晋愣了一愣,方反应过来四阿哥是在跟她问话。刚要答话,四阿哥已经站起了身,在屋中走了几步。他贪凉,难免往冰山那里去,福晋见他背后衣料汗湿了老大一片,生怕他着了凉,有意想提醒又不敢。只见四阿哥右手拇指上的扳指,在昏暗的屋里闪着碧绿幽光。
四阿哥悠悠道:“皇阿玛今日方下了旨意,今年的巡视塞外,我要陪驾前往,也许十一月才能回京。”,福晋听出他话里苗头,心里有些不定,抬头望向四阿哥道::“贝勒爷……”,果然四阿哥朗声接着道:“武氏一路随侍,府里却是要你多劳心了。”
福晋嗫嚅了一下嘴唇,寂然望向四阿哥,半晌方干涩着嗓子道:“武格格身子骨向来虚弱,这一路都在塞外,好几个月,妾身担心她……”,四阿哥截断她话语,道:“去年的木兰秋狝,她也是跟着的,一路的规矩是习惯了的。”,福晋听四阿哥语音坚决,不敢再说什么,只能顺着四阿哥的意思道:“贝勒爷所言极是,武妹妹向来是个知规矩懂礼的,有她服侍着爷,我也放心。”
四阿哥又说了些其他事情,便离了福晋正院,福晋见他难得来一趟,不顾着院子里下人,追出去带了些恳求道:“爷不在这里用膳吗?用过午膳再去书房也不迟。”,四阿哥脚步一顿,见她一脸哀求,心里不忍,触目之处又尽是下人,不好拂了福晋面子,便点头道:“也好。”
在临近塞外巡幸的最后几天里,武宁院子里一片繁忙。
珠棋兴奋地收拾着武宁的衣装行李,武宁微笑着坐在一边看着,笑道:“行了行了,哪用得着这么多?”,珠棋抬头对她笑了笑,道:“主子,这个您听奴才一句劝,出门在外不比平常,缺了什么东西,有银子也买不到,现下带得越多越全备,到时候就越放心。”
武宁抬手在脸上轻轻比划了一下,道:“珠棋正是越来越有管家奶奶的风范了!”,珠棋跺脚笑道:“主子!奴才一心为您!您倒好,拿奴才取笑。”,武宁笑着走过去道:“好珠棋,快整罢!”,又看其中一个包裹里装满药香,道:“这是什么?”
珠棋看了一眼,道:“回主子,那是熏虫的。”,武宁嗯了一声,将那药香凑到鼻子下,深深吸了一口气,道:“倒是清香得很。”,珠棋抬手轻轻擦了擦头上的汗,道:“主子再想想,可有什么遗漏的?这出了门就不好补了。”
武宁见她如临大敌,轻轻拍了拍她肩膀安慰道:“去年的木兰秋狝,你也是帮我整理过行装的,又不是头一次。”
几日后。
皇上出巡,御林军驻守在城外,密密麻麻,天光未明,淡月如水,铠甲流光。
四阿哥早早地便去了宫里——他要随着万岁的仪仗从宫里一起出来,武宁作为贝勒爷随行人员,只要从贝勒府出发,到了城外会合就行。两人分了两路。
夜里,四阿哥前脚刚走,武宁后脚就装扮了起来,珠棋见她满面倦容,忍不住道:“主子,天色还早,您在矮榻上歪一会儿?”
武宁强撑着精神摇了摇头,怕自己一不小心睡过去了,误了时辰。主仆两人就坐在这房里,一直等到天光大亮,才被通知着要出发了。武宁去正院向福晋道了别,又听了附近一番不痛不痒的嘱咐外,便被人拥着上了马车——珠棋和武宁坐同一辆车,方便伺候主子,其他几个婢女则坐在另一辆车上,两辆车前后相邻,剩下的几辆车都是行李车。
车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贝勒府,隔着窗纱,武宁能看见街上一片肃静,到处都是身板挺直,骑着高头大马不住逡巡的侍卫们,眼神扫过各处屋顶房角。
车队愈行愈远,渐渐出了城,终于追上了康熙的圣驾。浩野无际,满天黄沙扑过。背后的紫禁城沉默地蛰伏在风沙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