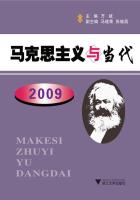以上就是《端木与萧红》中有关端木抛下妻子离去的事件的记述。端木的离去,并不是出于他的自私,而是在萧红的吩咐下走的。诚然,在这里,端木也有着他的懦弱。他本可以以丈夫的强硬不听妻子的话,留下来陪着她;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端木如此做也是为了迁就萧红,不想妻子忧虑,也不想她因担心过度而伤了身体。若是从这方面看,可以看出萧红与端木是互敬互爱的。
可是,世人都觉得,丈夫照顾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紧要关头,男方就应该承担家里的一切难事,就应该是家中的顶梁柱。可他们也忽略了妻子体贴丈夫也是人之常情。爱着丈夫的妻子,哪一个不设心处地地为他着想?爱到深处,就算叫她去吃子弹,她也愿意。再加上,这个妻子是萧红,是一个为爱所痴的女人,一个追求自由又不愿被男人看低的女人。她在危难关头,一定是站在了男女平等的角度上,站在你我一样、并无性别之分的角度上,带着爱意让端木先走的。
在端木上船之前,他一定带着不舍与爱意,深深拥抱自己的妻子,就像他之后在医院里拥抱妻子一样,把她拥进自己那能融化一切的温暖怀抱。
所谓良人到头来也不过是水中捞月
1939年底,萧红与端木已来到了重庆。这一年,重庆也逃不过战火,四处烟火弥漫。
这天晚上,重庆上空又出现了日本轰炸机。“呜呼——呜呼——”尖锐的警报声响彻天空,敲击着人们的心房。
“快跑啊,飞机来了!”有人敲打着萧红的门。很快,这声音就出现在了别处,没过多久,这声音也不再喊了,被一阵阵的跑步声替代。
萧红听到声音,马上放下笔,抓了几张刚才写的稿纸,一边走一边往身上塞,紧跟在端木身后。她抬头看着天空,没有看到敌机,只见城市中灯光一闪一闪,像指示灯一样指引着道路。即使这些灯光真的是指示灯,有没有也是一样。每天,警报都会响一次,萧红走惯了,闭上眼睛都能走到防空洞。
她跑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没多久就要缓下脚步,或者要靠着墙停一停,缓一口气再接着跑。虽然附近的防空洞并不远,可萧红走起来还是十分吃力。她不仅仅要跑,还要避开人群的推搡,还要跟着人群跑,否则在惊慌的时候,人推人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接着就是人踩人。
端木跟着萧红一起跑的时候,他会牵着萧红一路小跑。端木看上去不是体育健将,可跑起来双腿像是装了翅膀一样,跑得飞快。他一只手牵着萧红,一只手拿着备用包。有时候,他见拉不动萧红,也会心急地说:“快点吧,飞机就来了。”
萧红还没缓过气来,又要急匆匆地跟着跑起来。
安然无恙地跑去防空洞,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防空洞里人多嘈杂,潮湿阴暗,空气稀薄,还弥漫着紧张。在这里要是不注意,也会发生人踏人的事。
每次,萧红都会选一个靠近出口的地方,尽量呼吸着外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实在让人受不了,有几次她都呕吐起来。
这次,她与端木一起被后面的人群推涌着,不知不觉走到了防空洞深处。萧红看着四周全是一张张茫然的脸孔,不禁抓紧了端木的手。那是一张张漠然到盲目的脸孔!白得可怕!冷得可怕!
空气中混杂着汗味与污秽物等各种腥臭味,萧红垫高了脚,想呼吸来自上方的空气。她觉得自己的肺部越来越难受。
等到出去的时候,萧红迫不及待地跟着人群往外走。她当时患有肺病,渴望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在无意中,她被人绊倒了。她摔了下去,趴在地上站不起来,身边的人流分成两拨,没有一点空余的地方让她能支撑着站起来。
“乃莹!乃莹!你在哪里?”她听到端木在叫她。她大声叫:“我在这里呢,在地下。”终于,端木看到了她,一把把她拉了起来。
萧红站稳脚后,发现自己的双手湿湿的,一看是鲜红的血,伤口上还混着泥沙。她拍一拍手,说回家包扎一下就好。但是,对于这次的事故,她还是心有余悸。
后来,她跟端木商量,不如再次出走。每天这样躲防空洞,不仅影响她写作,还让她的病情加重。端木也觉得的确如此。于是,俩人便商量着要去哪里。
当时,文化界人士一般聚集在桂林与香港。俩人就这两个地方商量起来。端木是主张去桂林的,他说:“你想,现在桂林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像胡愈之、千家驹、张铁生、范长江、郭沫若、夏衍、巴金、艾青、田汉、叶圣陶等,都是我们认识的。去到那里,如果有需要,他们也许会乐于帮忙。”
萧红摇了摇头,说:“桂林那边是有很多朋友,可是我就怕桂林那边时局也不够稳定,你看,广州沦陷了,武汉沦陷了,现在重庆又整天被轰炸,照着这个局势,恐怕日军还会向西南推进。到时,又要从桂林转移。不如去香港,比起来,会稳当些。”
那时候,《新华日报》的副总编辑华岗也建议他们:“看形势,你们还是到香港避一避较好。”于是,俩人与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后,就乘着飞机,在1940年初飞到了香港。
初到香港,端木就与重庆复旦大学的董事长孙寒冰先生取得联系,在他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这位孙寒冰先生,在香港办了一份《经济评论》杂志,让端木为他编其中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和《时代文学》。
事实上,端木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他本想着到了香港,能够安静下来,不如潜心写作,不用为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奔波,也能好好照料有病在身的萧红。不过,又想到初来乍到,家里也需要用钱,再加上朋友们的怂恿与支持,他就答应了。
这样便接下了这份工作,也就埋下了一个隐患。他与萧红的感情被这忙碌的工作阻挡了。
端木没有想到这些,只是潜心工作。最后,经过多方努力,《时代文学》赢得了一些非常有才干的左派文学家的支持,像上海的许广平与巴人,还有丁玲,都会为杂志写稿。一下子,《时代文学》强大的作者阵容震动了香港文坛,成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刊物。
在这段时间,萧红不用每天去跑防空洞,她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写作了,尽管这时候,她还需要分一部分精力去抵抗她的病。对于香港这座南方城市,萧红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倒也不是喜欢,也不是讨厌,而是在二者的拔河中,常常会生出另外一种异样感觉。
“也许,是这里天气热的时候太热,不像重庆,不像武汉,更不像呼兰河。”来到了香港,她总会不自觉地想到呼兰河。“绝对不是想念,那地方已经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了。如果可以,我倒希望能看一看爷爷的墓。”
在被这种别样思绪主宰着的时候,萧红拿起了笔,写下了她人生中最重要作品之一《呼兰河传》。在写作时间里,萧红专心而专注,对身外事一点也不在乎,而对端木的早出晚归也不以为意。也许这就是作家们的通病,当他们通过写作来治疗内心的创伤时,对周围的世界就都冷漠得可怕。
此时,外界传说称端木与萧红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他们认为,萧红对于端木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感情,随着相处时间的加长,他们俩人性格中的差异性,成了他们婚姻的绊脚石。
端木看似软弱,但他绝不是一个软皮球,他也有着自己的原则,就如同萧红所认为的,他是软中有硬。加上他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娇生惯养,性格中不免也有缺陷。萧红年纪轻轻就离家出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日子,使得她在弱女子的外表下有着自己的坚强与倔强。如此俩人,在婚姻生活中,没有一人忍让的话,绝对会有不少矛盾。话说回来,夫妻之间,哪一对是没有一点矛盾的呢?
就在各种矛盾中,俩人无论是感情还是婚姻,多少都出现了问题。冷漠出现在这对夫妻当中,他们俩虽住在一起,对话次数却越来越少。由于不适应香港潮湿的空气,萧红的肺病越来越严重。
终于,她不得不住进了玛丽医院。
现在看来,肺病是一种不大不小的病,绝对是能够治愈的。可是,在当时,患上肺病,就等同于患上了绝症。依据当时的情况,玛丽医院让萧红接受阳台空气疗法。这种疗法,实际上就是让萧红多吹吹冷风。
但是,这种疗法让萧红觉得不适应。医院就又尝试了多种办法,就连当时最先进的打空气针治疗法,也让萧红尝试。
站在冷风中,萧红的身子骨受不了。打空气针,她的肺部又痛得受不了。此时,端木为了筹集医药费,很少到医院去探望萧红,这让萧红有了怨言:“再怎么忙,你也可以抽时间来看看我啊,白天筹集医院费,晚上就不能来看我吗?”端木沉默了,她说得对,再忙,他也应该来医院多看看病中的妻子。但是,他每次来到医院,闻到那一阵阵的消毒药水味,就会反胃。他觉得消毒水的味道似乎捆绑在了萧红身上,让她成了一具失去生命力的形体。他害怕这股味道,更害怕看到萧红没有血色的脸。像逃避他们婚姻出现的问题一样,他也逃避着去见萧红。
“医院不是讨人喜欢的地方,先生已经算是尽心尽力了。”旁边的护士帮着劝解。
“我真恨你。”萧红看着端木,一字一顿地说。其实,她并不是真的恨,不过是病重的人的一种发泄。她天天躺在医院,没有欢乐,只能呆望着天花板,还要忍受各种治疗带来的痛苦。她需要更多的关怀与爱护,可端木呢,只想到了现实问题,没有及时给予妻子精神上的关怀。
那些本就对端木有怨言的人们,就当然地认为做丈夫的打算要再次抛妻弃子,甚至把阳台空气疗法当作对萧红的虐待。端木没有虐待过萧红,即使感情上已经疏远了她,他也希望萧红能尽快好起来。他也四处寻师问药,还经朋友介绍,找到了替宋庆龄看过病的大夫为萧红治疗。只可惜,这位大夫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萧红的生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殆尽,被病魔牢牢地抓住。偶尔像离水的鱼儿般扑腾几下,随即又沉寂下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不少医院被日军征用。端木产生了恐惧,怕日军会抓他们这些左派文学家,就想为萧红寻找一个没有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同时,他的心里也产生了突围的想法。
“突围?”萧红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惊讶地问丈夫。她睁大眼睛,眼里写满了恐惧。
“我知道,你是要离开我了。”萧红黯然地说。
“没有的事,我想带着你突围,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那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为什么你把我扔给骆宾基,就对我不管不顾了?”
“我不是不管你,你住院需要医药费,我要给你筹钱,再说,我也在忙着给你联系一家没被日军接管的医院。”端木内疚起来,继续说着,“我还要回到我们的住处,整理我们的东西,像你的《呼兰河传》这些手稿,我都想整理好。”
“那些东西重要,还是我重要?”萧红质问着。她不解,有一个卧床的妻子,为什么做丈夫的只想着这些无关紧要之事。在病床上,萧红也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对于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只有偶尔产生不甘的情绪时,才会重新点燃求生意志。除此之外,她不过只是想能有一个人陪伴在自己身边,跟自己说说话,在痛得厉害时能握着她的手,跟她说有他在。这个人,本该是端木,可偏偏由一个年轻的骆宾基代办了。由此滋生出的巨大失落,是萧红说不出口的。
在念着端木时,萧红也会生恨,她不只对端木说出她的恨,她也会写下她的恨。她在孤独寂寥之时,叫人拿来了纸,认认真真地在上面写道:我恨端木。
真的恨吗?那是当然的。那个最应该出现的人,却久久不露面,怎能叫她不恨?端木让她想到了曾经抛弃她的未婚夫,曾经朝思暮想的萧军,曾经爱着她又远去了的祖父。那是一个个拥她进入生活,又一个个抛她而去的人。
那端木呢?即使俩人的婚姻存在矛盾,可也不至于令端木心狠到极点,置妻子的死活于不顾吧?那倒不会,毕竟在萧红死后的十八年他才再娶,且在十年动荡之后,他也是年年都去祭拜前妻的陵墓。如果说他对萧红没有爱,这是绝对不合情理的。
也许,那时候的端木的确是被懦弱的性格攫住了,他害怕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害怕医院,也害怕看到萧红如同僵尸般的病态。同时,他也需要取款、筹钱,去为突围准备好一切。就这样,他在有意无意之中,错过了萧红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四天。
不少人会为萧红喊冤,数落端木的懦弱。其实,人们在唏嘘和怜惜萧红的悲剧之余,或许更应该存有一份包容之心,去理解在面临天灾人祸时人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