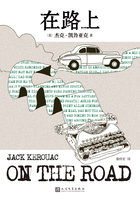式欧见这房间收拾得十分精雅,四壁图书插架,满目琳琅,分明是个书房。又从一个书架旁边的小门,走进一间精室。里面依然是书房模样,却只多了一付床帐,想是西席先生的所居。看屋内的光景,却又不像有人常住的。那仆人送进来一壶茶,道了安置,便自去了。式欧关了房门,顾不得许多,上床便睡。才觉得浑身骨节酸疼,但因方才所受的惊恐过深,刺激过重。脑中不易平静,倒睡不着。想起最近所经历的事,只觉得七乱八糟,没一件事有些条理,仿佛糊里糊涂地做了许多可笑而又可怕的梦。想起来心中麻乱得很。再向前途思量,那更黑暗暗像一团漆,说不定那一时便被人捉了去,当做乱党处治。即使幸而没事,此地也非久居之处。以一个逋逃中的罪人,又向那里取寻归宿。若回北京家里,原无不可。不过当初我所以离家,是因为受了刺激。那芷华飘泊无依,病在我家。我不合对她生了爱情,及至向她求爱,竟遭她拒绝,弄得两下都很难堪。我虽然吃了她的没味,可是对她怜悯之心,绝未消灭。觉得在那时情形之下,她定不愿再和我相见,必要迁出我家。可怜她久病初愈之身,怎禁得住再去飘泊风尘?不如我直截了当的离开家庭,让她伴着我妹同居,便可安住下去,所以我才跑到天津。如今芷华想还和淑敏相处,自然都很快乐,我一回去,那芷华怕我还去缠绕,定又要走。那我岂不是无形中回去赶她么?看来我便是能返北京,也不可仓卒家去。又想起自己倘然能早在天津娶了家室,带回家去,芷华见我爱情已有寄托,或者不致再行避忌。可惜那祁姨太太和柳如眉两件事,都成了虚话。想到这里,又想起在医院葡萄架上所听的秘语,自己十有八九是被柳如眉所害。却又想不出她所以要害自己的原因,如此左思右想的好大工夫。直到天色大明,方才睡着,一觉睡到晌午大后。起床时就有仆人进来服侍着洗过了脸,迟一会便开上饭来。式欧见只摆着一付杯箸,暗想主人不出来陪也罢了,他原是个官僚。那有工夫应酬我。怎房正梁也不见面?我与他共同患难,又同寄居在他的朋友家中,岂能不稍稍照应一下?便问那服侍的仆人道:“昨天同我一道来的房先生呢?怎么不见?莫非还睡着没醒?”那仆人怔了一怔才道:“房先生出门去了。”式欧暗想他原是到此地来躲灾避难,怎能在这危险期间,倒大胆出去闲逛?但又转想到房正梁本是个行踪诡秘的角色,他既敢出门,自有他的把握。说不定化装易服才出去的。便也不再问,自己吃过了饭,自己闷在房里,无事可做,又因在他人家中,不便到房外走串。只得从书架上寻了些合于脾胃的书,看着解阅,直到了日落黄昏,还不见房正梁的影儿。及至摆上晚饭,却是两付杯箸。式欧以为必是房正梁回来了,正好和他谈谈以后的办法。那知迟了一会,门帘一启,一个人手托水烟袋进来,满面笑容向式欧点点头。那里是房正梁?却是本宅里主人余亦舒。
式欧想不到他那样官气十足的人,居然还出来陪客,连忙起立致礼。余亦舒却十分客气,随便谈了几句,便同座用饭。式欧记挂着房正梁,忍不住就向余亦舒问起,余亦舒正色道。“候一会吃过饭细谈,我还有话要向阁下说呢。”式欧不便再问,只得陪他东拉西扯的闲话。直到饭后,余亦舒才让式欧同到了小客厅,他自己吸过六七个鸦片烟,过足了瘾,方向式欧道:“阁下是阴错阳差的和正梁打成一路,其中情形我很明白。无奈官中人已把阁下认作正梁同党,目下阁下身体很是危险,请留神一些。至于正梁恐怕已不易见面,此刻若见着他,只恐阁下也要入狱咧。?式欧听他的话音有异,愕然问道:“怎么说?正梁已经遇险了么?”余亦舒脸上毫无表情地笑了一笑,道:“阁下很年轻,我叨大叫你声老弟。老弟,不瞒你说,今天早晨,我就给侦缉队去了个电话,叫人把他抓去了。现在他大约已脚镣手铐的收起来咧。”式欧原在烟榻上坐着,听了这话,不觉霍然跳起几乎惊异得叫起来。但又猛然想到现在余亦舒家里,不可放肆,忙又悄没声的重复坐下,吃吃的问道:“怎……怎……的……正梁不是您的老朋友……”余亦舒冷笑道:“老弟,不明白我们的内幕,大约还以为我是卖友求荣呢。你再慢慢听我细说。说句实话,当初我和正梁原是一个党系的同人,论理我不该卖他,可是我也有我的难处。自从我们那个势力失败以后,凡是剩下几个钱的,全抱着胳膊忍了。惟有房正梁因为当初得势的时候不会搂钱,所以到如今还赤手空拳,故而野心不死,只管暗地活动,预备恢复旧日的势力。无奈他素常就仗着向旧同事打抽丰度日,那有钱活动?于是乎我们这一般人就捣霉了。他向我们筹款,拿我们的钱去活动,我们原也盼他成了功。把我们的旧首领拥起来,大家再辉煌一阵,所以都量力帮助。那知房正梁始终图谋不成,却只管向大家索款,大家都疲于应付,有许多都躲到上海去了。只有我因特别原故,离不开天津,没奈何只得受他的逼勒。这两年中已被房正梁零碎讨去了三四万块钱。你想,我们作官的钱是容易得来的么?无声无臭的耗去了这许多,谁能不心疼?后来我想有这些钱,现在运动个像样的差使也用之不尽,何必再填房正梁这无底的漏洞。因此就翻然改计,不再理会房正梁这笔帐。恰巧我有个旧日运使任上用的文案张尔孔,如今阔了,升到此地的捐务处长,又兼着督军署的参议,是尚督军的红人。前些日他来访我,我和他当初同做过许多利害相关的事,处得感情很好,无话不谈。便托他给走个门路,再弄个官儿做做,他答应了,但因我是敌派的旧人。若没个机会,不便向尚督军开口。后来谈到房正梁一节事,我也不瞒他,便把内情都说了。他说这是个好机会。房正梁是尚督军最嫉恨的人,若能把房正梁献出去,尚督军可一定欢喜,也可表明反正的诚心,就以此做个进身之阶,便是不用一支运动费,也包可得一个美缺。而旦推荐的人也容易进言。我听了张尔孔的话,想了想这理儿也对,这种年头儿,没有皇上,忠字也跟着取消,武将倒戈是家常便饭。我们做文官的,另巴结个上司,更不成问题。不过卖了房正梁有些过意不去。但又想到若不卖他,他也永远叫我不得清静。而且他们做武官的,不定杀了多少人,造了多少孽,害了他不为缺德。再说他花我的钱,已够运动一个阔差使的费用。他既不能还我的钱,我就用他的身体去给我捐官,于报施之道也很说得通。所以就答应了张尔孔。在最近等机会便相机行事,谁知近日房正梁因官面上察缉得紧,竟绝迹不到我这里来。我也不知道他移居何处,正在焦急,昨天他竟同你来了。这还不是礼物自送上门。我当时稳住了他,就暗地叫人把他捉了去。张尔孔方才来访,许我在一星期内可以发出差使。你明白了?就是这么件事。”说着又吸起烟来。
式欧听得又怕又气,暗想你还说不是卖友求荣,这不是卖友求荣是什么?难为他还能老着脸皮说出来。自己因昨夜曾同房正梁共过患难,觉得房正梁人很直爽,对他感情颇好。如今听得他已被当局的奸人陷害,不由愤气填胸,恨不得抓过余亦舒饱打一顿。但想到自己也尚在余亦舒掌握之中,此身尚不知祸福如何,不觉又嗒然气丧。只把眼瞅着余亦舒,见他那满面奸恶之气,十分可怕。猛然又疑惑像他这样神奸巨猾,当然城府很深,既然卖了。房正梁,何不连我一同卖了?落个斩草除根。即使他因和我无仇无恨,发了侧隐之心,放过了我,也就罢了。怎忽的又对我这陌生的人,把隐事都宣布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式欧正在疑惑,余亦舒擎着烟枪坐起,迷缝着眼说道:“老弟,你见我收拾了房正梁,必还怕我不肯饶你,那你请放宽心。一来我不作这有伤阴骘的事,二来我见你少年英俊,正是有用的材料,正有事用你帮忙呢。不然时又何必把我的秘密都向你说明?可有一样,现在你不能出门,只要一离这里,立刻就有危险。我因为护庇你,所以今天早晨,先把侦缉队人们伏在门外,然后把房正梁赚出去,才动手的。方才侦缉队还有电话来问,你是不是也在这里?我回说除房正梁以外,并无他人。然而他们也未必肯信,不过不敢进门来搜。只是你可要特别小心,只要一出离这个宅门,便要踏进狱门。那时我就没法救你了。”式欧听完毛发悚然,觉得这余亦舒真是个戴着假面具的魔鬼,厌恶他到了十分。可是惧怕他也到了极点。又从害怕了生出了仪注,连忙悚然立起,诚惶诚恐的改了称呼道:“余大人,谢谢您搭救我。”余亦舒倒笑道:“老弟,何必这样?我既救你就要救到底。只要你对我忠心任事,我自不当你外人看待。”式欧道:“大人,方才说有事用我,不知是什么事?”余亦舒方开口要说,又沉吟道:“那倒不忙,那事我正在筹划,还未实行,等用你时再细谈。你先休息几日,不过切记不可出门。”说着把烟灯吹熄,道:“我要出门去办事,你今天移到这屋里来睡吧。昨天你睡的房间是小女们的书室,因为今天她们不在家,所以你占着不妨。明天她们都回来,要上课了,你还是挪过来方便。”式欧唯唯答应。
等余亦舒出门以后,式欧翻来覆去的比昨夜加倍不宁。余亦舒那样大奸大恶的人,把害人当作闲耍一般,自己却托庇在他宇下,受他的保护。据他说有用自己之处,又不知他用我去作何事。而且象他这样妖鬼等类的人,能有什么好事可做?说不定更有想不到的怪事,那时我若不依他去做,当然还要害我。如今分明已落在陷阱之中。余亦舒行为诡秘,绝不是个好相识。为今之计,真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是余亦舒既然轻描淡写地收拾了房正梁,却卫护着我,而且对我大有推心置腹之概,这里面定然另有作用。他那一方面必已布置周密,绝不会轻易放我走。而且便是逃出余亦舒的手掌,到外边也躲不开官人们的罗网,真是去住两难,避退维谷,把个式欧愁得心怀麻乱。后来才决定主意,跑出门去便是凶多吉少,住在这里,虽然祸福还不可知,到底总比立刻鎯铛入狱的好。万一事情生了变化,或是余亦舒竟大发慈悲,把自己救出去,也许有之。当下便忍着千般愁苦,住在这小客厅里,直转侧到天明方得睡着。
次日醒时,天色已近中午。在枕上便听得对面书室里有许多女人的声音,莺声燕语的,像是正在讲论学业,料得是余亦舒的女儿们正在上课。便悄悄起床,唤进仆人,洗漱过了。自己连客厅门也不敢出,好容易听这些女郎们都过后楼去吃午饭,式欧才敢出去走动,回来仍自闷在屋里。过了一会,那些女郎仍回到书室上课,式欧寂寞无聊,就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闻听书声解闷。只听她们载笑载言,像是师生们的感情十分融洽。半晌才又听出有两三个略带南方口音的女郎是学生,一个满口流利官话而喉音清脆的女郎是教师。这时正讲的是西洋史,中国话里夹着英文名词,事理阐发得十分晓畅,说话儿更得婉妙动听。式欧听得竟入了神,暗想女教师居然有如此通才,真是难得。西洋史讲完,休息一会,接着又讲起女诫来。这女教师却并不依着书本解释,只准着人情物理,把意义譬解得透明雪亮,既不陈腐,也不浮薄,式欧更自佩服。到了天近四点,有个女学生向教师称说今天要到个亲戚家拜寿,要早些退席。那教师用很和蔼的声音答道:“好。我还要在这儿看一会儿书,你们不必管我,就先去吧。”那些女生还向教师恋恋不台地说笑,不肯便走。那教师又温语敦促道:“你们既有事,快去吧。”
式欧听到这里,脑中猛然一阵颤动,通身的神经都跳了一下,猛然想起,这种声音和语气,以先似也有人向自己如此说过。再一寻恩,又触起思绪,脑中深深的映出一个人影,不觉痴然立起,急于要晓得对面书室中的教师,是否是自己所认识的人。就着窗帘隙缝向外面看时,恰见三个女郎从书室走出,个个都是玉貌锦衣,富丽非常,都向门外而去,接着便听门外汽车声动。式欧料到这三个少女定是余亦舒的家属,现在出门应酬。那教师还在书室未走,恨不得立刻闯进书室,去看个明白,才一举步,忙又停住。暗道:“不妥,莫说室中倘不是我所料及的人,枉自讨个没趣。即使果然是她,想起当初的事,我已没有和她见面的可能。如今卒然对面,有什么可说?岂不更是无趣。再说我离家时,她还同我妹妹一起住着,乍会也来到此间?世上那有这等巧事?这不过是我疑心生暗鬼罢了。”便暗暗自己叫道:“式欧式欧,你现在正是颠沛流离,顾命还来不及,还想这些闲事。怎的满当她是你所想的人,你又能怎样?趁早歇了心吧。”想到这里。就要转身到榻上假寐一会,但因想到目前处境的危险,又从对面书室中人生出希望。猛一回想,我也不可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