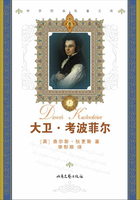在小说的高潮与冲突到来之前,我还必须补叙几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那是我完成本小说几名主要人物最终形成之悲剧所万万不可遗漏的。
其一、关于那个悬空架于过街楼上的阁楼。阁楼是在高斌被强制送往少年管教所之后一年,高斌的生父姓范的司机坠崖死亡后不到一个月,就由平正明公开露面、亲自上门设计并且率领一帮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四号公众之众目睽睽之下,仅用了三天时间,就高速度高质量地搭成了的。阁楼搭成当天,那帮十七八岁的学生子竟还将两挂一千发的电光鞭炮从过街楼上长长地悬挂到弄堂口的地上,不顾社会公德不顾市政府关于在市中心严禁燃放鞭炮的三令五申,同时点燃,声震环宇地足足炸了五分钟之久。四号门口所有的人都抱头鼠窜,弄堂两边的窗户都开启过伸出过好奇的脑袋继而紧紧关闭,拍手叫好赛如过节过年的只有一帮子戴红领巾绿领巾的小娃娃们。电光炮响声刚停硝烟尚未散尽,那几个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学生子们就从四号一拥而出,送他们出门洞的竟是数年前在本弄一度被活捉被关注被久久地讨论过的新闻人物——那个新寡不满一月的高丽蓉和家有妻小头发花白快当爷爷的平正明。他们俩并肩站在四号门口,与学生子们一个个握手言别,口称“谢谢”,面上带笑,简直就像一对立于饭店酒楼大门口迎送宾客的新婚夫妇!弄堂里的人见了这么有声有色的一幕,当时没一个说什么的,从第二天起则言论鼎沸,民愤难平,厨房里弄堂里嘁嘁喳喳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嘻嘻笑笑之外,竟还有三封匿名信分别寄到平正明的学校、高丽蓉的学校,还有当地的房管所。前两封揭发“一对狗男女伤风败俗”,后一封呼吁房管部门制止乱搭违章建筑。三封信都没引起什么事端来。平正明的学校对平、高两人的事早因过于熟悉而了无兴趣了,况且五十多岁的平正明帮人家搭房造屋,毕竟与“风化”事难以划等号,一封匿名信何以定罪。高丽蓉的学校更是无动于衷。高丽蓉工作多年任劳任怨,教的班级升学率特高而且还常出个把在区里市里获这奖那奖的尖子人才,学校里本来就应该考虑解决她住房困难的问题了,如今有人帮她自力更生就地多出了一间房来,学校里高兴轻松还来不及呢!弄堂居民好瞎嚼舌头,高丽蓉所在学校的校长心里明白,匿名信到手看过就撕掉扔掉,提也不与别人提一下。房管所则派人来阁楼视察了一下。但搭阁楼前高丽蓉是递过申请报告而且得到批准的,那过街楼虽小但高,中间加了一层木板,一间变成了两间,根本就不用对原房结构伤筋动骨。那房管所的青工来看了一圈马上就表了态,说是符合搭建要求,只是这架上阁楼的木梯子不妨做成活动的,可以更隐蔽些,免得架在明处有碍观瞻。高丽蓉请他抽了一支当年很时兴的“云烟”,满面笑容地送他出门,把那位写这封匿名信的林教导气得几乎闭过气去。他只写过这一封信。实在是因为阁楼一搭,他的窥探视野无疑缩小了一半以上,而且在他想来,这个阁楼,完全是为了平正明与高丽蓉公开姘居而搭的!
说出来又有谁能相信呢?平正明自从那次被当众“活捉”之后,就此失去了性功能。他寻过不少医生,吃过不少偏方,但无一奏效最后只好认命。他与自己的患肾病的妻子早已分床,而老天又让那种足以从机能上枪毙一个男子汉的打击猝然降临到他头上而且果真就这么结束了他肉体上的男子使命。他与高丽蓉从此转而成为柏拉图的信徒。高丽蓉对此反而欣喜,并且自我解放地认为她与他几近乎“凤凰涅槃”,从此摆脱了罪孽感。范司机一死,她愈加感到了一种几十年没有过的轻松,她决心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搭个阁楼给自己住;楼下的正房待儿子高斌返回后就再装修一下,若干年后作为他的新房。没有了那个失去理性的酒徒丈夫,她可以放心大胆地接待平正明了,她想。她自欺欺人地认为,反正如今早已没有了肉体关系,不就是个朋友吗?不就是自己过去的老师吗?谁还能说三道四呢?所以阁楼搭成之后,她就与平正明重新恢复了公开往来,全然不顾那种锥子般的目光了。
随之需要补充说明的第二个细节是:高斌从少管所出来后,何以高丽蓉又躲躲闪闪贼头狗脑地努力在儿子面前隐瞒掩盖她与平正明的来往。这个责任在高斌身上。高斌当年亲见的那床上一幕,成为他理解母亲与平正明关系的惟一形象阐释。他回家的第一天,因为一进厨房就又感受到满脑袋长满了锥子般的目光,所以当即于晚间闯到平正明的家里,当了他那病弱的老妻和已经娶了媳妇的儿子的面,将一把水果刀扎进了他们全家吃饭的小圆台面。“听着,”他说,“不要让我在兴业路上看见你!你的脑袋不会比这张台面硬!”如此穷凶极恶的恫吓,足以惊破高丽蓉的美梦和勇气了,原本已经很公开的正常交往不得不转为地下转为秘密,并且因为偷偷摸摸,真的好像不干不净起来,且不说别的吧,就说平正明殒命那天吧,高丽蓉是因为胃疼发作而未能上班,家里的“三九胃泰”又刚刚服完,所以在高斌去上班之后,就打了个公用电话给平正明,问平正明能否给弄一盒药来,这药对自己还是挺有效的。平正明说,我下午就到一个学生那儿去一次,他的妻子是街道医院的护士,有办法弄到,我拿到了就给你送来,只是,只是……高丽蓉马上接口道,小斌不回来吃晚饭的,我早上问过他,你来吧,我给你准备个剥皮蹄髈装进饭盒,你们全家不是都喜欢吃我烧的蹄髈吗?由于高丽蓉一个下午都因胃寒焐在被子里,所以高斌闯入时被褥零乱;由于高丽蓉正与平正明谈到儿子与自己的隔阂而忍不住流了泪,所以儿子冲人时她是脸红红的眼睛水汪汪的;由于那个高高架于空中的阁楼很隐蔽,具有太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林教导和高斌,都只能以曾经亲见亲闻的历史内容进行填充……这么多的由于,还能不如同导弹尾部烈焰炽射的推进器一般,把久蓄杀心的高斌推到那最后的目的地去?
于是本小说的高潮终于到来了。高斌一刀结果了平正明的性命。上天可怜见,平正明没经受太大的痛苦,他只是往上翻白了双眼看定了高斌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嘴唇微微地哆嗦了几下,浑身很快就痉挛抽搐卷了起来。高斌的痉挛发作得与他一样快。他浑身抖动着,箍住平正明脖子的手臂和捏住刀把的手指都变得如石块石条一般硬,他想松手想快停止想快逃走想决不能这么干想一切都错了完了都马上重新开始吧,但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已不听指挥了。他与平正明一起,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软软地缓缓地倒在过街楼里,而方才亲见了那把尖刀扎入胸膛的朱娜娜,早几秒钟便已经软瘫滑落到地板上。
阁楼上的高丽蓉不动弹不用看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平正明的灵魂带走了她的灵魂。她在过街楼里留下的只是一个躯壳,那躯壳里只有一个思想:床旁的小柜抽斗里,有一瓶剧毒的贴了一个骷髅头标签的丸药,几颗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