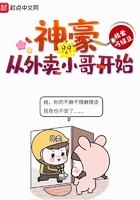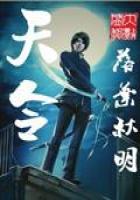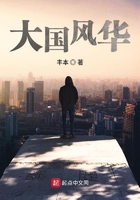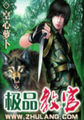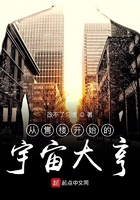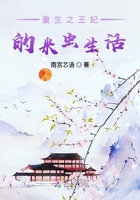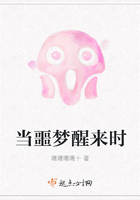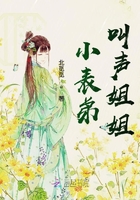转眼又是冬天。
今年冬天似乎格外来得早,刚进阳历十一月就开始大冷,接着上了冻,于是各家都争抢着给麦地浇冻水。曹春英和李同两个人都不是那巴尖抢上的,而是处处谦让别人,好事先紧别人,到了十二月中旬,才轮到给自家麦子浇冻水。天气特别特别冷,那流动的水几乎也要结冰了。
这一天,他们浅完麦子,李同回家吃了晚饭,如平常一样,他去酒厂接齐常富的白班,上夜班。
值班的小屋里生了火。按每日的习惯,李同先看看库房门口是否干净,是否卫生;他发现不太干净,便扫了扫,然后把昨天剁好的煤茧子填到炉子里去。那煤茧子虽然不干不燥,但冻得很磁实,添到炉子里立刻溶化,而且冒出带着湿气的一股股浓烟。
李同知道,齐常富最怕冷,于是那小屋就被堵得严严实实,所有窗上的、门上的孔洞和缝隙都密不透风。
炉子上做着开水,铁壶咝咝地响。李同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又打开料库的门,看看库里是否干净,是否有耗子出没的痕迹。
也活活该出事了,就在这天晚上,李同发现了料库的一个让人难以琢磨、又琢磨不透的问题。其实这问题早已存在,只是李同平时没太在意,齐常富更没有看出,而偏偏今天晚上李同着实留意了,也看出了,原来,他发现用来做酒的高梁、大麦、稻谷之类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它们成包成包,还和运来的时候一样码得整整齐齐,一点也沒有少,但每天的出酒量呢,据说依然是那样地多,依然夜里常有三轮车、嘣子车、小面包之类前来提货。这是怎么回事呢?打个比方,就如同面没少,而蒸出的馍还那样地多!“面”,从哪儿来的呢?难道还有另外的一个料库?又在什么地方?
其实话说回来,你发现了,又怎样?又与你何干?你只不过是个看守的人,不丢、不闹耗子就好了,你便算完成了任务,又何苦来多操一份心呢?但李同不,他偏偏今晚上有了一份闲兴,大概是麦子浇完了冻水、心里踏实的缘故吧。于是,他竟自一人走出小屋,想寻个究竟。
李同走过几间大房子,又走过一个夹道,然后遇到一扇铁门,门虚掩着,他推开了,此时他发现了另外的一个小院,院里有两间房,全亮着灯,但一间有人,一间没人。酒厂的改造、拓展本来与他和齐常富毫无关系,日常的许多事都与他们毫无关系,但李同此时感到新奇,他朝那间没人的房间走去。隔着玻璃,他看见这间房里有码得高高的、成箱的酒,另外还有空着的包装箱。什么酒,他不知道,包装箱上面的字他也不认识,但他保证不是“南庄高粱白”,因为这几个字不用认,平时看也看得滚瓜烂熟。
李同正心中纳闷儿,忽然觉身后站了人,回头看,是王厂长。
王通森问李同:“你来这儿干什么?”
李同回答:“没事,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李同有些害怕了,因为王通森的面孔是阴冷的,腔调是横横的,眼睛是红红的,李同赶紧转身走掉。
……故事说到这里,必须要提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玉山。
韩玉山也是南庄的一个农户,比李同年长几岁,家里有一儿一女。他在猪场上班,干的也是类似看守的差使,他的看守地点是在猪场的一个把角,那里也有他的一间小屋,为的是防止有人夜间越墙而入偷盗猪饲料,或者有黄鼠狼、野狗甚或从山上下来的狼去偷袭还未长大的小猪。韩玉山是个谨慎、小心而又富有心计的人,他是争取,争取到了这份看守的差使,虽然目的也和李同一样,夜间可以睡觉,白天可以干许多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
李同为人忠厚老实,很容易相处,韩玉山在晚上经常锁了自己的小屋到李同这里来串门儿。猪场和酒厂仅隔一墙,在墙边两棵树的掩遮下,那里已经被韩玉山走出了一条小小的缺口。他来李同这儿除了随便聊一会儿天儿之外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便是他每天都要从李同这儿串走一暖瓶开水,因为猪场没有给他预备火炉,用柴锅烧出来的水不好喝,又有一股烟薰火燎的味道。
这天晚上,李同看到了他不该看的、从酒厂深处转回来的时候,韩玉山已经坐在李同的小屋里等半天了。
韩玉山开口说:“你也不锁门。”
李同说:“没什么可丢,不过一份铺盖褥子。”
韩玉山问:“你去哪儿了?”
李同说:“我没在厂里转过,今天开了眼,这酒厂可真是越扩越大。”
炉子上的水开了,韩玉山串好了一暖瓶。临走,韩玉山伸过头来,很神秘地对李同:“发现没有?你们这儿在做假酒。”
李同没反映过来:“假酒?什么假酒?”
韩玉山说:“把别人的酒买来,一瓶兑两三瓶,充低度酒。”
李同质疑:“你说做假酒?南庄高梁白不是挺好喝吗?干嘛做假酒?”
韩玉山指了指他的鼻子:“你呀李同,真是个实心眼子……好,就如同我什么也没说!”
李同想想,想过味儿来了,便说:“也许是吧,刚才我看见那房子里满都是酒,可料没动,还是那么多。不信我给你开库房门,你可以看看。”
韩玉山说:“行了,我也不用去看。李同,这事咱就说到这为止,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许再对第二个人说,不许再让任何人知道。听见没?”
天很黑,也很冷,朦胧的月光伴随着阵阵凉风。当韩玉山提着暖瓶刚刚走出李同小屋的时候,他忽然听见远处有人说话。
“厂长,还没回去?”
“还没。”
很简单的两句对话,但韩玉山已经听出问话的是王二润,答话的是王通森。王二润是酒厂的巡夜,此人也算得上是村里的一个青皮无赖,二十多岁了,地也不种,光指着犯混耍刺儿过日子。王通森用他来当巡夜,应该说很恰当,同时也有收买的意思。
韩玉山既胆小又多疑,这么晚了,他倒要看看王通森来这僻静的东南角干什么?他轻步走过那墙的缺口,站到墙外,观察动静。
他看见王通森开门进了李同的小屋。
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王通森出来了。韩玉山觉得没啥,想走,回自己小屋去。但他刚要转身,却看见王通森只是出了屋子、却没有离开屋子、或者说并没有走掉,月光下,只见王通森站在了李同小屋的窗下;再看,王通森似乎在做什么,或者说做了点什么……又见王通森地上捡起个什么东西,续而踮起脚,手伸向火炉通到外面的烟囱……
做了什么呢?没人知道。但管它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大冷天,还是回去,回去,于是韩玉山看见王通森走了,他也走了。
第二早上,一个消息传出来,让全南庄人以及韩玉山本人都大吃一惊:李同被煤气薰死了!
韩玉山不但吃惊,也感到蹊跷,昨晚还好好的,怎么就薰死了呢?他在街上听完这事,回到家里,反复琢磨,连中午饭也没有吃,但终于被他琢磨出个大概来;那大概,即使是大概,也不能说,不能说……
从此,韩玉山装作什么都不知,一概不晓,人前人后也一句不提。别人问他:“老韩,你不是晚上常到李同那儿串门吗?”他回答说:“好长时间没去了。”要么就摇头:“谁说的?我根本就没去过。”
首先发现李同死的是齐常富。他来接李同的班,见门锁和釕铞挂在了一起,虽没有锁死,但人从里面是出不来的。齐常富从釕铞上摘下锁,拉开门,李同便随着那门死尸般地倒了出来。齐常富吓傻了,大呼小叫,想喊来人,又想把李同抱起,但李同此时已全身冰凉,齐常富便大哭,边哭边罗着锅子一路奔一路喊呌,去村西头李同家找曹春英。
当曹春英与闻风赶来的乡亲们把李同抬到外面,身下又垫了褥子,然后做人工呼吸,齐常富便开始检查那屋子了。他发现炉子的火门竞然是关着的,暗暗责怪李同的粗心大意。当人们把李同抬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奔往公社卫生院去抢救的时候,齐常富又发现外面的烟茼不知被什么人堵死,接着,他从烟茼里掏出了一团被熏焦了的麻包片。火炉已奄奄一息,屋内冰冷,齐常富开始重新生火。
在李同被送往公社卫生院以前,曹春英曾去找过王通森。那时王通森还没有来厂,还在家里睡大觉,是妻子把他叫醒,但王通森醒来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王通森昨天晚上看见了李同,那时他正和几个客人喝酒,喝了许多的酒。酒将散,他忽然隔着玻璃看见外面有人,深更半夜不得不提高警惕,后来才认出是李同。当他向李同发问的同时,已感觉到自己有些醉,感觉自己腔调有些反常,但也同时看出李同的紧张;李同为什么紧张呢?是不是来打探?是不是做贼心虚?谁又敢保证那不是打探、不是做贼心虚?于是客人走了以后,他晃晃悠悠,便去了李同的小屋。路上,似有人和他说话,说了什么已不记得。当他进了李同小屋,其实韩玉山刚出了李同的小屋。
在小屋里,他问李同:“怎么还不睡?”
李同说:“马上睡。”
他又问:“你刚才都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只看了看。”
“你都看见了什么?”
“没看见什么。”
“看见了什么就直说!”
李同不再言语,只默默在床铺上坐着。王通森也不再理他,不经意间却把水壶提起来,装作看火炉的火,然后,便顺手把那火门儿关上了。出了小屋之后,王通森隔着门上的小块玻璃看见李同上床睡觉了,便把那门锁扣在了钉铞上,又是不经意。欲走不走之间,他又发现窗根下有一块麻包片子,于是他捡起来,踮起脚,把团好的麻包片子塞进了烟茼里。他把这些事做完了,忽觉得酒劲上来,便又晃晃悠悠,是回家?还是回办公室?还是回家吧。到了家,他倒头便睡,连衣服也没脱。
酒精让王通森没有思考为什么做那些事,或者说,他做了那些事究竞为了什么,似乎一切全是不经意,一切全是潜意识在做怪。
曹春英急冲冲来家里找他,朝他喊道:“李同让煤气熏了!你赶快派车!”
他从床上坐起,惺忪着两眼,楞了一会儿,然后看着天花板发呆。曹春英跳脚嚷道:“人快不成了,你见死不救怎地?”
王通森似刚刚缓过神,也似刚刚清醒。他瞪着眼睛问:“怎么会出了这种事?嗯?”续而说,“糟糕,真糟糕!”
曹春英伸手拽他:“你有车,一三0车!”
王通森说:“春英,你先回去,我马上派车。”
过了一会儿,王通森打发人去告诉曹春英,说一三0汽车坏了,司机正在修。若不信,可以去看,所有人都可以去看。
曹春英只好用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把李同送到公社卫生院,但公社卫生院没有接收李同,并且说也不要去县医院,因为县医院也没有高压仓,煤气中毒到这个程度不进高压仓是根本不行的。从南庄到大王庄是二十里,从大王庄经县城到丰安市,还要一百多里,手扶拖拉机半路加了柴油,一路颠波,但还没有到丰安市,不用别人说,别人也不好说,曹春英自己说了:“叔,大哥……别去了,人根本不行了。”
李同早已浑身僵挺,大家一致确认已经死亡。
就在李同死后第三天,他的父亲也死了。因为一个哮喘多年的老人经不住突然失去儿子的打击。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连办了两起丧事,乡亲们都来帮忙,王通森也出了不少力。李同是在岗位上死的,因此王通森很合情理地出了一笔抚恤金。
下了一场雪,大雪把一切都掩埋了。
曹春英坐在屋子里,望着窗外。秋儿不哭不闹,只依偎在母亲身边,望着母亲的脸。这屋子只剩了他们两个人。
曹春英像做了一场梦,人死得那么突然。
她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李同没有死;他不应该死,死得毫无通理,纵然齐常富把小屋堵得十分严实,纵然煤是湿的,但有火门儿,有烟筒,怎么就被煤气薰了呢?退一万步说,纵然受了煤气,又何至于死?
她忽然想起齐常富向她说过的一些话,他说门锁从外面挂死了,开门的时候李同随着那门倒出来,可见李同爬到门边是推了门的,但那门推不开……也许他还喊了,但是深更半夜,没人能听见。曹春英又想起自己去找王通森的时候,半路上曾遇到过王二润。王二润问她干什么去?她说李同中了煤气,找王厂长要车;王二润说咦?昨天半夜还好好的,王厂长还去过李同的小屋……
曹春英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蹊跷。下午,她把秋儿反锁在屋里,踏着厚厚的积雪去找齐常富。
齐常富也正坐在小屋里发呆。没了李同,王通森也不再找别人,这里白天黑夜就他一个人。
曹春英说:“常富,嫂子问你事。你说门锁从外面挂了,是怎么回事?”
齐常富说:“也是呢,我也正纳闷。”
曹春英问:“那是谁挂的呢?”
“也是呢。”
“那天晚上是不是有人来过?”
“也是呢。”
“你别总也是也是的,嫂子快急死了。常富,你觉不觉得李同死得很怪?”
“嫂子,要说怪真是怪哩。”齐常富说,“你们走了之后我查看这屋子,你猜怎地?火炉门是关着的!我寻思李同再傻怎就傻到这地步?再说烟筒也堵了,我从里面掏出一团麻包布,经风一吹全散了。”
“常富呵,你怎不早说?”
“你们光责怪我把这小屋堵得太严实,我痛恨自己还来不及呢。再说,我跟大伙也说了,当时都急,都没人着耳朵听。”
曹春英楞楞地坐了一会儿,说:“行,常富你歇着吧。”
曹春英去找王二润。
王二润是个挑皮捣蛋的青年,二十多岁了,没结婚,连个女朋友也没有。父母也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分出去单过。曹春英找到王二润的时候,王二润因为巡夜,睡觉刚醒。
曹春英问:“二润,我去找王厂长,半路碰上你,你说那天晚上王厂长去过李同的小屋?”
王二润点头:“是呵。”
“你怎么知道他去过那小屋?”
“我巡夜嘛,问他,厂长,还没回去呀?他说,还没有。我亲眼见他进了小屋。”
“他去干什么?”
“我哪知道?”
“后来呢?”
“后来我就放夹子套黄鼠狼去了。”
曹春英说:“你洗脸吧,我走了。”
整整一天一宿,曹春英没有睡,也没有吃,只给秋儿扒拉了些疙瘩汤。她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难道李同的死与王通森有关?甚或于王通森从中做了手脚?为什么?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可能嫉妒李同?就因为他可能认为李同是绊脚石?然而在她面前王通森从来没有显露过一点这方面的心思,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李同,更没说过李同一句不好的话。到底为什么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是的,不得不承认,王通森那流氓般的种种动作曹春英曾被动地承受过,但是那海誓山盟,那种种爱意的表达,曹春英却从来没有主动回应,更没有任何的允诺。这当然是基于对李同的爱,基于对她和李同的婚姻坚定不移。然而王通森倔强、胆大,也显出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的成熟和智慧,当曹春英为此产生感动的时候,她立刻纠正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她会遭唾骂,遭全村人唾骂,同时也会受自己良心谴责,更何况她那么深爱着李同,从始至终爱他,爱他忠厚老实,爱他仁义,爱他勤恳,爱他对自己太爱了,从她坠下悬崖,李同救她时起,她就决心把终身许给李同。后来,她曾经对李同说过:“秋儿他爸,别去值那夜班了,咱不挣那个钱。”
李同当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便摇头,便坚持去酒厂看料库、值夜班。
曹春英不得不说出:“晚上我害怕。”
李同的回答是奇怪,说你怎会害怕呢?有秋儿,还有咱爸。
曹春英又说:“你走了,我一个人闷得慌。”
李同笑,只是笑,接着使劲儿亲了她一口,说:“放心,我夜里偷偷回来几趟。”
曹春英呵,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更透彻一些呢?让李同产生误会,以为自己是为了夫妻事。假如你明说了,就坚持不让李同再去酒厂值夜班,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李同也不会死!
曹春英找过齐常富又找过王二润以后,王通森又来了。这一次他显得坦然自若,几乎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院子。曹春英披散着头发,但却一反常态,主动为王通森开了屋门。
王通森给秋儿带来了糖果,也给曹春英买了件新款式的棉衣。
曹春英回到炕上,披起被子坐着。
王通森说:“春英,看你这些日子瘦的,简直成了人灯。”
曹春英不理他。
王通森又说:“春英,你一定要想得开。人死了不能复活,将来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曹春英还是不理他。于是王通森凑到炕边去,掀开曹春英的被子,却不料,曹春英从被子里伸出了手,手里有一把明晃晃的剪刀。
“你这是干什么?春英,你是病了还是糊涂了?”
曹春英说:“你在那边坐好,我有话问你。”
王通森楞楞地坐回原处。
“在李同熏着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去过那间小屋?”
“谁说的?”
“你不用问谁说的,有人看见你,还和你说了话。”
“去了又怎地?这和煤气中毒有什么关系?难道我用煤气筒子往他嘴里吹?”
“我再问你,那煤炉子火门儿怎会是关着的?烟筒怎么堵了?难道是李同自己堵的?就算是李同粗心大意,那门锁又怎会从外面挂死了呢?想从里面推也推不开,难道也是李同干的?”
王通森从坐位上站起来,开始在地上踱步。秋儿在炕里坐着,但他并不动那糖,也直楞楞地望着王通森。
王通森忽然笑嘻嘻地说:“春英,你可能受刺激太严重了,在说胡话……你看外面冷得很,到现在我还没暖和过来呢。”说着,要上炕里去,却不料曹春英又一次用剪刀对准了他。秋儿喳地一声哭起来。
王通森似是彻底寒了心,他又在地上踱了几步,说:“那好。春英,你好好养,过几天我再来。”
出门的时候曹春英把衣服和糖果摔给了王通森。王通森头也不回地溜了。
曹春英第二天去了大队部,却发现齐常贵正和几个人围张桌子打麻将。也是,分田到户了,干部们没那么多事可做。
齐常贵把曹春英引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也很新,不是新装修就是新翻盖,比以前宽绰、漂亮了许多。
齐常贵问:“甚事?”
曹春英说:“齐大哥,李同死了,可是我觉得他死得有问题。”
齐常贵不知是没听懂还是装糊涂:“李同家的,人死如灯灭,李同再有问题也算了。”
“我是说他死得有问题!不是说他人有问题!”曹春英喊起来。
“哦?有什么问题?他不是煤气中毒吗?”齐常贵问。
“问题就是,有人把烟茼堵了,把火炉门儿关了,又把门锁从外面挂死了,李同想出也出不来,想喊也没人听得见!”曹春英强忍着眼泪。
齐常贵眨巴着眼睛:“你是说,有人使坏,故意害李同。是吗?”
曹春英点了头,眼泪哗地流出来。
“问题严重,问题严重!”齐常贵习惯拍桌子,便又使劲拍了下桌子,“曹春英,你要明白,照你这么说就成了一桩人命案。既是人命案,你找我又有什么用呢?大队只管行政只管生产,别的事管不了。我劝你还是赶快去公社派出所报告警察吧。”
说完,齐常贵嘿嘿笑起来。曹春英也不知那笑是什么意思。
于是,齐常贵命人给曹春英开了封介绍信。曹春英当天便去了公社派出所。
公社派出所有五个警察。曹春英先碰到的是所长,所长说出去有事,叫来两个警察听她反映情况。其中一个是高个子,三十多岁,另一个看去还是个小青年,比较瘦。
曹春英把李同的死以及她的怀疑一五一十地向警察同志说了,不清楚的,高个子警察负责问,小青年警察负责记录。说也说了,问也问了,最后小青年警察让曹春英在书面记录上签了字,说他们很快就去调查了解。
曹春英在家等了三天,第四天警察同志果然来了,来的就是那高个子警察和小青年警察两个人。不过他们到了王家庄并没有直接去找曹春英,而是先到了大队部,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诸事先和当地领导取得联系,很正常,也很正确。于是齐常贵专门派人来了,把曹春英从家里叫到了大队部。就在齐常贵的办公室里,两位警察和齐常贵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曹春英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只凳子上,距桌子一米远。这让曹春英感到像是她被审问。
高个子警察:“曹春英,现场我们也看了,你对你所反映的情况敢负责吗?”
曹春英回答:“敢负责。”
高个子警察又问:“据你推测那个作案的人可能是谁呢?”
曹春英说:“这我不能肯定。但是我对这个人有怀疑,所以请警察同志调查。”
“你所谓的证人,就是你所说的那两个吗?”
曹春英点头:“是。”
警察说“好。”便让齐常贵去传人。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完全出乎曹春英的意料之外了。当王二润被叫来、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他像个偷东西的贼,目光躲闪着曹春英;警察向他核实,他竟然全盘否定了他向曹春英曾说过的话。他说他在那天晚上没有见过王通森,更没有看见王通森去过什么李同的小屋,于是当然也就没和王通森说过话;他又说他那天晚上头疼,前半夜根本没有来,后半夜才来巡夜;他更不承认曹春英在路上曾碰见过他,所以曹春英前几天还特地到他家里向他核实,什么核实不核实,根本没有,这全是曹春英捏造出来的,目的是把李同的死归罪于别人,为的是得到赔偿金!
第二个叫来的是齐常富。如果说王二润是个青皮无赖、如此出尔反尔还不足为怪,那么齐常富一改以前的窝囊与木讷、公然说起瞎话来就完全不能让人理解了。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门锁,什么火门儿,也从来没有说过跟这有关的话,曹春英也同样没有去过他的小屋找过他,至于烟茼里堵了麻袋片子,他倒是和人说过,但那是风刮进去的,而不是什么人塞进去的。也全怪李同不小心,睡觉前不留意,更怪自己体弱,平时怕冷,把屋子封得太严实了,要治罪就治他的罪吧。
“不!不!常富,这不是你,这不是你的话,是别人教给你的!”曹春英奔过去双手抓住齐常富的胳膊,又揪住他的脖领子。
但齐常富只低垂着头,一动不动,任她揪,任她喊,不再说一句话。
曹春英又转向王二润,想抽他的耳光、撕他的衣裳,两个警察同时把她拦住。
曹春英呆呆地楞在那里。
齐常贵放这两个人走了。
高个子警察朝曹春英摊了摊手:“怎么办?”
负责记录的小警察问:“曹春英,想一想,你还有其它的证人吗?”
曹春英慢慢摇了摇头。
齐常贵说:“我看也就这样了。曹春英,人死了也就死了,王通森不是也给了你抚恤金吗?再说,往后有什么困难,大队还可以照顾你、帮你解决,你也可以再找王通森嘛”
曹春英忽然跳起来喊道:“不对!他们串通了!我敢保证,他们串通了!”
高个子警察问:“证据呢?你怎么证明他们串通了?他们和谁串通了?”
齐常贵说:“曹春英,你这就让警察同志很为难。现在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搞逼供信,更不能像文革,说什么串通一气、一丘之貉、什么黑帮黑线……”
曹春英真想说出那天晚上王通森又来她家、又想对她动手动脚,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不敢说,说不出口,因为那会引出一连串话题……也就在那天晚上,她向王通森发出了质问,问王通森去没去过李同的小屋,问烟囱为什么堵了?谁堵的,等等,但曹春英现在才明白,那些、那样的质问便等于给了王通森信息,所以他们才串通一气,所以才有王二润的出尔反尔和齐常富的死不认账。王二润是王通森的爪牙,齐常富无论怎样也是王通森的弟弟,他们当然听王通森的。况且,王通森那么霸道,那么翻脸无情。
因为曹春英没有说出“串通一气”的证据,所以派出所的调查到此为止。警察同志倒也沒有追究曹春英,问她为什么要揑造事实、揑造证人,无端地诬告人家王通森。
过后据乡亲们说,警察同志在村边的一家饭馆吃了一顿饭,陪客的不是王通森,而是齐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