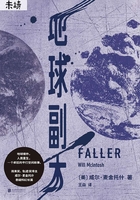房间里一共五个人,倒有四双眼睛在审查董玉梅,她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哆哆嗦嗦地喘作一团;实在无法分辩,眼泪抑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哭,岂不是等同于招认罪状,真相大白?这种监守自盗,诬告他人的恶作剧,于所长见得多了;毛法官的丈夫皮总经理,断然不是那种鼠目寸光的蝇营狗苟之徒,于所长心中自然有数。依照平时办案经验,他要控制住局面,先休息十分钟,待这小女人心理完全崩溃,再和颜悦色地问明作案事实,叫手下人依程序去办就行了。
偏是这会计沉不住气,一看情形不对,深感自己上了董玉梅的当,当下涨红了脸,跑过来抓住皮总经理的双手,连声道歉,痛悔自己有眼无珠;段瑞林也是不甘落后,急忙站起来,张口怒斥董玉梅是无耻小人,要求于所长从严惩处盗贼。
那董玉梅正委屈得无从分辩,忽然听到这二人的话,反而冷静下来,抹去眼泪,止住哭泣,面露阴笑,目光锁定这一对男女,要看他们如何表演栽赃陷害的伎俩。
皮越眼看事态已经闹大,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万一于所长不加深究,一味地偏袒自己,一旦真相大白,岂不有损公安人员的形象?遂笑着转移线索:“会计,我上任时,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现在还剩多少钱?”
“皮总上任时,公司有七千五百元,后来发了一次工资,一共用去三千二百元,外加一些零星开支,现在账面上还剩四千零九元。”会计毕恭毕敬,口齿清晰,报出这一组数字。
“段瑞林,向马师傅买货,一共付款多少?”
“洮砚石料三千元,翡翠玉镯一万元,合计一万三千元整。”段瑞林也不含糊,事情没过去多久,记得还很清楚。
“会计,出纳,你们付了多少款?”皮越再问。
会计和出纳员一齐摇头。
皮越哈哈大笑:“于所长,公司没付一分钱,他们却要在保险柜里找到翡翠玉镯,我看应当把这三个人各打二十大板,游街示众,以儆效尤。”
于所长是何等精明之人,皮越话没说完,他已经转过了弯,也哈哈大笑起来:“派出所不是你们演戏的地方,”又挥了一下手,“你们三个,都给我滚出去。”
段瑞林和会计都灰暗了脸,立刻转身出门;董玉梅双眼犯直,木呆呆地发愣,冷不丁给皮越跪下,磕了一个响头,铁青了脸色,走出门外。
于所长喝了口茶:“我说皮总,都是你的部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还能在公司里干下去吗?今后再有人告你,还是让你老婆来审合适,免得尽让你来愚弄我。”
是啊,本来还想借公司的招牌拖延些时日,再寻机会运作,这三个部下却要私卖玉镯,惹出今天这场风波,公司里是待不成了,只好另谋出路。
这可为难了杨文波,皮越签约要承包两年,只干了几个月,就来辞职,实在是让他为难。
皮越是何等精明之人,刚从生死劫难上舍命逃出,自然不会小肚鸡肠地和老同学为了几个小钱过不去。他拍拍杨文波的肩膀:“老朋友,别犯难,一千元押金,小事一桩,我不会向你讨要。辞职不干,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对你不会有半点牵连。”
两个金城大学的校友,鬼使神差,放弃本职工作不干,居然会在同一个小矿产品开发公司里先后失魂落魄,此时惺惺相惜,自然都不甘心,遂相互激励一番,盟下誓言:要用十年光阴,打造个人奋斗的成功途径,那时再来相见,遍约同校学人,也要学那曹阿瞒,志得意骄之时,来个金城煮酒论英雄,慷慨激昂,潇洒一回。
卸去负担,发下宏愿,耍了一回阿Q精神,皮越躺在床上自我总结:交了一千元承包费,用一万三千元购买玉镯,卖出六万元天价,又去那秦岭蛮荒野地里折损五万元,平添了许多生意场上的宝贵经验,虽说是九死一生,总归有惊无险,只不过赔了四千元钱,并没有伤筋动骨,摇散根基。从辞职到如今,也不过只有八个月整。若以此经历推算下去,只要瞅准机会,钱挣到手里,不可太贪,随时抽身,规避灾祸,一年挣个六七万元没什么问题;仗是越打越精,生意会愈作愈活,十年拼搏下来,挣个百八十万的,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这种设想,理论上虽然没有问题,实际操作中,还是要慎重行事,稳扎稳打,不能再跌大跟头,本钱折尽了,再想白手起家,那可是难于上青天了。
黄书包里有一万五千元,密码箱里有两万元,其中一万元是赵文军给的酬劳费,有这三万五千元垫底,难道还怕不能东山再起吗?
既要重打锣鼓另开张,终究干点什么,又成了当务之急,光阴宝贵,自然不能虚掷。皮越思忖再三,还是得先去看看儿子和父母,以释心中思念。
皮鼎看见父亲两手空空进门,叫了一声,扭头就跑回房间里,这让皮越十分奇怪,也就两个多月没见面,总不至于父子亲情,疏远得如同水火,不能相容了吧?
母亲看儿子面色黝黑,略显消瘦,虽然强打精神,却遮掩不住人生失意之后、通体积蓄的疲惫和沮丧。老人们久历人世,对儿女们的言行举止,仪容精神,只须朦胧一瞥,便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她不想甫一见面,开口就问不如意的事,要给长子留点情面,等待他自己说出这两个多月的坎坷经历来。
皮鼎头戴一顶太阳帽,穿了一身新衣服,脚登红白相间的旅游鞋,背着一只金黄色的小书包,站在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少先队员的举手礼,大声宣布:“爸爸,我要上学了!”
噢!儿子满六周岁了,九月一日开学,就要正式踏入知识的殿堂,开始漫长的求学生涯,直到大学本科毕业,如同自己一样,成为一名骄傲的、让人羡慕的知识分子。离开学还有多长时间,也就十几天了吧?儿子的童年生活就要结束了,做父亲的,应当多陪他玩耍几天,到处去看看,好好地照几张相,留做纪念。童年,自己的童年在哪里?早已模糊在记忆的深处了;儿子的童年,鲜活灿烂地,就在自己的面前。
皮越思绪万千,忍不住大发感慨:“儿子,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爸爸晚年,只能依靠你了。”话一出口,顿觉味道不对,自己正当青壮年的人生辉煌时期,怎么倒要依靠这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真怕是无心之口,剿灭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爸爸!”皮鼎大声询问:“妈妈买的衣服,小姑送我书包,你给我买什么好东西啦?”
这个问题,突兀喊出,不啻于迎头棒喝,让皮越浑身一颤,脸红心跳,一时手足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是啊,孩子要上学了,做父亲的居然完全忘却,整日里在秦岭的深山老林中,抱着一支枪,守住一堆顽石,追寻狂热的发财梦想;暴雨昼夜狂泻,山洪荡平了沟谷,本该在九死一生之后,幡然醒悟,却仍不思妻儿亲情,还要打磨经验,图谋再次出手,博取钱财;似这样心态急迫,莫非要学猴儿掰苞谷,忙碌不休,而收获却仅限于掖下所挟持之物?
他摇摇头,强自镇定下来,取下衣袋里的钢笔,送给儿子,作为上学的礼品。皮鼎接在手里,拔出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用力一甩,一串墨水,散落在纸上,他把笔还给爸爸:“小姑说了,小学生不能用钢笔,我要带橡皮头的、各种各样的、多多的铅笔。”
“好,好,爸爸带你去买。”皮越拉着儿子的手,去酒泉路上、金城最大的文具商店里,任凭儿子选挑,花了几十元钱,买了些铅笔、橡皮、卷笔刀、铅笔盒、格尺、整盒的二十四种颜色的画笔、还有些儿童读物,把皮鼎的小书包装得满满的。皮越试提一下,书包很沉,他拎在手里,儿子大叫起来,坚决要自己背在身上,雄赳赳地甩着手,走在爸爸的前面。
中午十二点整,媛媛准时下班,刚走到法院大门口,“妈妈!”一声尖叫,皮鼎自马路对面,撒腿就要跑过来迎接,慌得皮越紧追两步,将他擒在手中;道路上车辆往来穿梭,实在是太危险了。
媛媛看到丈夫和儿子一块站在马路对面,快步穿过车流,双手抱着儿子,想高举起来,却是力有不济,书包大大地增加了儿子的重量。“妈妈,我长大了,你抱不动我了。”皮鼎很骄傲地昂着头宣布。
有儿子在身边,长时间在外游荡,两个多月不登家门的皮越,见到自己的媳妇,少了许多尴尬和不安。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费翔的歌声又在耳边响起:“……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是啊,曾几何时,密码箱里塞满了钞票,那是何等的惬意舒心?可是钱来得容易,也溜得飞快,如今远方归来,折戟沉沙之后,行囊空空的男人,怎么向妻子交代事情的始末呢?能说得清楚吗?她能相信我吗?五万元的亏空本不是件小事,可是钱从哪里来的,需要还给别人吗?皮越最害怕和妻子谈论经济问题,商海搏浪中发生的赢损,总是和平常告诉她的钱数风马牛不相及,他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
对这两个多月时间里皮越的所作所为,媛媛几乎是一无所知,他能杳如黄鹤,她只好独善其身;他不说,她也不想问;他总处在大起大落的悲喜之中,自己设计的人生巅峰状态,却是迟迟不肯出现,或者失之交臂。有命运吗?有机遇就应该有命运,那是一对孪生姊妹。命运暂不去推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机遇呢?我皮越的下一个机遇在哪里呢?
皮越深深地沉浸在遐思中,媛媛领着儿子走进了路边的饭店里,特意点了几道好菜,她要犒劳几年来疏于照看的亲生儿子,让他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两个多月深山密林里的淘金生涯,不仅疲惫了他强壮的身躯,也完全消耗了他那不屈不挠的人生意志;死里逃生的历险,恍如昨日梦醒,而心力交瘁的平和与复苏,却还要有大段时间的休息和放松。与妻儿在一起聚餐,对皮越来说,几乎是自喧嚣纷争之中潜身于桃花源里。妻子是自己值得依赖的大后方,家庭是历经溃败后能容留他喘息休整的唯一场所;一个以执掌法律、裁决是非为终生职业的法官,原本就是生活波涛中最平静安宁可靠的港湾。
皮越向妻子投去万分感激的一瞥,精致的菜肴勾起了他的口腹之欲,长期以不饿为准则的粗糙饮食,早已把他对美味食品的敏感,催生到了口目耳鼻皆能大快朵颐的精神超常境界。
红油肝片,刀功细腻,含在口中,舌头搅动若干圈,便化作酱末;腰果鸡丁,软硬相煎,一勺勺送入,唇齿留香;一只肥美的香酥鸡,大半在手,扭扯撕拽,片刻之间,丢下一堆骨头;整条的糖醋鱼,翻夹几筷子,大半已经吃尽;唯有一盘香菇油菜,皮越懒得去动。
媛媛捕捉到了他那讨好的眼神,欣赏他那风卷残云似的狼吞虎咽;儿子长大了,也会像父亲一样能吃善侃;媛媛不担心,她有能力养活两个大肚皮的海量男人。只是,他撞了南墙会回头吗?他肯去把单人床买回来吗?在原则问题上,她不能让步。
丈夫这种贪婪而掠夺式的吃相,使她想起了“吃在嘴里,盯着碗中”的民间俗话,虽有些闻之不雅,但是却十分贴切。她早已停筷在手,欣赏着他那种只顾一人吃饱,必定全家不饿的唯我独尊的大男子主义。儿子在翻弄书包里的学习用品,一件件拿出来向母亲炫耀。皮鼎还太小,不知道什么叫做餐桌上的角逐;他要再成长二十年,也许才能明白对待食物的态度,乃是借以观察人品和生存际遇的极佳时机之一。
皮越饿了,至少是长期缺少油水和味道;那么,他去工作的地方,必定是艰苦的农村、山沟里或者戈壁滩上;他承受不了太多的苦难,这她很清楚;居住在大城市里,享受舒适的生活,是他一直在反复向她承诺的。他成功了吗?挣到钱了吗?从他那一脸疲惫中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一种万般无奈地顺从,这是少有的迹象,强悍的丈夫是从来不向什么人低头的,哪怕在嘴上敷衍一下都不肯;他失败了吗?败得很惨痛吗?丢掉了一万元,没有什么关系,媛媛不在乎,男人不亏损些钱财是永远不会退缩畏惧的;那么他会背上外债吗?以他那种十分珍重钱财,东掖西藏,对发妻都不肯如实相告的天性,他不会有很大的欠债,巨额的债务会要了他的命,那是对他人生自信的毁灭性的打击,会彻底地破坏他的食欲;一个能在妻儿面前眨眼之间吃掉大半只香酥鸡的人,不会有太坏的遭遇或是痛不欲生的悲愤。那么,他是有所失有所得,输赢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里了!媛媛不怕他亏空,不怕他欠债,她有思想准备,有经济能力,乐意帮丈夫渡过难关。她盼着他就此止步,回到国有企业去上班;买一只单人床来,放在大客厅里,一切都会平静下来:母亲不会活很多年了,儿子在慢慢长大,家庭应该完整,日子会很红火地过下去,媛媛没有其他的奢望。
给母亲要了一份红烧肉,二两大米饭,拎在手里,一家三口人,慢慢地向家里走去。媛媛的脚步缓慢,希望那些时常在她身边出现,似乎很关心地询问自己的丈夫的音讯的人们能看到,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正追随在自己身边。大男人很强壮,精悍而温顺;小男人发育得很好,已经背上了一只鼓鼓囊囊的小书包。有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护持,自己是幸福的、安全的,不怕那些心怀叵测的男人们的骚扰;家庭,是神圣而宁静的、不容他人觊觎的休憩港湾。
中午的时间太短促了,媛媛去上班,皮越恭顺地带着儿子,在家里陪老人。
点燃一支烟,歪靠着沙发,两只脚平放在茶几上,老丈母娘自己从不下床,皮越放肆一点,不会有谁来窥看他这不雅的举止。电视机正在播放动物世界,一只雄健的豹子飞快地追捕着一只羚羊。皮鼎大睁着双眼,紧张地注视着画面,他离屏幕太近了,皮越把他叫回来,坐在自己身边。二十分钟很快过去了,商业广告占据着画面,皮鼎失去了兴趣,在房间里四处窥探,希图寻找点什么好玩的东西。
房间里十分整洁,女主人是染有洁癖的,容不得灰尘和凌乱。皮鼎用手去摸茶几、柜子、桌面、窗台,再悄悄地在地板上抹蹭,到处是干净的,几乎一尘不染,他心里有些奇怪:为什么爷爷奶奶家里那么多人,还没有妈妈一个人搞的卫生好呢?
皮越闭目假寐,午间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安逸;到了晚上,怎么向妻子交代这两个多月的行踪呢?闭口不谈不是明智的作法,信口胡言毕竟不能蒙混过关。从现状来看,她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和租来的一套房子,又在孝顺老人的传统习俗上,赢得了一切知情人的赞赏;而自己呢?无拘无束,踪影不定。也许人们认为我是轻浮浪荡,不负责任,抛下妻儿岳母,只图一人自在逍遥。皮越皱眉苦笑,天可怜见,真是屈死我也!哪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甘心寄身于石榴裙下,自暴自弃,聊度余生?那岂不与酒囊饭袋无异,犹如行尸走肉一般!想我在国有企业里,也是头号人物,独自承接工程,挑头承包;回收欠款,功在千万元之上;只不过是碰上了邓亚智和朱经理一类啮齿小人,鼠目寸光,不守信誉,出尔反尔,逼得我皮越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
再点燃一支烟,思绪飘远:主动下海经商的第一仗,虽然险象环生,总归是我初试身手,避凶趋吉,全身而退;盘点下来,大胜之后大败,非我无能,天灾不可抗拒,最终仅亏损四千元而已,不过是一笔小小数目;回到金城,与段瑞林们斗智,赢得小胜垫底,总归不至于亏输尽净,折损了周旋商界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