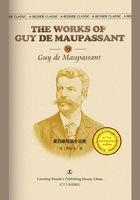我说缺不缺是一回事儿,拿不拿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起码体现一种心意啊。秦月儿对此不置可否。我想了想说:“要不这样吧,我店里有个根雕不错,就是一帆风顺那个,送给他,祝愿他做生意一帆风顺。”秦月儿说:“多少钱?”我说:“进价才几千元,不算贵,一点心意而已。”
秦月儿点点头:“那好吧。”
生日那天终于到来,秦月儿告诉我在香格里拉酒店定的包房,让我到时候直接过去就行。由于店里临时有事要处理一下,再加上路上堵车,我到酒店的时候时间已近中午。推门进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秦月儿,倒是她父亲正站在门口迎接客人。见到我,先是愣了一下,我彬彬有礼地鞠躬问候:“叔叔好,祝您生日快乐。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特别的礼物,希望这个根雕您能喜欢。”然后叮嘱店员将礼物放在了旁边。
秦月儿的父亲似乎对我的到来深感意外,但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谢谢了,这么客气,让你破费了。我没让小月儿通知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里面请吧!”
我通过秦月儿父亲的表情判断出,他确实没有想到我会来,这说明秦月儿事先没有跟他沟通,这一点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抬眼望去,虽然整个包房的面积不算太大,仅仅摆放了十几桌酒席,但是几乎坐满了人。而且从房间的豪华程度以及餐桌上酒菜的丰盛程度可以判断出,这一桌饭菜没有一万,也得八千元。茅台酒、中华烟、燕窝、鱼翅都赫然在列。而且前来道贺的客人层次也不一般,这一点从形象气质上就能看出。我进屋之前和秦月儿父亲说话时,就有很多客人往我们这边张望,估计他们一定在猜测,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进入房间之后,我更感觉有些尴尬了,因为我发现找不到适合我的位置。是啊,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知道坐哪儿才合适。尴尬之余,我站在角落里给秦月儿打电话,结果电话响了半天都没人接听。不一会儿,却发现秦月儿挽着母亲的胳膊从另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跟她们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小伙子。我的心里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我冲秦月儿摆摆手,秦月儿看到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面前,高兴地说:“你来了啊?”
我说:“嗯,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秦月儿说:“电话被我放在车里了,没带在身上。”
这时,秦月儿的母亲也走了过来,旁边的女人向她打探道:“这位是?”
秦月儿妈说:“哦,是小许,小月儿的朋友。”
我礼貌地跟对方打招呼:“您好!”
对方充满敌意地上下打量我,很不友好地从鼻腔“嗯”了一声。对我不友好的还有那个年轻人,长得矮墩墩的,胖得跟一头猪似的,挺大个脑袋好像直接安在了躯干上一样,连个脖子都没有。
打过招呼之后,秦月儿将我叫到了一边儿,小声对我说,那个中年女人就是省委某秘书长的老婆,旁边那个就是他儿子。我说:“哪个?”秦月儿说:“你咋这么笨呢,就是上次跟你说的,要给我介绍对象的那个。”
我这才恍然大悟。联想到进门时,秦月儿父亲所说,没让秦月儿通知我,以及刚才那一对母子对我不友好的目光,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事情至此还远没有结束,我发现这个生日聚会我似乎有些多余,自从我来了之后,除了秦月儿不时地回到我身边,跟我打打招呼之外,更多时候根本没人理我。倒是那个胖猪很会来事儿,宴会开始不久之后,就主动站在前台,拿着麦克风要给大家献歌儿,说是祝秦叔叔生日快乐。然后引吭高歌,说实话,他的歌儿唱得还真不错,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再不堪的人也有他的优点和长处,看来人不可貌相这话是对的。他的歌声结束之后,台下掌声一片。
我听身边有人议论道:“他是谁啊?”
另一个回答说:“好像是秦总女儿的男朋友吧。”
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仿佛被人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心想他是秦月儿的男朋友,那我是什么?
那肥猪唱完之后,整个宴会的气氛被他调动起来,台下有不少人高喊着让他再来一首。这厮倒也不客气,又献上了一首刘和刚的《父亲》,唱得是声情并茂,就连秦月儿的父亲也在台下鼓起掌来,似乎对他的印象很不错。
我万万没料到生日宴会还有这样的小插曲,说实话唱歌我比不过他,但写文章我应该远远在他之上,可惜今天这样的场合我根本没有机会展示。我只能眼看着肥猪以他精彩的表现,将我彻彻底底地秒杀。更可气的是,肥猪唱完之后,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秦月儿面前,故意和她套近乎。秦月儿心不在焉地应承着,对他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不一会儿,秦月儿摆脱了他,来到我的身边。看我似乎有些不高兴,秦月儿关切地问:“怎么了?不开心吗?”
我故作轻松地说:“没有啊!”
秦月儿何等聪明,立刻就摸准了我的心里所想:“你就放心吧,即便我嫁不出去,也不会嫁给这个猪一样的男人。尤其不喜欢他那种张狂的样子,整天泡酒吧歌厅惯了,仗着能吼几嗓子,就来我爸的生日宴会上卖弄。这事儿也怪我爸,压根儿就不应该让他来。”
秦月儿给我解释着,似乎想给我吃一粒定心丸。
我表面微笑着,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
从今天的种种迹象表明,秦月儿的父母显然更倾向于将女儿嫁给这个肥猪,否则不会想不到应该邀请我以秦月儿男朋友的身份参加。还有就是,从秦月儿妈和肥猪妈从房间里出来时亲热的样子就能够看出来,家长们对他们的婚事是认可的。不过对这样的结果我也不意外,毕竟肥猪的爸爸是个副秘书长,而秦月儿的父亲正需要巴结这样的权贵,现在做生意离不开官员做保护伞,与高官结为儿女亲家,好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顿饭我吃得很没趣,简直是如坐针毡,尽管秦月儿不时地走过来陪陪我,但更多时候她也忙着招呼客人。好不容易等到宴会进行得差不多了,我再也没有待下去的兴趣,也没告诉秦月儿,而是站起身来跟秦月儿的父亲打了个招呼,说有事,先走了。秦月儿的父亲没有挽留我,只是简单跟我客气了两句,那表情跟招待其他的客人没什么两样,这让我十分郁闷。
让我更郁闷的是,我走的时候,那对肥猪母子还没走,十分活跃地帮着招呼客人,俨然他们就是这家的主人。直到回到家里,我的眼前依然浮现着那对肥猪母子的笑容,就感觉胸口像堵了一层棉花。我刚到家没一会儿,秦月儿的电话就打来了,质问我为啥没跟她打招呼就走了。我冷冷地说:“也没我啥事,看你们又那么忙,我就先回来了。”
我特意用了你们的字眼,以表达我对那肥猪母子的不满。秦月儿何等聪明,一下子就明白我在闹情绪,在电话里跟我说:“我已经解释过了,你不用担心我和那肥猪有什么,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我说:“这不是担心不担心的问题,从种种表现来看,你爸妈确实接纳了他,而不是我。”
秦月儿也有些急了,在电话里跟我吵架:“我爸妈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我都说一千次了,我的婚姻我做主。”
我说:“既然你能做主,就应该彻底回绝他,为啥还让他今天参加这个生日宴会?这样让我心里怎么想?”
秦月儿说:“他爸和我爸是朋友关系,他爸今天有个重要的会议抽不开身,所以让他和他妈来参加宴会,出于礼貌,我们又不能把他们撵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