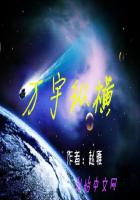天马弹得一手好吉他。他弹起吉他来,丁丁当当的像泉水一样。女生说天马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意思是指他能稍微安静一会儿,才能显出他男子汉的魅力来,才可爱;他要是刃说话,天哪,女生非退避三舍不可!
在女生的眼里,天马像是一条可怕而又可爱的毛毛虫。天马喜欢崔健,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留了一个崔健的发型,不知从哪儿找出一件文物似的二尺五黄褂子,皱皱巴巴地穿在身上。那一次,我们班在黄河大桥的雪地上搞了一个篝火晚会,天马自弹自唱,唱了一支崔健的歌曲,那歌声在旷野之中显得格外粗犷豪放,摄人魂魄。没想到,女生们的掌声比男生们的还热烈。
大雪里,人都变得那么净洁,灵魂像被洗过一般。天马向女生丢雪团,使绊子,惹得女生吱哇乱叫。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子,惹得男生们既羡慕又嫉妒。嘿!谁有天马的胆儿呢?那些文静的女生,此时像麻雀一样叽喳个不停,男生们倒显得文文静静的。
天马打篮球、踢足球,都是一把好手。要是和别的班里搞踢球比赛,天马像疯子一样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大喊大叫。曲尽人散,可是天马意犹未尽。天马的高喉咙大嗓门在楼道里嚷嚷个没完:“某某,你的球臭死啦!某某,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不传球!虬生格刚烈的男生,没少和他干仗。
天马的父母都是教授,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可是这小子的外表没有一点书香气息,倒像是个货真价实的痞子。他钟情美国托马斯?沃尔夫和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有一次,他在宿舍里大段大段背诵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说实话,我们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托马斯?沃尔夫的名字。天马博闻强记,倒让我们看走了眼。
天马爱和女生开玩笑,开起玩笑来没有一点分寸,那些话让我们男生听了都觉得脸红,可这家伙一点也不在乎。有一次,他和上海的女孩蓉予开玩笑,我们好几个男生都在场。天马说:“蓉子,可怜可怜我吧!蓉子,救救我吧!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聊天啦。”蓉子脸红了,垂着头痴痴地笑,但没有一点恼怒的意思。蓉子故意板着脸说:“走开!”天马说:?你伤我的心哟,你好伤我的心哟,噢!“蓉子说:“天马,你的脸皮真厚!”天马说:“那你就蒙鼓皮用吧。”一句话,又把蓉予逗得开心大笑起来。
一次,一个女生慌慌张张地来找男生,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两个社会上的小痞子……来……来纠缠蓉子……,天马一听,眼睛瞪得铜铃一般,他大喝一声:“哥,抄家伙!走啊!”天马不知从哪儿抽出一条九节鞭,哗哗啦啦地响着,旋风一样向女生宿舍奔去。两个小痞子可能得到了信儿,早已溜之大吉。天马咬牙切齿地说:“好家伙,跑到校园耍流氓来了,若要让我撞上,非让他挂花不可!”天马像古代武侠中的侠客,介乎于正邪两者之间。他外表有点邪劲儿,实际骨子里却是顶顶严肃的。
天马这小子活得就是潇洒!如果有人在背后说天马的坏话,立马就有人反对:“瑕不掩瑜,兄弟,懂吗?”
那些蝉声如歌的下午,我曾多少次在栀子树下恍惚地微笑;而当月亮挂上玉兰树梢的时候,我又曾多少次地暗自叹息;
靡靡
蝉歌如箭
收到她的信,正是六月,炙热的阳光和热闹的蝉声让人心浮气躁。栀子花肆无忌惮地开着,神秘的花香使人意志软弱。
笔友指责我不能理解她,十六岁的她说:我真怀疑你从未经历过十六岁!于是,三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回想,凝眸于那到现在还令人隐隐作痛的十六岁夏季。
其实,十六岁少女的心思,我大概是明白的。
因为,十六岁时的我和所有十六岁的少女没有区别。总是偷偷地祈望自己变成长发公主,被打败班主任的王子带至天涯海角。使我兴奋的,不外乎是男同学的一件生目礼物老师的赞美或是与一位特别出色的陌生人的邂逅;而使我侈心沮丧的,也不过是女同学的一句讽刺或丢失了的长裙。弱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简单循旧地流走,就像天永远那么湛盔不变。
但那一日天空昏暗,乌云密布,大雨哗哗下了个措手不及。我没带雨具,在这突发的大雨里狂奔回教室。然后,在转弯的拐角,我撞到了他。正确地说,是他撞到了我——可当删的我并未意识到这两者有何不同。
我顺着洁白的球鞋往上看,蓝色牛仔裤,白色衬衣。他用明亮的眼睛饶有趣味地看着我慌张地道歉,顽皮的微笑含在他的嘴角。
他什么也没说,只将我散落一地的书拾起,塞在我手里,很快地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知为什么,一种茫然的快乐泛了起来。
两天之后,他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响亮地叫着我的名字,吸引了不少女生的注意。我当然知道他为何而来。在那大叠的参考书里,我发现了一本诗集,写着素不相识的男孩的名字,不可遏制的,我立即想到他。诗集的第二面有一句用红笔划过的诗: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我就是那一只/决心不再躲闪的白乌。
我怔怔的,无法避免地想了一夜,有千百种理由,也有千百种心事。十六岁少女所期待和憧憬的,不过如此。从此,只属于自己的单纯的喜乐开始被他左右,深深浅浅的快乐忧伤莫名而来,那些蝉声如歌的下午,我曾多少次在栀子树下恍惚地微笑而当月亮挂上玉兰树梢的时候,我又曾多少次地暗自叹息……
在那年轻而又无知的日子里,我曾经有过多少难懂的心事,也曾把自己肤浅的感情包装得深沉,把所有的渴望都只肯透露一点,所有的话都只说一半儿。而且,一直固执地认为:和他,是永远到天长地久的事了。
直到那个中午,蝉声短而急促,我躲在假山后的一颗树下乘凉。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由远至近的脚步声,还有他的笑声。一个男孩子嘲弄地说“看来,她是真的喜欢上你啦!”我预感一种沉重的东西临近了……
于是,所有的快乐和感情都化为虚幻,所有的故事和偶然都是精心策划。在一个恶作剧里,在一次无关紧要的玩笑中布下了甜蜜的陷阱,只为了引导我这个傻瓜一步步靠近,如飞蛾扑火,终不可拔——我是怎样的愚不可及啊!
我急痛攻心、手脚麻木、不能言语,已忘记哭泣。是谁欺骗了我?是他,是他们,还是我盲目的心和模糊的双腿?原来,那样纯净无邪的笑容里,并没有一颗纯净无邪的心:原来,我才是那只飞向残忍射手的愚蠢白鸟:原宝来,我一直扮演的,只是一个小丑,在众人讥讽的目光里,自以为是地编织故事。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这个自作多情的女孩在别人早已写好的剧本里卖力演出。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也只能听见渐近渐远的脚步声,听见上课的铃声,听见惊心动魄的蝉鸣,听见有什么东西慢慢裂开,然后炸成碎片,丁丁东东清脆地落在脚边。蝉歌如箭,在盛夏的浓密里穿心而过。
而我那十六岁的短暂夏季,也在这如箭的蝉歌声里一夜凋谢。
柳筠,你真的是个好女孩,如果,我是专程来游玩的,是个健康的人,我一定会好好呵护你,可是,我再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仅剩九天的生命历程了……
刘梧桐
今年风好大
明天文化街的大礼堂,将要举行一次由着名教授李晶主讲的文学讲座。
我看了看日历,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要做,因此决定不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为了保持充足的精力,我早早地洗了澡,翻了几页英文小说,然后就关灯睡觉了。
第二天起床吃过早饭,我跟爸妈道了别,便到街上站牌下去等巴士。家里到文化街还有四个站的路程,巴士上坐着几个同样要去听讲座的年轻人,正在高谈阔论,我朝他们笑笑,便专心地望窗外的风景——我一直都习惯于坐巴士时皇望窗外飞逝的风景。东停停西走走,很快四个站就过去了。了车,慢慢地走,早晨的微风很新鲜,迎面吹来,长发飘起感觉很舒服,今天我穿了件白色中袖上衣配一条淡蓝色短裙使自己显得精神些,到了礼堂门口,我轻轻地走了进去,也是带了一个早晨的清新吧,我发现好多双眼睛向我望来,我刳了个前排的位子坐下,以便不至于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时候还早,教授还没来,我便静静地坐着,这时朝蕃望的眼睛陆续转移了视线,可我却分明感到有一双隔桌的砂亮清澈的眸子依然默默地注视着我,灼热却又不失礼貌,熬少女矜持的心也不禁有点慌乱起来。
讲室里突然静了下来,诧异中,我抬起头来,见到了那个叫李晶的教授站在讲台上——这是位很有风度的老者,一眼便知是有着渊博知识的人,和他的“现代”的名字{展不相称,我又趁机偏头望了望那双清亮的眸子,白皙的度肤,使得高大的身躯也显得满是斯文的书卷气,一张很让女孩子心动的脸庞,仿佛这双眸子在哪儿见过似的,一时又想不起来。
教授的课讲得很精彩,我不停地做笔记,再没有去望那双眸子,一个上午的讲座教授洋洋洒洒地讲完,令人意犹未尽,还沉浸于文学中奥妙的境界里。好一会儿,才发觉礼堂里早已空空旷旷,剩下我和那双微笑的眸子,他走过来,望着我说:“一起去喝杯咖啡好吗?”
我点点头,和他并肩走出讲室,进了一间叫“郁金香”的咖啡室,柔和的音乐,优雅的装饰,伴着四周弥漫的浓浓的咖啡香,令人浑身舒畅,坐下来,点了咖啡,他那双眸子深深地注视着我,令我手足无措,他说:“你像早晨的清风。”“明月清风是令人怡然的,我也是吗?”
“是的,你是,其实在三个月以前,我已经认识了你,我的房子就在你的对面不远处,新搬来的,每天早上在阳台上我都能见到你的身影。”
“怎么我却没见过你?”
“我是来度假的,也不大常出门,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柳筠,你呢?”
“航,希望你能记住这个名字!”
航是个很有才华的男孩子,对人生对生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们谈托尔斯泰,谈泰戈尔,谈《牡丹亭》、《红与黑》,也谈音乐,政治以及对人生对理想的看法,可是言谈之中,我发现他很悲观,“人世间总有许多美好的一面,鼓起勇气来,你就会发现一个新的生活在等着你。”我最后对他说。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能收到航的一朵鲜花和一束短笺,字数不多,可句句都在倾吐心声,我也每每回赠一束短笺,不必天天见面,但我们的心已交融到了一起。
再次见到航,是在秋天的枫林园。
“你看,火红的枫叶是一幅多灿烂的秋景啊,秋的悲凉因有了它而富有诗意,听过‘晓来谁染霜林醉’吗?”航对我说。
“航,你还是没变,你太悲观了。”
“不,当有一天,你等待已久的感情到来之时,却发现不能去喜欢你所喜欢的人,你的心境会是多么地苍凉悲哀。”“为什么不能去爱,难道你心中的女孩子不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可是……柳筠,以后你会明白的。”“航,保重!”我握了握他冰凉的手。
日子一天天地在手中过去,航的短信渐渐地少了,终于,在一个红叶灼灼,浓雾袅袅的清晨,我收到航的一封长信和一大束玫瑰。
轻轻地展开信,航潦草的字迹纳入眼帘。柳筠:
原谅我太久不寄给你短信,我只想告诉你,我是多么地喜欢你——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你的倩影,你的清新动人已在我心目中扎根了,我等髭庆睾能认预标,让你了解我,让我也了解你。
还记得枫林中的一番话吗?是的,我不能去喜欢你,可是我又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你,是因为你我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只因你是我梦中寻了念了多少回的白衣天使,我也告诫自己,这种爱,只会徒增你我的烦恼,可是我办不到,我整日整夜地想念你。
十个月前我已得知我身患绝症一一血癌,只有一年的存活期,于是我父母不定期带我到这儿度假,可是偏偏,在我生命的蜡烛将要燃尽之时一一我遇到了你。
柳筠,你真的是个好女孩,如果,我是专程来游玩的,是个健康的人,我一定会好好呵护你,可是,我再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仅剩九天的生命历程了……
珍重,柳筠,生命中有你相知,我已无憾,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快快乐乐。
航字
我呆住了,航,原来,他的悲观来源于他的绝症,航太年轻了,生命为何对他这般吝啬?
我握着被泪水打湿的信,冲到街上,匆匆地推开了航的家门,航的温柔的母亲开了门,什么也没说,含泪的眼光望了我一下,便把我拉到航的床前,然后,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我看到航的眼中满是泪水。在他床头,“柳筠”两个字用大大的心形裹住了,这尘世间来来往往多少人,却全然没有对死神的恐惧,越是知道留在世上的日子不多,越会感到生命的可贵。
我用我真诚的心陪着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天,当巨大的悲痛压着我时,我的眼里只有航那双微笑的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