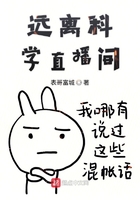敦煌、吐鲁番诉讼法制文书中的拟判文献主要指《文明判集残卷》和《开元判集残卷》,该文献本世纪初出于敦煌,为法国人伯希和掠走,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共存判文十九道,其中一道缺答判,判文皆采用唐代事例,引唐代律令条文断案,而案例中所用之人名,或拟用古代人名,如石崇、原宪、郭泰、李膺、李陵、缪贤、宋玉等。可能是取材于现实,而又加以虚拟润色。判文所表现的法律意识极强,文笔朴素,剖析具体,显示出相当高的司法解释水准。《开元判集残卷》亦为本世纪初敦煌所出,为法国人伯希和掠走,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该卷所载判文共有三道,其中一道不完,判词词藻华丽繁缛,排比典故,内容空疏,缺乏具体性,亦不见援引律条,王重民先生在其《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指出此件所载判文体例类似于《龙筋凤髓判》,评价非常准确。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律》的制定标志着儒法合流的最终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制定法的最高成就。与之相适应,运用判例弥补制定法的不足,推行制定法的实施,也成为唐代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制定法与判例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饶有特色的立法技术特点,具体而言,制定法的某些律文,往往离不开判例的辅助性说明与解释。以《唐律名例》“诸本条别有制”律文为例,这条律文的疏议,就采用的是判例注解的方法该条律文规定:“其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者,听从本。”对此规定,疏议就援引判例进行了注释假有叔侄,别处生长,素未相识,侄打叔伤,官司推问始知,听依凡人斗法。又如别处行盗,盗得大祀神御之物,如此之类,并是“犯时不知,得依凡论,悉同常盗断。其‘本应轻者’,或有父不识子,主不识奴,殴打之后,然始知悉,须依打子及奴本法,不可以凡斗而论,是名‘本应轻者,听从本。’”不难看出,采用判例的方式注释律文,一方面避免了律文繁冗的缺陷,回避了制定法立法的缺点,另一方面又发扬了制定法概括性强,适用性强的长处,保持了制定法立法的优势,这一立法的技术性特点,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文明判集》和《开元判集》的出台,是唐代这一立法技术特点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也是对《唐律疏议》法律精神的进一步揭示。
《文明判集》和《开元判集》可能是当时政府为规范各级官吏司法办案的判词范文,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推行,影响巨大,据日本学者池田温研究,日本古籍《令集解》卷13《赋役令孝子顺孙条》根据《古记》所引《判集》,内容与《文明判集》文献中所载寡妇阿刘案相同,《古记》是日本《大宝令》注释书,完成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前后,因此可知《文明判集》早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即已远传日本。足见其在当时的盛行。
二判例对唐法律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唐朝判例以广泛的角度揭示了唐政府的法律宗旨,通过判例形成了一系列我国古代司法办案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使制定法更加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深化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例如:
1、奉判:石崇殷富,原宪家贫。崇乃用钱百文,雇宪掏井。井崩压宪致死,崇乃不告官司,惧惶之间,遂弃宪尸于青门外。武候巡检,得崇送官司,请断。原宪家途窘追,特异常伦,饮啄无数救之资,柄息之一枝之分。遂乃佣身取给,肆力求资。两自相贪,遂令掏井。面欣断当,心悦交关,入井求钱,明非抑遣。宪乃井崩被压,因而致狙。死状虽关崇言,命(丧)实堪伤痛。自可告诸(邻)里,谙以官司,具彼名由,申兹死状。岂得弃尸荒野,致犯汤罗。眷彼无情,理难逃责。遂使恂恂朽质,望坆垅而无依;眇眇孤魂,仰灵榇其何托。武候职当巡察,志在本公。执崇虽复送官,仍恐未穷由绪。直云压死,死状谁明,空道弃尸,尸仍未检。检尸必无他损,推压复有根由,状实方可科辜,事疑无容断罪。宜勘问得实,待实量科。这件判例说的是,石崇殷富,原宪家贫,石崇用百钱雇用原宪掏井,后井崩将原宪压死,原宪死后,石崇因惧怕惶恐,没有向官府报案,而是将原宪移尸荒野,被武候捉住送官审判。
从判词看,如果石崇在原宪井崩被压而死时告诸邻里,求官请验,将死状加以明确,则原宪死于意外事件,加之石崇雇佣原宪掏井,原宪知道掏井的风险,故“肆力求资”,最后两协商一致,“心悦交关”,因此,石崇本可免责,确立了民间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风险责任负担原则。何题主要在于原宪死后石崇并未报官,而是将其移尸荒野,被武候捉住送官。石崇虽供称原宪死亡是因井崩被压,但办案官员认为如果不对尸体进行检验,对推压进行确证,就难以对原宪之死进行认定,“直云压死,死状谁明”,缺乏证据。因此,进一步指出,内有检尸别无他损,推压确有根由,才能确切原宪之死的原因。最后处理意见为状实方可科辜,事疑无容断罪。宜勘问得实,待实量科。”明确提出了定罪量刑以事实为根据的思想。敦煌、吐鲁番诉讼法制文书中的判例,关于刑事责任的论述,表现出了深刻的法律理念和法律思想。例如:
本判:郭泰、李广,同船共济,但遭风浪,遂被菝舟。共得一挽,且浮且竞膺为力弱,泰乃力强,推膺取桡,逐蒙至岸,膺失桡势,因而致租。其妻阿宋,喧讼公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共推膺取桡是实。郭泰,李膺,同为利涉,杨帆鼓泄,庶免倾危。岂谓巨浪惊天,奔涛浴日,遂乃遇斯舟夜,共被漂沦。同得一挠,俱望济已。且浮且竞,皆为性命之忧,一弱一强,俄致死生之隔。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悴彼沈魂,随逝水而长往,痛兹沦魄,仰同穴而无期。遂乃喧诉公庭,必仇郭泰。披寻状迹,清浊自分。狱贵平反,无容滥罚。且膺死元由落水,落水本为覆舟,覆舟自是天灾,溺死伊人咎。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俱缘身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喧扰。此案中郭泰、李膺同船共济,虽有船覆落水后,郭泰、李膺同争一桡的事实,“泰共推膺取桡是实”,但判例确认李膺溺死的直接原因,是舟覆落水这一意外事件,而非舟覆之后与郭泰同争一桡。判例在法理分析中所阐发的因果关系理论,区分了直接因果关系与间接因果关系的不同,强调了直接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刑事案件中意外事件免责的原则。
又如:
本判:弘教府队正李陵,往者从驾征辽,当在跸驻阵,临战遂失马亡弓。贼来相逼,陵乃以石乱投,贼徒大溃。统管以陵阵功,遂与第一勋,检勾依定,判破不与陵勋。未知若为处断?
经纬乾坤,必藉九功之力;克平祸乱,先资七德之功。往以蕞尔朝鲜,久迷声教,据辽东以狼顾,凭蓟北以蜂飞。我皇风踌龙旋,天临日镋,掩八绂而顿纲,笼万代以翔英。遂乃亲统六军,恭行九伐。俨七萃而云布。李陵雄心早着,壮志先闻。弯繁弱以从戎,负千将而应暮。军临驻跸,贼徒蜂起,骇其不意,失马亡弓。眷彼事由,岂其情愿?于时凶徒渐逼,锋刃交临,乃援石代戈,且前交战,气拥万人之敌,胆壮疋夫之勇。投躯殒命,志在必摧;群寇奢威,卒徒鱼溃。是以丹诚所感,鲁阳回落日之光;忠节可期,耿恭飞枯泉之液。以今望古,彼实多惭。于时统管叙勋,陵乃功标第一。司勋勾检、咸亦无疑。兵部以临阵忘弓,弃其劳效,以愚管见,窃未弘通。且饰马弓,俱为战备。弓持御贼,马拟代劳,此非仪注合然,志在必摧凶丑。但人之禀性,工拙有殊;军事多权,理不专一。陵或不便乘马,情原步行,或身拙弯弓,性工投石。不可约其军器,抑以不能。苟在破军,何妨取便。若马非私马,弓是官弓,于战自可录勋,言失亦须科罪。今若勘依旧定,罪更别推;庶使勇战之夫,见标功而勘己;怯懦之士,闻定罪而惩心。自然赏罚合宜,功过无失。失纵有罪,公私未分,更仰下推,待至量断。此判例范文逻辑分析缜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是一件难得的判例范文。此案首先分析了李陵失马亡弓的原因,或因贼来的突然,出其不意,或因李陵不善马弓,而谙熟投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李陵英勇善战,“气拥万人之乱,胆壮匹夫之勇,”以石投敌的行为,使贼徒大溃,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对其录勋重赏无可厚非。然而,李陵的行为虽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但其失马亡弓的行为,如果马非私马,弓是官弓,根据唐代律法,则必然触犯了唐律关于严格保护封建国家财产的规定,应科其罪。制判所依据的事实中“公私未分”,没有准确的交待李陵所亡弓马是官物还是私物,因而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调査,方能作出最后判决。这则判例范文一方面强调了行为的客观效果,另一方面强调了行为的法律性质,从而使录勋与失马亡弓成为相互独立的两个法律事实,体现了深刻的法理内容。
再如:
本判:豆其谷遂本自风牛同宿,主人遂邀其饮,加药令其闷乱,困后遂窃其资。所得之财,计当十疋。事发推勘,初拒不承。官司苦加拷谇,遂乃孪其双脚,后便吐实,乃款盗药不虚。未知益药之人,若为科断?
九刑是设,为四海之堤防;五礼爰陈,信把庶之纲纪。莫不上防君子,下禁小人。欲使六合同风,万方攸则,谷遂幸沾唐化,须存廉耻之风;轻犯汤罗,自挂呑舟之网。行李与其相遇,因此踅款生平,良宵同宿。主人遂乃密怀奸匿,外结金兰之妤,内包壑之心,托风月以遨期,指林泉而命赏,啖兹芳酎,诱以甘言,意欲经求,便行酖毒。买药令其闷乱,困后遂窃其资。语窃虽似非强,加药自当强法。事发犹生括讳,肆情侮弄官司。断狱须尽根源,据状便可拷谇,因拷遂孪双脚,孝后方始承赃。计理虽合死刑,孪脚还成骂疾,笃疾法当收赎,虽死只合输铜。正賍与倍赃,并合征还财主。案律云:犯时幼小,即从幼小之法;事发老疾,听依老疾之条。但狱赖平反,刑宜折衷,赏功宁重,罚罪须轻。虽云疋之赃,断罪宜依上估,估既高下未定,赃亦多少难知。赃估既未可明,与夺凭何取定?宜牒市估,待至量科。这是一起投药致人昏迷,然后窃盗财物的案例。判例首先简要介绍了案件事实与经过,随后提出如何定罪判刑,“若为科断”。判词首先从法理上分析了罪犯的行为特征,论述了强盗罪与窃盗罪的不同之处。加药使物主闷乱,然后窃取其物,看似窃盗,实为强盗。因为,从法理上讲,强盗罪的行为特征是使用暴力,“以威若力而取”。而“窃盗罪”的行为特征则是“潜身隐面而取加药后物主失去反抗能力,便与使用暴力使物主无法反抗具有相同的后果。
其次,判词对法律适用提出疑问。此案中,案犯由于抓捕后的拷掠成为残疾,虽然唐律规定“事发老疾,听依老疾之条”,但对于审讯中始成残疾者是否应按老疾之条办,却并不明确。因此,判词从刑宜折衷,罚罪须轻的思想出发,主张判处收赎。
第三,主张定罪量刑必须以赃物数额多少为基础。由于制判事实并未详细说明估赃的具体情节,赃数多少难知,无法进行具体科刑。因此必须要先牒审估定之后再予科断。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诉讼法制文书所反映出的两法官在适用法律时阐发的独特见解,足以有力的影响整个国家的司法活动。例如:
本判:秦鸾母患在床,家贫无以追福。人子情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实为孝子,准盗法合推缂。取舍二途,若为科结?
秦鸾母患,久缠床枕,至诚惶约,惧舍慈颜,遂乃托志二乘,希销八难;驰心四部,庶免三灾。但家道先贫,素无资产,有心不遂,追恨曾深。乃舍彼固穷,行斯滥窃。辄亏公宪,敬顺私心。取梁上之资,为膝下之福。今若偷财造佛,盗物设斋,即得着彼孝名,成斯果业,此斋为盗本,佛是根粮,假踔成功,因賍致福,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6侧镜此途,深乖至理。据礼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行益礼合计賍,定罪须知多少4多少既无疋数,不可巷科。更问盗赃,待至量断。此案中,秦鸾为了给久病床的母亲祈福,在家贫无资,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行盗取资。在尽孝与行盗二者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此案,成为该案的难点。判词认为,秦鸾为其母行盗取财祈福的行为,并非封建礼教所谓之行孝,其行为已构成了’盗窃罪,因此,如果不以治罪,便会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应依法予以追究。但由于制判事实没有明确秦鸾行窃得赃之具体数目,判词要求查明盗赃之数,以决定具体的刑罚。这一判词成功的确定了为了敬孝而盗窃他人财产的行为的性质,在封建礼教与法律冲突中,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在下面这一段判例中,司法官在封建礼教与法律冲突中,维护了封建礼教中提倡的孝道。
奉判:宋里仁兄弟三人,随日乱离,各在一所里仁贯属甘州,弟为贯属钎县,美弟处智贯属幽州,母姜元贯杨州不改。今三处兄弟,并是边贯之人,俱悉入军,母又老疾,不堪运致,申省户部听裁。
昔随季道销,皇纲弛紊,四溟皮骇,五岳尘飞,兆庶将落叶而同飙,簪裾共断篷而俱逝。但宋仁昆季,属此凋残,因而播迁,东西异壌。遂使兄居张掖,弟住蓟门,子滞西州,母留南楚。俱沾边贯,并入军团。各限宪幸,无由觐谒。了言圣善,弥凄冈极之心,眷彼友于,更轸陟岗之思。恂恂老母,绝彼旙玷,悠悠弟兄,阻斯姜被。慈颜致参商之隔,同气为胡越之分。抚事论情,实抽肝胆。方今文明御历,遐迩义安,书轨大同,华戎混一。难兄难弟,咸曰王臣,此州彼州,俱沾年土。至若名沾军贯,不许迁移,法意本为防奸,非为绝其孝道。即知母年八十,子被配流,据法犹许养亲,亲殁方之配所。此则意存孝养,具显条幸,举重明轻,昭然可悉。且律通异义,义有多途,不可执军贯之偏文,乖养亲之正理。今若移三州之兄择,就一郢之慈亲,庶子有负米之心,母息倚闾之望,无亏户口,不损王瑶,上下获安,公私允惬。移子从母,理在无疑。此案宋里仁兄弟俱是军士,驻防边州,而他们家在扬州,家有八十岁的老母,根据军队法律,不许迁移回家侍候老母,最后报请户部评判,户部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出发,对唐代法律的价值追求作了精确的阐述,“法意本为防奸,非为绝其孝道”。从而更进一步作出了“移子从母,理在无疑”的判决。
妇女阿刘案反映了封建司法官审慎用刑的法律思想。
奉判:妇女阿刘,早失夫婿,心求守志,情愿事故。夫亡数年,遂生一子,款与亡夫梦合,因即有娠。姑乃养以为孙,更无他虑。其兄将为耻辱,遂即私适张衡。已付婷财,克时成纳。其妹确乎之志,贞固不移。史遂以女代姑,赴时成礼。未知合为婚不?刘请为孝妇,其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