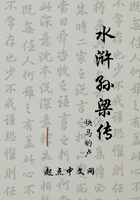我们都是头一次听说过这样的节日,都说边地的少数民族好客,从这个侧面便能看出来了。
姜三思有心劝道:“老乡啊,这也算陋俗啊,你们这不得赚一年的钱,一个月就给吃掉了啊?我瞧着你们的菜还挺硬的。”
中年男人嘿嘿笑道:“现在可不就是这样嘛!几位快进里面坐吧,晚上就睡这里,地方够大的。”
我们走进院中,看着几个外地游客坐在一张桌子前,便也凑了过去,找地方分别坐下。一个清秀的小伙看到我还拄着拐,便问:“这是中途出车祸了啊?”
我答非所问地说道:“小毛病,不碍事!”
引我们进来的中年男人也前问我们能喝酒吗,我正要说能喝,姜三思抢先说道:“酒量都不行啊,比不了你们。”
中年男人便说道:“那你们就少喝点吧,先来两箱吧。”说着就去搬啤酒。
我们吓了一跳,说少喝点,也要两箱?刚才说话的清秀小伙子说道:“你们还算聪明,说不能喝,要是说能喝,那几桌的人都会来敬酒,你一个人不喝上几十瓶都别想下桌,我前几天刚来时就吃过这么一次亏。当然,他们找出一个陪你喝的,也会喝上几址瓶的。”
我不由吐了下舌头,暗叫侥幸,早就听说少数民族都能喝酒,没想到能喝到这程度。我们和桌上的五个都相互做了介绍,刚才说话的清秀小伙子叫钱入库,是个来自由游的大学学生。他旁边的女生是他女朋友,叫郑秋玲。一个一脸胡子的大汉叫贾真金,自称是水果商贩,听说这个村的水果物美价廉,上门来熟悉下路。另一个染了一头黄毛的小年轻叫杜子藤,是个茶商,路过这里来看看本地的茶叶情况。
我们则称自己是几个朋友自驾游了来玩的,碰上食节纯属巧合。
我不由多看了几眼那个贾真金,这人如果是水果进货的话,说不定能探听一点消息。
开始我还和郑秋玲一样,说自己不能喝酒,但一会儿和大家聊了起来后,我便有点得意忘形了,于是起开一瓶啤酒就对瓶吹,一口气干尽了,把一桌子人都给震住了。而本地的几桌看到我这豪爽相,都拍手叫好起来,果然开始有人过来敬酒。
姜三思忙以我身体有伤,不能多喝酒为由,帮我挡下了不少,当然他自己便免不了被灌酒了。
我借着酒劲问郑秋玲:“你们来几天了啊?晚上住哪啊?”
郑秋玲有些不好意思,说道:“这里的风俗好像大家都可以睡在地上,我们也是大家一起睡在楼上的地板上。”她指了指木板楼。
我好奇道:“你和这些大男人挤一个地板上?”
郑秋玲的脸更红了:“嗯,我睡在最里面,阿库睡在我旁边。”
我有些无语,但人家风俗如此,怕是我晚上也只能这么睡了,到时我就说腿有伤,别人不能碰,画出个隔离带出来。
酒桌的菜还不错,鱼、肉、鸡、蛋上了几大盘子,还有些菜像是野菜,吃起来香味浓郁,吃起来感觉很舒服。我好久没有这么放开大吃大喝了,心情也畅快起来,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盘龙村时的日子。
引我们进门的中年男人也过来敬酒,这个面子我得给,马上和他一口闷了一杯。我一抹嘴问道:“大叔,你怎么称呼?吃你的喝你的,都没问过你叫什么呢。”
中年男人笑道:“俺姓刀,叫刀秋白,是外来的傣族人。村上能让俺办食节,说明信仰俺啊,嘿嘿,这个节一过,俺就成了地道的本村人了。”
我一愣,姓刀?那在村中路口卖芭蕉的老太太,好像就是推荐我们到村头的刀家来吃住,还说他家正在讨媳妇。难道这食节免费吃住是幌子,而是他在暗中选媳妇,这西南偏远之地,盅术横行,如果不慎,可能便被人选中下了情盅,心甘情愿嫁给什么糟老头子了。
我借着酒劲,故意试探道:“刀大叔,怎么只见一个人忙前忙后的,刀大婶也不出来帮忙呢?”
刀秋白收起了笑,说道:“俺当年因为赌博被赶出以前的傣族村子,老婆就离俺去了。这些年都是一个人过,不过不要紧了,等过了食节,俺就是本村人了,就可以再娶媳妇了。嘿嘿……”
同桌的人都惊讶道:“还有这种风俗啊,真是新鲜了。”于是对这事不停地问来问去,觉得天下之大,什么稀奇古怪的风俗都有。
我的兴致却已经消了下去,看他们说得正热闹,我却静下来思考。这事有些蹊跷,我倒没看出刀秋白有什么居心,他似乎就是个普通的乡下人。我蹊跷的是路口的老太太,她好像在预言着什么,比方说我时,说我的老公不得好死。和我配阴婚的那个鬼傀可不就是不得好死的吗?
她说刀家时,说这里要讨媳妇,但听刀秋白的语气,他只是办食节,并没开始考虑这事呢,但瞧着这样子,他真有可能在食节期间讨到一房媳妇的。这个老太太到底是谁,她是在预测这之后会出现的事吗?总之她肯定不是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
一研究起这些事,我便没有了吃喝的兴致了,一会儿工夫便推说自己酒喝多了,想去休息,于是李遇求把我扶到了楼上,看了看整个二楼居然没有隔断,全是睡在一个平板的地板上,面积倒是很大,看着有几百平米,如果只是外地游客住的话,倒是足够大的。
李遇求当警卫多年,对照顾领导这种事很有经验,也不用我说什么,便在二楼靠角落的地方选了一个地方,将地板收拾干净后,便从背包扯出一包东西,看他一会儿是铁杆,一会儿又是面料的忙活,居然很快组装出了一个帐篷出来。
我一见之下,欣喜不已,之前听到男女同住在地板,总觉得不大方便,没想到这李遇求居然会随身带着一个简易的帐篷,有了它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随口赞了他一句,便钻进帐篷呼呼大睡起来。中间听到外边不断上来人,因为是木质结构的房子,可以防震,但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有点晃动,一有人走楼梯理整个房子都跟着颤。
帐篷不时传来别人的感慨或惊讶之声:“哎呀,这是啥玩意儿?”“这帐篷好啊,这睡觉多方便啊。”“阿库,你怎么没想着带个帐篷啊,怕我还得和男人挤在一起……”
总之,我很快睡着了,但睡了一阵,便被热醒了,这帐篷的保暖也太好了,现在我们处身的上齐村正好在北回归线附近,大下午的,这一热人都觉得身体都要沸腾了。但我翻了个身,又接着睡起来,不好好休息哪有精力对付本地横行的盅术啊。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皮肤痒痒的,似乎有人在轻轻给我瘙痒,有麻酥酥的感觉。不由醒过来,向那个麻痒的地方摸去,却发现一个肉嘟嘟的东西慢慢爬在我的手臂上,我睁眼一看,居然是黑球。
我不由精神起来,这个黑球这么不安分,怕是饿了吧。它今天嗅到老太大送我的那个银镯子的气味,便一直像饿了似的,蠢蠢欲动,见我睡着了,居然自己出来长找食物来了。
我笑着在它的头上点了一下,黑球马上扬起多脚的脑袋向我抗议。我呵呵笑着,便把今天新收入的银镯子从口袋夹层取出,然后用手拿着递到黑球的嘴边。黑球马上把多只脚都伸长出来,把那镯子紧紧抱紧,张开大嘴便在镯子上咬了一口。那镯子立马便缺了一块。黑球把那块银子含在嘴里慢慢嚼着,我却发现银镯子里露出一小点黑芯,大概是民族自己冶炼的银子杂质太多了吧,不过这么明显的一个黑芯却有点太粗糙了。
黑球吃得很香,而且越吃越快,连续几口下去,便将手镯吃掉了一小截。我还没见它吃得如此快速的时候,不由轻轻抚摸下它的小脑袋。
黑球吃着吃着便开始挑剔起来,又一块黑芯被它直接跳过啃也不啃。我起初只当这镯子质量太差,怕是不值一千块。
少数民族的银饰品一般都是提取的银、锡混合物,含银量并不高,有的时候甚至只有锡没有银,但传统习惯上还是管这种饰品叫做银器。我猜想这个手镯便是不含银或者含银极低的,因为按照常理,盅虫是不喜欢吃甚至会不愿意接近银器的。
银器本身有辟邪作用,在苗族等少数民族之中,女人总是带上数量尽量多的银饰品,便有祛盅辟邪的意思。就是在西方的传说中,吸血鬼对银器也是颇为忌惮的,直接接触银器也会让其受伤。
而黑球对这镯子吃得如此甘美,我便猜想这手链含银量低,估计也就值个几十块钱,我肯买下来,就是因为黑球喜欢。
黑球现在开始变成绕着吃了,像是只吃一层银皮,慢慢地一个黑色的圆柱形的黑芯便露了出来。
我觉得奇怪,一个镯子才多大啊,怎么会里面出现这么大的黑芯呢?莫非是用银子把这个黑芯裹起来了?我轻轻地用手捏了一下,发现黑芯里面竟生出了反抗之力,我不由加大力气再掐了一下,那圆柱黑芯马上扭曲起来,但又快速地还原成之前的样子。我马上警觉起来,心中升起另一个大大的疑惑,“这东西不会是活的吧?”
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说不定这黑芯里藏着什么盅物,比方是情盅,那路口的老太太当初是硬把手镯送给我的,也许就是想在我身上下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