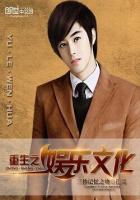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很久,又或许,只是看了那么一眼星辰。
只是,再盛的绿蝉酒已经渐凉,泡不开那一片傲峰渊蓝。案前的山魈也已经被吃得狼藉,突兀着一双眼,肉质已经变得干硬。
金衣仰躺在藤椅上,仿佛是眯了一会儿,摇着椅子,头也不回地说:“这星辰看得厌了,撤去吧!”
紫襟衣微微点头,只向天空拂手而过,宛若抹去风中残痕,便瞧得漫天斗转星移,月落西山,东山之巅渐起鱼白,金色的光泽将半边天空照耀地透亮,云层翻滚着,深浅不一,宛若鱼鳞一般。有细微而不可见的紫气自东方而来,落在紫云之巅上,酝酿着一颗绝美的晶石。
他伸手一招,将那绿豆大的晶石收入手中,对金衣递了过去:“收下吧。”
金衣转过头来瞧了一眼,饶有兴致地将这紫色晶石捏在手里,笑道:“啧,很是完美的紫气么,你不心疼?”
紫襟衣只看着一旁仅剩下的山魈,随手撕裂了两只大腿,递给金衣:“呐,吃吧。”
金衣接过两只大腿,好笑地问他:“你不吃?”
“我已经尝了滋味,足够了!”紫襟衣说着,便将双手枕在脑后,躺在藤椅上,看一树凝碧树叶在风中招摇,如舞女的裙摆。
“哈!”金衣也不客气,随手将那紫晶石按在自己的眉间,随即一手一只山魈腿,吃得津津有味:“看你这眉心弄得这样漂亮,我也就按在眉心好了,如此明显的地方,你若找不着,便真真儿是讨打!”
“知道了。”
金衣微微一笑,忽然便不吃了,随手将两只未啃完的山魈腿扔在地上,油腻腻的手在身上擦了擦,也学着紫襟衣那样枕着头,看着天空。
“不吃了?”紫襟衣看了一眼地上的山魈,问,
“凉了,肉硬了。”
“那就不吃罢。”
金衣叹息一声,幽声说道:“无相,我去了之后,就莫要再纠葛了,修为如你,早就该抛去这些,不必耿耿于怀。”
“好啊,若你能解开凝碧树的封印,我便自行封印记忆,直至你轮回归来。”紫襟衣淡淡道。
金衣沉默了。
“你放心不下,如何叫我放心?”紫襟衣问他。
金衣叹息一声,没有说话。
“将凝碧树的封印解开吧,能助你早日归来。你的神力被剥夺于此,转世投胎再也不能成为今世这般神兽了。”
“你养我啊!”
“解开吧,无相。”
金衣不肯回答,只看着叶嫩枝繁的凝碧树,微微笑着:“你这样也挺好的,养养鱼,逗逗猫,看凤栖梧桐,观南山虎下。时而种种树,赏赏花,听一听清风,纳一纳紫气,就这样挺好。”
“将封印解开吧!”紫襟衣不肯罢休,又问道,恳切无比。
“我若说不呢?”金衣舔了舔嘴角,用舌头从牙齿缝里挑出一根肉丝,“呸”的一口吐到一旁,却是用力过猛,连一颗牙齿都连带着吐了出去,他愣了愣,倒也没有多诧异,依旧躺好,说道:“今日已经答应你一件事了,总该有让我保留意见的权利吧?这封印会打开的,但我已经无能为力,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紫襟衣紧紧抿着唇,不语。
“你瞧上的那小子不是挺好么?让他照看这凝碧树,还让他开了一树凝碧花,就证明他就是那有缘人,他会代替我解开这封印,你着急什么?封印一开,有你苦头吃,倒不如趁着现在多运动,好加强你逃命的本事!”
“哈哈!”紫襟衣淡笑一声。
“西昆仑你去看过了吗?”金衣忽然又问。
紫襟衣微微点了点头:“远远地看了一眼,猫儿差寄奴回去了,想来也是不急。”
“兮和剑将出,你的事情便多了起来,好好把握现在吧。”
紫襟衣淡淡一笑:“又岂止是兮和剑?预仙师的三则预言,都已经初见其效,修真界再也安稳不了多久了。”
“哦?我倒是记得一个是关于天玄二十七年的预言,其他两则又是什么?”
“红莲出,鬼王复,帝阖屠尽万古枯。”紫襟衣道:“以及:山崩地裂,神鬼魔佛葬天关。”
“前一则我且知道些许,后一则是什么意思?”
“山崩、地裂……巫祁山、七绝地!”紫襟衣寒声道。
“巫祁山,七绝地!”金衣一愣,随即缓缓叹息一声。“如是多事之秋,如是多事之秋啊!”
紫襟衣微微笑着,没继续说。
“天地之间,哪里有什么亘古不变的道理,改一改,换一换,也挺好的,不是吗?”金衣笑了起来。
“是啊,挺好的……”
“不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道理,道理都在你这边,想来我也不用担心什么!”金衣又笑了起来。
紫襟衣点头说:“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我脾气不好吗?他们畏惧我,我便乐得清闲,你不用担心,起码这世上要我死的人没那么容易让我死的。”
“嗯,早看出来你洪福齐天了!”金衣笑道。
紫襟衣抿唇不语。
“我……”
金衣忽然哀叹起来,眼神微微颤抖着,那双眸子格外的明亮。“无相,我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去说……”“那就不必说了,我明白。”紫襟衣说。
“嗯,那就,不说了吧……”
金衣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缓缓闭上眼睛,宛若厌倦了世间烦恼,阖上眼睑,才发觉,此时的他,已经老态龙钟,再不复当日的风华正茂。他就如同睡着了一般,恬静而安详,仿佛是远离尘嚣的烦恼,干净无比。
紫襟衣神色一顿,深吸了一口气来,伸手举起琉璃尊,对着凝碧树遥遥一敬:“来,干杯!”
随后,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原本旭日东升,华光万千,此时忽然便飘来一朵乌云,默默地下起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如银丝练成线,密密麻麻地将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花草上如同沾染了一层细密的绒毛,然后渐渐凝聚成一滴晶莹的水珠,从修长的叶片上滑落下来,滴在土壤里。
弱水河上有一圈一圈细小的水晕,圈不开水波,只结成了一颗颗珍珠一般,然后沉入弱水之下,在河底铺成一晶莹的水层,与弱水分隔开,好似油与水形成鲜明的界限。
紫轩忽然抬起头来,悲亢地躺下一滴泪来,又与雨丝混在一起,变得格外浑浊。
白凤在梧桐枝头将头埋在翅膀里,细密的雨滴染湿了修长的尾羽,他蓬松了毛发微微抖了抖,往梧桐枝叶深处走了几步,听着雨滴洒在梧桐叶上细密的声音,心里头莫名传来一丝悲伤。
华庭凑在洞口内张望,牛犇屈膝跪伏在一旁,将头埋在膝盖里,眼神带着忧郁。他们双双对望了一眼,便各自回了洞口来,不出一声。
獠翾站在亭子里,看着湖面点点涟漪,心里也起了点点涟漪,他想想些什么,可是脑海中却苍茫一片,好似连记忆也没有,眼神之中唯独剩下迷惘的哀伤。
小雪儿在一块石头后藏着,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向凝碧树的方向,渐渐的,渐渐的,惊恐就演变成了哀默。身上的毛发湿漉漉地搭在一起,她抖了抖身子,用舌头梳理着。
“走了,还是走了……”她叹息着。
整个东来阁都笼罩在哀伤的氛围中,就连西方的沼泽也泛起了水泡,升起了水雾一片,南方的火墙的火势也被压抑下去,只剩一点星星之火,保持着不灭。
“哎”
一声叹息,在空气中闯荡开来,似要将什么人的心纠结在一起,又似要将什么人的眉拧成一股。
紫襟衣手中多了一把纸伞,撑开,举在金衣的头顶,雨落下来,染湿了他的一头紫发,狼狈了他的绝代风采。那只撑伞的手,一直不曾动摇过一分一毫,仿佛时间就静止在这里,没有了定义。
阁楼内,苍术抽了一口水烟袋,长长吐出一口气,有些沉重。
他回想起不少事情,可如今却好似烟消云散,只留存这丝丝哀愁。
少忘尘总觉得空气之中有些压抑,他看了一眼苍术,又看了一眼,终于忍不住问道:“师尊,是出什么事了吗?”
苍术抽了一大口水烟,烟雾从鼻子里喷了出来,成双成对。“金毛犼走了。”他说。
“金毛犼?”少忘尘一愣,随即一惊:“啊,是老祖宗!那他是……”
“嗯。”苍术微微点了点头。
“那先生他……”少忘尘忽然有些担心紫襟衣,他也不知道这担心从何而来,也许是从踏入东来阁第一天就听闻过这两人的传闻吧。
苍术瞪了他一眼,道:“他什么他?你若能起死回生,就闭嘴去做,你若不能,就闭嘴不做!”
少忘尘低了低头,他的确无能为力。
只是看着传世蛊的时候,他仿佛也多了一重心事似的。
雨,还是那么细细绵绵地下着。
东来阁很久都没有下雨了,凝碧树在雨中伸展着枝叶,被砍下的那一部分,在此刻渐渐延展,与先前一般模样。
举目四望,就好似天地突然失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