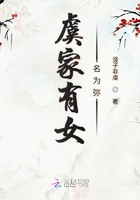谢七郎不知道这么晚上门是否适合,可有些莫名地情愫驱使他此时前来,叩门声响了三下,茗娘出来的比他意料的早。“谢郎君,什么事?”茗娘瞧着他怀里的红纱说。
“刘月梅让我把这个还给你,她跟你说谢谢。”
“月梅跟你说的?”茗娘惊讶地问。
“她给我托的梦。”谢七郎想了个解释。
“要是再等过几天,她就能穿上这身衣裳了。”
“所以说人世无常,有什么想做的事就尽早做。”谢七郎旁敲侧击地说。
“谢郎君操劳了一天,我给你煮碗汤饼吧。”
谢七郎坐在桌旁,看着茗娘在锅前忙忙碌碌地背影,说道:“其实可以仍叫织娘把这匹纱做出一身喜服出来,否则多可惜。”
“做完了给谁穿呀,知道月梅事情的人一定都很忌讳。”
“可你不忌讳啊。”
“我?”茗娘转向谢七郎,两手在围裙上抹了抹,“我穿给谁看呀!”她笑了笑,露出一颗小小的虎牙,紧接着又下面去了。
“那你想不想嫁人呢?”
茗娘的背部有一瞬间的僵硬,“嫁人是一定要嫁的,可得等缘分啊。”
“你看——”谢七郎喉结抖动了一下,“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呢?”
茗娘的背影彻底顿住了,锅中的水滚滚而开,过久的火候把汤饼都给煮碎了,茗娘没有说话。谢七郎挠了挠头,十分勉强地又问了一遍:“我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呀?”
“谢郎君怎么会突然说出这话呢……”
“想说就说呗,就怕你嫌弃我命硬。”谢七郎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扭头要走,“算了算了,我去刘家灵堂了。”
“谢郎君别走!”茗娘的两只手不知该怎么摆,“那个,我、我明儿个就叫织娘过来。”
在茗娘的注视下,谢七郎以默声定下了这桩婚事。
他也很出乎意料。
已经是第四日了。
他得先把刘月梅的丧事办完,才有闲暇办自己的喜事,正好这几天可以用来赶制茗娘的喜服。
茗娘把红纱交到织娘手里,织娘问起:“这是给哪家姑娘做的?”
茗娘嘴角噙着笑回道:“是给我做的。”
“你要嫁人了?”织娘听了好不惊讶,“你要嫁给谁?”
“操办丧事的谢郎君。”
“啊呀,那谢七郎命可硬着呢,全家都被他给克死了,这样的人你怎么也敢嫁!”
茗娘露出些尬色,直言道:“我不信这个。吴婆,我多给你加钱,劳您这几日尽快赶出来。”
第五日刘月梅下葬,谢七郎主持了整个过程,刘氏老夫妇哭恸天地,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谢七郎看着黄土一锹一锹填满墓坑,心中只想着一件事:这个丧礼办完之后,就该办他的婚礼了。
倒也没什么喜悦,他只是帮人完成个心愿而已。
谢七郎的棺材铺子自然是不能用的,茗娘开始将自己家里收拾成喜房,把白纱素料尽可能多的染成红色,好用这个颜色装点满整个屋子,使每个角落都能散发出喜气。
茗娘满心欢喜,可城中的其余人却因新流窜来的山贼而人心惶惶,刘月梅的死如同丧钟,在此城上空敲响警音。
第六日,茗娘在街上置办家物,却遇上了那个心坏的钱老爷,钱老爷嘲讽道:“听说你要嫁给那个丧门星了,难道是图自己的后事有人料理?”
茗娘不理他,尽管城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也都在心里暗暗把谢七郎叫做丧门星,可是她统统不想理,一心准备着把自己嫁出去。
谢七郎自然是知道这些言语,不禁有些后悔了自己的仓促决定,本是希望让茗娘了无牵挂地离开人世,结果此举却让她遭人议论。尽管谢七郎开始觉得事与愿违,可茗娘却对那些风言风语却置若罔闻,满心扑在婚事上。谢七郎有些不解,但又渐渐地生了些喜事临身的迫近感。
是呀,他要成家了,不再是一个人了。
茗娘人很贤惠,会染布,会下厨,长得也挺标致,无论她嫁与谁家去,那家都一定挑不出毛病的,这样好的媳妇怎么就嫁到他手里了呢。有时想想,他也觉得心里很有滋味,而忽略了这场喜事其实得成于一场哀事。
第七日,织娘把喜服送了过来,十个织娘连夜赶制,终于三日成衣,而茗娘也差不多打点好了一切,左右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拜天地,一切都很清简,也就是说,只等这喜服一到,他们就可以成亲了。
这天晚上,谢七郎又躺在棺材里,想着自己从明日开始就不必再睡棺材了,心中百感交集。忽然屋里出现了些动静,他知道鬼差又来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搭理他们。
鬼差揶揄道:“你居然要成亲了,还是跟那个将死的茗娘。”
“你们也没说过不许我成亲。”谢七郎的双手枕在头下,仍然是那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
“是没说过,我们只是来提醒你,别忘了三日后戌时把茗娘的亡魂带来。”
谢七郎的面色有些凝滞。
第八日,大婚之日。
白日茗娘去开了面,将自己收拾得很利索,而谢七郎显然比她将就许多,他们没有更多的钱去赶制两件喜服,所以只等时辰一到,他往髻上绑根红条,便可做新郎官了。
天一黑,便是喜时。拜堂行礼,喝合欢酒,两人往床上一坐,只差掀盖头了。谢七郎迟迟没有掀盖头,面前一对龙凤红烛燃出幽暗的光亮,窗外只透着黑夜的寂静,尽管满堂都映出喜庆的红色,但丝毫没有喜事的气氛,因为不见宾客贺喜,也不闻鞭炮鸣啸,他们的婚礼仿佛是什么私下的勾当,竟要无声无息,尽力不惹人注目。
连他们彼此之间也是不怎么说话的,谢七郎暗自琢磨,给姑娘这样一个婚礼,是否还算是心满意足?
“为何如此轻易地就答应嫁给我,不怕我克死你吗。”
“我与郎君都是福薄的人,只要你不嫌弃我,我也不会介意有关你的那些说法。”
盖头下传来茗娘轻柔的声音,她似乎并未感触到这婚礼的萧瑟气息,也不后悔如此轻易地与另一个人结合。他怎么会嫌弃她呢,她有什么可值得他嫌弃的,此时,谢七郎开始心怀感恩,茗娘的薄命竟让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好妻子,有生之年,他竟还可以有过一日正常人的洞房花烛夜。
他都快忘了自己是个人,而现在,他无比地憎恨起自己的命格,以及茗娘短短的阳寿,他想把这样的日子过一辈子。
盖头掀开,开过面的茗娘的脸光滑无暇,厚施****,重涂口脂,红白分明,平时素雅的茗娘在今夜多了些别样的味道,既光彩艳丽,也有点像陪葬的纸人。
茗娘用荔枝核一般的瞳光仰头看他,把他的心神浑都摄走了。
“你若不后悔,我们便是夫妻了。”谢七郎像是决心一去不复还的义士,怀着一种悲壮向她确认。
“唯郎君是从。”
茗娘没有落红,他似乎知道了什么,可又在无比美妙的夜晚里熟睡了过去。要让茗娘活下去,他想和她过一辈子——将熟未熟的瞬间,他在心里混沌地下了决心。
第九日一早,他一醒来便看到茗娘端着他们的早饭,两碗汤饼,升腾着浓厚的热气,勾着人垂涎,却又灼着人的口舌,让人迟迟吃不进嘴里,空留巴望,这两碗汤饼似乎像文人的论一样,佐证他娶到了一位贤惠的妻子。
只剩今明两日了,他端起早饭,已经想好今天要去做什么。
鬼差又揶揄道:“新郎官找我们什么事?”
“怎么才能不让茗娘死。”
“明天就是她命尽之日,你却把我们找来说这个?”
“你们地府是做生意的地方,再跟我做一回生意,我要让茗娘长久地活着。”
“那得看你能拿什么来换。”
“我的命,行吗,把我的命换给她三十年。”
“不行。”鬼差毫不留情的否决了他的打算,“你现在的寿命不是你的,只是地府给你的宽限,要知道,你自己就是个早该下阴间的人。”
谢七郎暗暗咬紧了牙,“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还想让我拿什么换!”
“容我们回去请示判官大人,再给你答复。”
“那你们最好尽快!”
夜晚,谢七郎小心翼翼地撩开床被,悄悄下了床,而茗娘还在沉睡。
“忘了你搬到这儿了,我们还去铺子里找你呢。”
“别废话。”谢七郎披着衣裳说,“判官怎么说?”
“判官大人说,只要你肯签下魂契,永远给地府做事,他可让茗娘多活几年。所以要么你跟我们下阴间,要么明日戌时把茗娘的亡魂交给我们。”
谢七郎攥了攥拳头,“能不能再给我几个时辰,戌时之前,我自会下去。”
谢七郎钻回被窝,忍不住注视起茗娘的脸,平稳细弱的气息从她的鼻子里喘出,他受到这细细的熟睡声的感染,也因而觉得满心安稳。此刻他心里有了些愧疚,因为自己马上就要让她成为寡妇了,不知留她一人在世是否真的会好,或许到时候又要遭受非议,这回不是因为他克妻,却是因为她克夫。
成亲三日,夫死身寡,一定少不了长舌。
谢七郎轻抱住这个细柔的身体,遗憾自己只做不到三日的郎君。
这时茗娘的喘息逐渐急促起来,直到最后从他的怀里惊醒,似乎做了噩梦。
“怎么了?”
茗娘缩在他的怀里,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