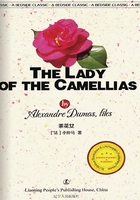程小雨这才知道,总经理是个来自北京的“太子党”,不仅总经理是,从未露过面的大老板也是。香港的当事人绝大多数都对自己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唯有这些来自内地的大亨才会无所忌讳。因祸得福的程小雨傻乎乎地从总经理室出来,连路都不会走了,想去厕所小便,走进女厕所听见某位女同事哇的一声叫,懵里懵懂退出来,又走进了部门经理办公室。部门经理正在接电话,看见他进去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程小雨,不,程、程副经理,我刚接到你被提职的通知,还没来得及给你安排办公桌,你就来、来啦?
一向习惯低调再低调的程小雨又高兴又害怕,特别是那天回家看见“狗仔队”在永兴街一带转来转去,他脸色苍白地躲到弄堂角落给老婆打电话。别急着回家,他说,我俩到维景酒店旁边那个茶楼去吃晚饭。电话里传来高峰期地铁中嘈杂的喧闹声,老婆声嘶力竭地说,那儿子怎么办,我买了他爱吃的菜,说好今晚做给他吃的!再说明天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天天去吃酒楼啦?
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的是程大明,他背着这些报纸重新走上了上访之路。背包里还有一面颜色暗淡的锦旗,是他被捕后培侨中学的“爱国师生”敬赠给他的,不知怎么被他从母亲留下的箱底中翻了出来。原先的机构敷衍他,他去找议员。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培侨校友出身的立法会议员,这位议员却说,在普通法下,好像没什么途径可以翻案,你或可向法庭申请延长上诉期,但要有充分理由。他耸耸肩说,政治因素一般不会考虑啦。程大明怒气冲冲地反驳说,不是政治因素我干啥上街去,我吃饱了撑的?
程大明蹒跚地走到赤柱走到海边,海风吹拂他的苍苍白发,他很想回到监狱去,那里可以养老,可以从铁窗里向外瞭望天空海洋,还可以触摸过去的梦境。而今的他,已经对自由不感兴趣,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程大明说扯淡,生命没了,爱情也没了,那自由也不是你的自由,而是别人的自由了。
岁月不知不觉过去。我大哥最后还是毁在了那条伤腿上,阴雨天隐隐作痛,没站稳滑了一跤,造成他中风而半身不遂。我不得不四处托人将他送进了老年医院。所谓医院,其大部分功能就是一家养老院。大哥要求和另外两位孤老住在同一个房间,免得看见其他老人隔三岔五有晚辈探视,心里不平衡。
我想给他搞个单人间,没这个门路。他刚住进去半个月,同屋就死了两个。半夜里时高时低的呻吟声,令人毛骨悚然,砰的一声响,一个老人从床上跌下,大哥喊着老兄老兄,却无法下床。他按床头的电铃,按了好久才有个从苏北乡下来的护工揉着惺忪睡眼走过来。大哥指着地上的老者,哆嗦着,护工蹲下去摸了摸,霍地站起身,乖乖,他诧异地说,这老头儿这么容易就死啦?!
我大哥这一辈子,除了做少爷的辰光,都是体力劳动者,他最大的爱好是吃肉。但是老年医院基本吃素,我探望他时带去一些鸡鸭熟肉,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才跟我说话。我找医院商量,能否由家属多出一点钱,让他吃得稍稍好一点?院方摇摇头说不行,你愿意多付钱别人不愿意,难道只给你做肉菜吃?
江南梅雨天,阴霾的日子总是少不了回忆与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灵魂的寂寞。有时候,我想我大哥和程大明这种人,好像是父母亲多余生出来的,寿命活得不短,却一辈子受苦受穷。别人或许有跌宕起伏,他们没有。他们为青春时节的骚动付出了终生的代价。上苍对他们真的很不公平。
这天晚上下雨,雨泼打着车窗外人行道两边梧桐树的枝叶,我驱车去看他,身边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路上我跟程小雨又通了一次电话,小雨说,他大哥已经坐在电脑桌前了,正在将信将疑地问他的侄子,这是真的吗,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那位老邻居老朋友啦?还能面对面的说话?
我将电脑调试好时,我大哥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从前他不是这样的,戴上手铐脚镣时他也不曾这样。他靠在床背上,直直地注视着视频,他说,是你吗,你真是大明吗?屏幕上有一点模糊,摇摇晃晃的,我大声喊,小雨,你把所有的灯打开,把灯光对着你哥!小雨答应着,将一盏台灯照到程大明脸上。程大明眯缝着眼睛,将脸都贴到了电脑上去,他侄子扳着他的肩,将他拉回去。程大明就势抱着侄子,哇地哭出声来,嘴里喊着,张家大哥啊,我好悔!我当初应该跟你一起跑去内地的啦,我不该留在这里啦,我真的好悔好悔。
我大哥看着窗外,雨依然下个不停,陈年往事湮没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程大明的开场白令他心里发堵。你别哭啦,别好悔啦。他瓮声瓮气地说,你好好看看我,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见面啦,说这些话就浪费电,也浪费时间了。
后来他对我说,程大明好像已经有点老年痴呆症了。这个发现令我大哥更加悲伤。雨水落在病房的窗子和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同屋的两位孤老,一个耳朵聋了,一个本来就是哑巴,不妨碍我们与香港的交流。但是,一个人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要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变成语言,即使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可能是一种危险。何况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之间有着一段莫名其妙的距离,隔着一重铁幕。
两个可怜的老头儿隔着视频相握,两个人伸出的手都是又苍白、又虚弱、又浮肿,手背上还长着褐色的老年斑。生命是短促的,我们看见时间在他们那没有血色的脸上飞快地消逝。程大明说,老哥呀,你当年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却向他人说你想回香港呀,这样你就完蛋啦。我大哥说,那时跟你商量不也一样?说不定你比人家更积极地把我卖了。程大明呵呵地笑了,将颤抖的双手蒙住老泪枞横的脸,说,老哥你真幽默,你说得我都有些惭愧了。
我们不能没有一点幽默感,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快的完蛋。我大哥认真地告诉他。但是我们的幽默感越来越让人辛酸,程大明说,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当年了。
明日黄花,他说,我们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我坐在他的床边,对面是那位哑巴,我看见哑巴在这养老院的病床上辗转反侧,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枯枝般抖瑟瑟的手,好像在梦中求人似的。这是一个从福利厂下岗的残疾人,白天院方将他的某个亲戚叫来过了,说是欠费太多不让他再留在这里了。不留在这里让他去哪里呢?没人回答。屋子里有一股霉气和一种很难形容的老人气,一种接近死亡的气息。我走到窗前,打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雨渐渐地小了,院里院外都睡得静悄悄的,只有电脑视频前的两位老人还在谈话。可说的话,好像很快就说完了,不可说的话,尽在默默对视的不言中。
让人惊讶的是,沉默许久之后,他俩居然又有了新的话题。这话题是程大明提起的。他抖瑟瑟地举起一张报纸,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点红晕。这个世界还是会变的,他的话令我们感到突兀,他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底层人士拥护这样的领导!报纸覆盖了整个荧屏,中国西南的一座城市广场上,红旗漫卷,歌声震天,广场周围警察荷枪实弹,黑色的囚车呜呜鸣笛疾驶街头。我和我大哥面面相觑了,愣了好一会儿,我大哥才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扳起指头算了算说,可怜,大明你今年七十五还是七十六岁了,五十年前开始做的梦,这一辈子就做不醒了吗?
报纸挪开了,程大明不服气地瞪着我大哥,两个老得苟延残喘的老朋友,好像山野小路上狭路相逢的两个老仇人。我突然忍不住了,凑过去插话。我说,小雨,你还记得当年吗,你请米老鼠吃的那顿饭?装着大喇叭的宣传车从街上驶过,宣布冻结所有“有问题”人的存款,一群学生和市民在马路边上高喊着坚决拥护的口号。
当然记得啦,程小雨将脸凑在他哥脑袋旁对我说,你骂他们是一帮傻瓜。他脸色深沉地回忆。米老鼠说,去******坚决拥护。我忘不了他的精辟总结,程小雨说,米老鼠说过,上面那些家伙,把所有有点钱的人都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不仅把这些钱拿去给自己拉帮结派,还借此获得没钱人的拥护。
报纸上这种人跟当年有什么区别?!
一层白翳遮住了程大明的昏花老眼,他迷茫地看着我们,佝偻着身子,很孤独,很苦涩。他想反驳我们,却无从反驳,半个世纪不安分的情绪在他的心里悸动着,思绪总是逆向出现,也许他也知道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病态,但是他已无法改变。
两个早已脱离了主流社会的老人,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的主题其实已远离他们。他们重新安静下来,莫名地互相瞧着对方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天真笑容。这个画面有点诡异,因为这种“天真笑容”隐藏在老树枯藤般的皱纹后面。
病房里很潮湿,从病床的床单被褥枕头和湿嗒嗒的地板窗台的每一块木料铁件上,都能闻到那股霉烂的气味。我看到大哥的眼睛也潮腻腻的,他抬起一只手,默默地揩着眼里的水珠。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动了我,也惊动了我大哥以及视频那边的程大明兄弟。走廊上突然亮起了灯光,一名护工在喊医生,黑黝黝的院子里晃动着几个灰白色的人影,医生进了病房。过了一会儿,真的只有一会儿时间,那杂沓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一辆破旧的担架车吱嘎吱嘎地响着被推了出去。我听见程大明微弱的喊声,他在问我大哥你那里发生什么事啦,病房惨白的日光灯照在我大哥脸上,他哭一样的笑了起来,泪花迸溅中,他嘶哑地说,又有一位老兄弟走了,见上帝去啦。
于是我走过去,我跟程小雨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程小雨说好吧,叫他儿子将视频关了,我看见的最后景象是小伙子抱着程大明,替他擦着那皱纹重重叠叠的脸上的泪水,他耐心地说,伯伯您放心吧,您跟他们不一样,您常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所以,你的日子应该还长着呢,过两天,我再让您跟您这位老哥通话吧。
(首发于2013年第6期《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