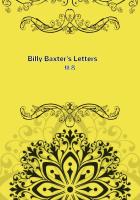我真想让你做我的姐夫。米老鼠因此而泪汪汪地瞧着我说。你比我姐小一岁比我大半岁,挺合适的,再说现在我们的家庭成分也快跟你家差不多了。他咬咬嘴唇,转脸对程小雨说:来斤加饭酒吧,三角五分的普通加饭就行。程小雨去柜台上买了酒,米老鼠端起杯子猛喝一口。湘九,米老鼠青面獠牙般说,我理解你大哥为什么坐牢了。他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要是我在香港待过那么多年,我******也会想着偷渡回去的,那个美国还是法国的诗人怎么说来着,生命啊女人啊,若为自由什么的,两者皆可抛?
西湖边天气很冷,但我们身上因为喝了酒而觉得很暖和。我们走到六公园公共厕所,撒完尿我和米老鼠就脱衣服,他换上我的人字呢黄皮,对着镜子左照右照。万里古德,他跷起大拇指说。我却一分钟都不想在湖滨路上逛了。我得赶紧回去洗你这身蓝皮,用烧滚的碱水泡一遍,再用透明皂狠狠地洗,我对米老鼠说,要不,我浑身都会长疥疮的,跟路边的叫花子没啥区别。
终于盼到了程家姆妈的回信,我关上门,程小雨抖瑟瑟地撕开信封。天好像亮了,又好像还在半夜里,这信的内容让我们心里七上八落。骚乱已经完全终结,香港的秩序恢复正常;程大明被判了七年徒刑,刑期从被羁押那天算起。港英当局发出公告,敦促所有参加过骚乱活动的人去各警署自首以获宽大处理。程家姆妈在信中举了几个例子,都是香岛或培侨中学的学生,因为是一般“非法会众”,自首后被判入监一年以下或缓刑。程家姆妈喟然长叹说,“这些学生尚未成年,来日方长,不自首又能怎么办呢?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只能这么做了。”
我们难忘在雨夹雪中从延定巷走到火车站,再慢腾腾走回来的过程。城市的街巷变得黑暗、曲折而漫长,我们看着浓重的夜色一点点地吞噬了桥栏干与行道树,不由得想起监狱铁窗和叮当作响的沉重镣铐。我们在火车站售票窗口前徘徊许久难以取舍。如果回去自首,首先将面临的不是港英当局,而是罗湖桥这边的边防警察,因为程小雨是偷渡过来的,所以他只能偷渡回去。想象中躲过后者比前者困难要大多了,程小雨说,他身上带着香港身份证,万一被抓住的话,大不了坦白交代后被遣送回去就是了。
我摇摇头。我说这边遣送你是没啥了不起,那边却会增加你一个偷渡罪。程小雨烦躁不安地说,增加就增加吧,用米老鼠的话说,虱多了不痒债多不愁。我说那多判你两年怎么办?两兄弟都在牢里,你爹娘还活得下去吗?
一辆卡车突然在我们身边爆了胎,车子和飞出的轮子使我们耳朵里灌满了绝望尖锐的鸣叫声,一位女同胞下了车,她说,真他妈倒霉,这下子半夜也到不了我爸妈那儿啦!我愣了愣,然后惊枪兔子般地从地上跳起,飞快地跑过去追那只轮胎。这轮胎骨碌碌地转着转到了护城河边,一半还在岸上一半悬在了河面上。我扑过去,在它即将掉下去的当儿抱住了它。
我滚着这会飞的轮胎回到卡车那儿去,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连声说谢谢谢谢。小花狐疑地瞪着我和程小雨,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拽着朝驾驶室推。我挣扎说你干什么,我不能扔下我表弟。小花哼哼了一声,松开手说,那咱们就都坐车上去吧,反正有车棚的。我心虚地问,你爸他老人家乐意见到我吗?他曾经告诫过你弟弟,不准他老跟我混在一起的。小花不以为然地笑笑,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还有啥资格瞧不起你?她转过脸对程小雨说,上去吧,不远,就在钱塘江对岸!
卡车换上了备用胎,司机踩下油门,车子猛地往前一冲,我们在车上挤成一堆。小花推开我说,老实点,你身上一股老碱水味儿。我坐直身子,在路灯和月光下看着她,觉得她那种撒娇的模样很滑稽。你爸他没资格瞧不起我了,你还有资格对吗?小花朝我撇一撇嘴,踢我一脚说,当然了,我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你是被****对象,这个地位能平等吗?我腾地站起身,我们下去,我对程小雨说,既然不平等,怎么能坐在一辆车上?
程小雨还没爬起来,我的腿被小花抱住了。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她撅着嘴唇说我,犟着不让我挣脱,她说,你也太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了。车子颠簸得厉害,我不得不重新坐下去,我苦笑说,你是工具我是对象,你不说我也清楚得很,但是你总得给我一点活下去的信心不是?小花愣愣地看着我,眼睛里慢慢地有了一层雾气,对不起,她轻声说,我不是有意的。
我的前十七年中很少经历这种独特的场面,程小雨想必也一样。车上沉默下来,我们的耳边掠过冬天凌厉的江风。小花斜倚在驾驶室的后背上,将整个身子缩瑟在蓝色的警棉大衣里面,脸色苍白,失去了我们上车前的鲜活。车子已经驶过了钱江大桥,眼前是大片空旷荒芜的原野,路边有一些东斜西歪的房屋,狗在村子里吠叫。汽车离开了大路,向一条泥泞的机耕路上开去。
我把小花扶下车,她的腿有点麻木了,那脸上也好像哭过似的,眼圈红肿着。程小雨替她拿着一个网兜一个纸箱子,里面大多是吃的东西。低矮的平房跟我大哥住的劳改场几乎一模一样。一个瘦削的身影被幽暗的月光投射在平房前的泥路上,凝固不动地盯着我们,就像一棵老树的影子那样。那一刻,我确实挺佩服这个十恶不赦的老头子,他身上有种死不改悔的精神,落到这种境地了******还站得如此挺拔。
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被你娘从罗湖桥下铁丝网塞过来的小家伙。他对我说,我儿子总爱跟你混在一起。现在又轮到我女儿了?
老爸。女儿嗔怪的声音在夜的旷野上显得娇柔无力。我看见老头子咧开嘴笑了,充满某种恶趣味的快乐。我低下头,看见自己和程小雨的影子萎缩在地上,很像两个进宫请安的奴才。我是她的马仔。我低三下四地说,谁叫我生来就是无产阶级****的对象呢。
老头子“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重新打量我,然后转过脸去看程小雨,终于,他侧身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小花已经跑到平房的门廊下去了,她推开门,我们就听见了她娘的哽咽声。算起来她娘那年只不过四十五六岁吧,却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她的压抑的哭泣声在夜的农场上空回荡着,引来一阵阵草狗的狂吠。
白发老妪坐在病榻上招呼我俩,原先丰腴白皙的她,现在又黑又瘦,不停地咳嗽着。她说,湘九你穿的好像是我儿子的衣服呀,那他现在穿什么呢?他穿得比谁都暖和,我安慰她说,他不仅换走了我的人字呢外套,还拿去一件毛线衣,我娘给我织的,米老鼠却说他穿着更合身。
有的人身上会带一些传奇的故事,过去他们对我感兴趣,现在转移到程小雨身上。老头子的眼光真是太毒辣了,他扑朔迷离地看着小雨,看得这少年坐立不安手足无措。你不是广州的学生,你是从境外过来的。问了几个听来很平常的问题后,公安分局老局长直截了当给他下了结论。我和程小雨倏地站起,悲哀地瞧着门外的茫茫夜色,又跌坐下来。门外停着那辆大卡车,膀大腰圆的司机打开车窗在抽烟,那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仿佛一盏盏警告我们的红灯。
为什么?我有气无力地说,死死盯着这个老狐狸狡黠的双眼。老头子坦然一笑说,我问他学校还上课吗,他应该说“没上课”,而不是说“冇上堂”,我问他以前跟公安警察是否交往过?他冲口而出他家楼下就住着一位“差人”。如果说前一句还可以解释为广东方言的话,后一句就根本是两种制度、两个世界所用的词汇了。你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哪个地方将民警称为“差人”的?!
程小雨已经缩成了一只毛毛虫。除了我,房间里有三位新老警察,他们像猫看老鼠似的看着他。这是一个残酷的耐人寻味的等待过程,等待这孩子彻底坦白交代。我紧紧握住程小雨的手,我说,别害怕,他们不会害你的。这孩子呜咽起来,他说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要隐瞒什么?反正横也是一刀竖也是一刀,你们看着办就是了。说着他将手伸进怀里往外掏东西,先掏出他的身份证,再掏出他的学生证,然后是他妈咪的来信,最后掏出一只红袖章来。香岛中学“湘江评论战斗队”!小花惊讶地抢过去看,眼睛里冒出了崇拜的小火花,程小雨,你了不起啊!她说。她把红袖章递给她爹娘看,她声音发颤地说,这是一位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斗争的自己人,咱们一定要坚决做好他的堡垒户啊。
本来打算做王连举的程小雨,现在闯进了李铁梅家。不管老家伙受到多少委屈,小花她爸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李玉和。革命者遇到革命者,这事情就比较好说了。老头子反复看了程小雨的证件,确信他所说都是真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点燃一支烟,沉吟起来。我提心吊胆地瞅着他,同时观察周边环境,只要他提出任何我们不能接受的做法,拼死也要夺路而逃。
我有个老战友在罗湖分局,老头子终于重新开口说道,以前是副政委,现在还是不是就不清楚了。老头子喷出一口浓烟,在腾云驾雾中斟字酌句,你去找他吧,把情况都跟他们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我想,他们会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给你帮助的。
屋子里充满劣质烟草的烟雾,老头子趴在一张油腻腻的小饭桌上给程小雨写那位老战友的姓名地址,小花她娘拍拍胸口,继续吭哧吭哧地咳嗽着。小花忧郁地瞧着老头子把信纸折好,送到程小雨手里,忧郁地看着他一迭声地表示感谢。我看看她的神情,心里就有一种对老家伙的怀疑和惶恐。果不其然,当我们一起告别两位老人,回到车上去时,车子一动,小花就跟程小雨说,别听他的话,不能傻乎乎地去找那个副政委!我说为什么,怕牵连谁吗?她略含幽怨地望着我,说,不是牵连谁的问题,而是不了解对方现在的处境、观念和变化。万一他坚持一切都要按程序办呢?这事情就没有转圜余地了。
千万别以为被批斗了几回,他们的思想就会转变了,十八岁的小花同志老谋深算地说,这些老家伙呀,多数都是花岗岩脑袋。
四
程小雨跟我们挥手说拜拜,车轮在他的脚下滚动,我们呆呆地站在月台上,煤烟带着炭黑的微粒飘落在我们身上。程小雨当初来到这里,还是秋天,城市和乡村还能看到一点金黄色,而今已是春寒料峭,太阳变得暖和了些,背阴之处,积雪还没融化。所谓我们,其实就是米老鼠和我,少得可怜的两个人,两个没地方上学或者上班的少年,两个小瘪三。
小花在派出所上班,空下来就修修指甲,她确实不必来给程小雨送行了,该做的一切,她都做了。她给罗湖分局那位副政委家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政委的儿子。小花啊?知道,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啦。南下的时候,你爸是营长,我爸是教导员对不对?两人争着向同一位小姐献殷勤对不对?哈,你爸那个大老粗怎么争得过我爸这个小白脸啊,该小姐后来就成了我妈啦!米老鼠对我们说,我总算纨绔了吧,我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这小子绝对是个衙内,整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真纨绔啊。
小花说程小雨你要找的就是这种人,江湖义气,天马行空。小花说我打听过了,他家老爷子现在被整得比我爸还惨,写他的大字报简直就是一部********。老爷子被关进去了,没人管的衙内就更是四处游荡。小花想了半天想不出贴切的形容词,她说你们香港人怎么称呼这种人呀?程小雨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小花同志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他就是一个“古惑仔”。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古惑仔,而在于他是跟程小雨站在一条战壕的同志。香港骚乱最严重的时候,大约有一百多名声援的“沙头角民兵”跟巡逻的香港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这位衙内当时就在现场。他在电话里激动地向小花姐弟大吹法螺,说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民兵送过弹药,亲自抬着伤员去医院等等。小花说你在沙头角随时能见到那些香港警察,你不怕人家报复吗?他们哪敢,小小的分局副政委的儿子说,这个地盘上谁他娘的敢跟我对着干呀?!
小花说程小雨你即使暴露了真实情况,他也只会帮助你而不会出卖你。
我的不安并没有随着火车车轮远去,我把手放在米老鼠肩膀上,觉得双脚发虚,好像踩在一堆棉花上。心里老是萦绕着一种可怕的陌生的感觉。程小雨找不到其他退路,我想帮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几个月朝夕相处,我跟这个本质淳朴的少年真的已成了兄弟。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我们小看了那个古惑仔,他开了一辆运货车亲自到广深交界处迎接程小雨。当然他不知道程小雨是回去自首的,小花含混地告诉他,有个离家出走的香港少年来旅游了一趟,现在想悄悄地回家。古惑仔说,进深圳就要查边防通行证了,啰嗦得很,干脆委屈他一下吧,跟猪猡们一起回家。
起初还好,程小雨跟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他递给小雨一支烟,抽吧,他说,这车上味儿太大。猪猡们在后面哼哼着,屎尿横流,程小雨被臭气烟味熏得眼泪鼻涕一起流出来。古惑仔拍拍他的肩,受罪了吧,你这个不良少年,他笑着将手指弹一下小雨的脑瓜,哥也受罪啊,受那位老花花女儿的委托亲自送你回家去啊,你可要改邪归正哦,从此做个你妈咪的乖宝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