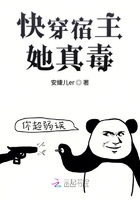可顾艳还是没有走的意思。
奇怪了!
都第六天了,省城所有顾艳该去的地方她都去过了,梦时代逛过了,苏圃路逛过了,“化蝶”也化过了,顾艳怎么还舍不得走呢?
是孟文发现了顾艳的秘密。
孟文那天夜里待在书房,他习惯每天睡觉前在网上的“清风”棋院下一盘围棋的,一般只下一盘。但那天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对手,就多下一盘了——因为是暑假,他有点放纵自己了。大约一点钟的时候,他刚结束第二盘棋,正准备睡觉了。这时听到客厅里的门“咔嚓”一声,继而楼道里也有隐约的脚步声,他警觉起来。小区前不久才出了事,前面楼里的苏教授家进了小偷,从排气扇窗口爬进去的,把苏教授的笔记本电脑偷了,笔记本里还有好几篇没发表的论文呢,据苏教授讲,那都是要引起学术界轰动的论文,其价值远远大于那个联想笔记本电脑。孟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胆小,不敢打开门察看楼道,而是从厨房探头往下看楼下单元门,既然楼道里有脚步声,那么小偷总要从单元门出去的吧?果然,单元门里走出一个人,奇怪,是个穿裙子的女人。
门廊前有灯,虽然灯光昏暗,但孟文还是能看出,那个穿裙子的女人好像是顾艳。
孟文赶紧去看孟骊的房间,顾艳真的不在,只有小灯。
按说孟文这时应该叫醒我,顾艳是我的弟媳,深夜一点出门,太诡异了。
但孟文没叫我,我的睡眠状况有些糟糕,如果醒了,就再也难以入眠了。而且,更可怕的是,我很可能会因此而陷入一种失眠的恶性循环,处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的我,按孟骊的说法,是会很可怕地发生畸变的。我会变得既萎靡又暴躁,还会歇斯底里,还会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把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升华成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完全不像个文学教授,而像个哲学教授——还是叔本华那样的悲观主义哲学教授,怀疑爱情,怀疑生命意义,言语里还会流露出严重的轻生倾向。所以,他们父女俩尽管平时总结盟在一起对付我,只有逮了机会,就会你一言我一语配合默契地对我进行冷嘲热讽,但在我的睡眠这个问题上,他们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护我的睡眠,就像保护国家野生动物一样。
而且,孟文以为顾艳马上会回来的,他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时候还出门——或许突然胃不舒服到药房去买药?我们小区前面有一家二十四小时开业的“黄庆仁药栈”;或许到小区后面的大排档去吃东西了?顾艳显然不喜欢吃“天花乱坠”,特别是晚餐,总是吃得蜻蜓点水,这时候有可能饿得受不了,于是偷偷到大排档去吃碗汤粉或吃几个蒜蓉烤生蚝。她特别喜欢吃蒜蓉烤生牦,在饭桌上说过很多次。
孟文为了等顾艳,又下起了围棋,下着下着就忘记顾艳的事了。
顾艳回来已经是早上七点了,她还买回几个糯米藕丝烧卖。她说她醒得早,所以去湖边散步了。小区不远有个李白湖,早上很多人去那儿慢跑或遛狗的。隔壁的周教授,就每天一大早牵了狗,拿本书,到湖边去散步。
我一点儿也没怀疑顾艳,虽然顾艳穿着吊带裙,高跟鞋,但我觉得顾艳就是那种穿吊带裙高跟鞋去散步的女人。
孟文当时没作声,他觉得这事太严重了,要三思而后言。
但还没等孟文三思。顾艳第二天夜里又花枝招展地出去了,孟文这才觉得不告诉我真的不行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还有这样的事?这女人是不是疯了?竟然在姑子家彻夜不归!
我立刻拨打顾艳的电话,电话关机。
这大半夜的,她去哪儿呢?干什么呢?
还是孟文冷静,他去孟骊房间,打开了孟骊的电脑——顾艳出去之前,一直都在玩孟骊电脑的,或许那儿会有蛛丝马迹。
果然有,顾艳的QQ头像还是亮着的,是个戴了满头珠饰的京剧小旦,叫“顾盼生姿”。
QQ上有她出去前的聊天记录,和一个叫“一杆老烟枪”的——之前的想必都删了。
怎么还不出来?
再等等。姐姐房里的灯刚刚还亮着呢。
我等不及了。
呸!
我真等不及了!
呸呸呸!
不信?不信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顾盼生姿”打了个娇羞的头像。
“一杆老烟枪”回了个流口水的头像。
我现在到“锦绣”门口去接你?
嗯。
——显然,顾艳是和网友约会去了。
怪不得顾艳不回去,原来她在这儿勾搭上男人了。
只是,这“一杆老烟枪”是她来这儿之后才勾搭上的,还是来这儿之前就勾搭上了?
应该是之前就勾搭上了,不然,短短几天,不至于狎昵和污秽到这个程度。
那么,她来这儿就是为了“一杆老烟枪”了。什么小灯要看鹦鹉,纯粹是幌子。我也是幌子,孟文也是幌子——待在自己的姐姐姐夫家,不管待多久,马可肯定也是放心的。
我们都被顾艳耍了!
这个不要脸的****!
我第一个反应是要给马可打电话。他不是一直把自己的老婆当宝吗?我要让他看看他的宝,是个什么货色!
但孟文阻止了我,孟文说,你看看时间,现在是半夜二点,你这个电话一打过去,马可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
这倒是。马可有辆本田摩托,接了这种电话,一定会不管不顾地骑了摩托就往省城冲。他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骑摩托呢?夜里国道上货车又多,司机经常疲劳驾驶,货车一个趔趄,可能就把马可的摩托辗得粉碎了。
那怎么办?
孟文的意思,等顾艳回来再说。
我等不了。
只好先给马果打电话。家里有什么事,我一般也是先和马果商量的。
孟文对此倒没有反对。
马果的反应和我一样,先惊诧,再愤怒,再幸灾乐祸。马果激动地说,顾艳的好日子这回怕是过到头了。
我们都看不惯顾艳,打她一嫁到我们家,就看不惯。结婚第二天,直到中午前她没出房门,中间是马可出来给她端早点的,包子稀饭早冷了,老蔺——也就是我妈,又重做了鸡蛋面条,端进去不到一分钟,马可又端出来了,说顾艳不爱吃面条,要吃酒酿汤圆。家里没汤圆,马可看着老蔺,那意思,是要老蔺出去买。我们以为老蔺要发作的,太过分了!但老蔺没有,老蔺看一眼老马,老马于是嘀咕着出去买汤圆了。我们不知老蔺唱得是哪一出,是曹操的“先礼后兵”?还是在用《郑伯克段于*》里“姑息养奸”那一招?
我们觉得顾艳太没家教了,太没羞耻了。新婚宴尔中的男人,哪个不是女巫胯下的扫帚一样,女人指向哪,就飞向哪。但有家教的女人会把这扫帚藏好,不会骑了它乱飞。我们都知道的,恃这种宠而骄矜的女人,又轻薄,又愚蠢。
何况,男人能宠你多久?一个月?一年?我们都是过来人,知道男人的这种宠,最靠不住。我们在一边冷笑,等着看马可对顾艳的爱情消失。它总会消失的,这一点,我们坚信。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顾艳十指纤纤把自己当金枝玉叶了,顾艳飞扬跋扈把自己当杨玉环了。但我们从来不在马可面前说什么,顾艳作得再过分,我们也只是相视一笑。我们有时候甚至会怂恿她作。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诩教养好,我们是有文化的小姑子,不屑在背后挑拨离间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想让顾艳“自毙”,只有这样,我们才更觉解恨——这是我们的刻毒,我们再自诩有文化,也还是小姑子,身上也还有女人的嫉妒天性,我们实在看不得马可对顾艳的那种好法。
但顾艳的朱楼一直不塌。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小灯都上幼儿园了,小灯都上小学了,我们望穿秋水,我们曲项成鹅。但马可对顾艳的好,还是一如既往,不,甚至比既往还要好。
我们好奇死了。顾艳到底是用什么招数让马可一直这么爱她?
马果说,难道她会房中术?
我白马果一眼,这种话,她竟然能说出口。但我其实也狐疑过这个。朱周曾经说,男女关系,一旦解释不了,答案就只能到床上去找。朱周说这话是因为我们单元里的一个女人,那女人是历史系的资料员,姓姜,长得普普通通,还比她老公程教授大六岁。每次看到玉树临风的程教授十分温柔地挽了他夫人的胳膊出门时,我和朱周都叹为观止且觉得匪夷所思。朱周说,没别的,只能作形而下的理解。那资料员长得像只鹌鹑,圆滚滚的,十分肉感。程教授可能喜欢那种“软肉温香抱满怀”的感官快乐。我对朱周的话不以为然,但我喜欢听朱周这样胡说八道。顾艳的长相虽然比那资料员好一些,但也就那样。她面若银盘,胯若骏马,或许以小城的审美观,也勉强可以算个美人。毕竟对女人最原始的审美,是表现在生育方面的。但马果坚决否认,马果说,小城的审美观怎么啦?小城的审美观也不是就只会审美女人的******!
马果是中学英语老师,对汉语的修养,还是差。一着急,说话就直白了。我为此批评过她,但马果说,你不懂,我这是返璞归真之美。
马果这是在讽刺我,因为我经常用“返璞归真”来狡辩的,我素面朝天,马果批评我,我说“你不懂,我这是返璞归真之美”;我衣着随意,马果批评我,我也说“你不懂,我这是返璞归真之美”。
我们虽然一直看不惯顾艳作,但我们也一直拿顾艳没办法。
但这回,顾艳的好日子怕是过到头了。马果说。
我也这么以为,我不相信马可知道这事后,还能对顾艳好?好成那个样子?
怎么办呢?我问马果。
要不,我们慢慢来?
什么意思?
就是先别告诉马可。
为什么?
你不觉得凌迟比大劈的惩罚更严厉?
比起我,看来还是马果更讨厌顾艳。毕竟马果和顾艳在一个地方生活,因此对顾艳的作,也看得更充分。
顾艳又是早上六点回来,又买了几个糯米藕丝烧卖回来。她说,她又去李白湖散步了,早上李白湖的空气真是好。
顾艳还是穿着吊带裙,高跟鞋,一夜没睡,她非但没憔悴,反而容光焕发。
这个****!
我阴沉着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言不发。
你几点出去散步的?我本来想问,但话到唇边,又打住了。
顾艳没看我的脸色,兀自进孟骊的房间蒙头睡觉去了。
中午时,我们还是吃“天花乱坠”,这一回,天花更简单了,只有生菜一样,飘在清汤寡水里。
小灯扁着嘴,不肯吃,但顾艳不管他,顾艳有些神情恍惚地用筷子挑了饭粒往嘴里送。
我看不得她这幅慵懒的样子,简直把自己当杨贵妃了。“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顾艳的表情,现在就是那种该死的表情。
你姐夫昨夜一夜没睡。我突然说。
顾艳抬头看我,神情仍然缥缈得很。
你QQ名叫“顾盼生姿”?我又说。
顾艳的脸这才煞地白了。
马果说,顾艳变了,从前是杨贵妃,现在变成花袭人了。
她一反常态,侍候起马可来了,姿态也像花袭人,奴颜婢骨的。
我能想象顾艳当花袭人的样子,她原来学过下腰。练过下腰的女人,柔韧性都很好。当花袭人,还不是看家本领?
马果说,她就在边上觑着,只要顾艳略略有些翘尾巴,她就阴阳怪气来一句,夜里到李白湖散步感觉如何?或者,一杆老烟枪是谁?
顾艳立刻就老实了。
马果极得意。她喜欢这样,捏着顾艳的七寸,然后看顾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我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合适,这样对马可不公平,马可有权利知道真相。
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
哪怕真相一点儿也不美?
是的。
所以你一直素颜?
这是什么话?我有几分不悦了。
可世上大多数人是喜欢浓妆艳抹的,顾艳喜欢,马可也喜欢。
你的意思,是不告诉马可了?
你觉得马可能离开顾艳吗?
我不知道。但那是马可的事。
我知道,马可是离不开顾艳的。这是顾艳的本事,不服不行。虽然一怒之下,马可因为男人的面子,可能会和顾艳离婚,他只能选择离婚不是?他总不能在两个姐姐的眼皮底下做一只缩头乌龟?但男人谁没有做乌龟的习性?退缩是男人的本能,在可以退缩的情况下,男人都是选择退缩的。但我们把这事一说,马可就不能退缩了——不是不想退缩,而是不能退缩,他只能伸了脖子前进,哪怕前面是刀山,他也只能往前了。之后呢,不用之后多久,他会后悔,这是一定的!他那么爱顾艳,不后悔才怪。再之后,他就恨我们了,他会想,要不是我们两个从中挑拨,他们就不会离婚了。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爱情和婚姻里不应该有背叛和欺骗。
你太理想主义了!其实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小城,很普遍的。
我冷笑。确实是普遍。不论马可,还是马果,都被普遍到了。
马果的事,全家没人知道,除了我。
就在前两年,马果也出过类似的事,她和一个男同事,夜里去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在城外,是有些偏僻的,白天都人迹罕至,一到夜里就更没什么人影了,如果有,也多是一些野合的男女。但他们还是被她老公的一个朋友撞见了。那朋友是个多事的人,立刻报告了马果的老公。马果的老公狠狠地扇了马果几耳光,然后把马果赶出了门。马果于是可怜兮兮地来找我——她老公不信任她,却一向很信任我这个大姨子的。马果说,她和那个男同事,只是在公园附近偶然遇到的,然后一起去公园探讨教学上的事。我不信。这话鬼才信。但我是马果的姐姐,别无选择,只能相信马果。有意思的是,马果的老公竟然也信了。当我向他转述马果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自己都羞得面红耳赤。但事情真的就这样过去了。
你和那个男同事夜里九点在公园真是探讨教学?
我后来问马果。马果说,你问这话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一个文学教授,而像小城里那些长舌妇。就算我不是,就算我做了别的什么,又有什么关系?不过像学生考试作弊一样,一个学生,谁还不会偶尔做一次弊?
我就没作过弊。
一次也没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