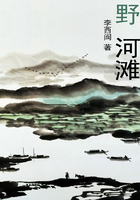1983年的秋天,咋就那么阴雨连绵?校园里那几棵歪脖子柳树下落满了衰败的叶子。鹅卵石铺就的甬道上也满是泥浆翻滚。土墙灰瓦的教室台阶上沾满了从鞋子上刮下来的污泥。
那个秋天,我脚上常常套着的是一双黑色的橡胶雨鞋。这种鞋现在已经很少见,或许已经绝迹了。他的材料就是今天的橡胶雨靴,但没有雨靴那样高的筒,就是和普通的解放鞋一样高低的鞋面。这种雨鞋是给没有足够的钱买雨靴的人准备的,就如今天的廉价房一样,是给穷人的生活必需品。这种鞋,雨大了防不了水,也挡不了泥,天晴了穿在脚上不透气,捂得脚臭。
往往,我从家里往学校走的时候下雨,我就很不情愿很无奈地穿上那双雨鞋。和我结伴去学校的是正芳,我们村里唯一姓韩的一个女生。她上初三,我上高一。我们俩的教室都在学校的后院,我的教室是第二排最西边的教室,她的教室是第三排最西边的教室,坐在教室里,透过窗子玻璃就可以看见对方。正芳不止一次对我说,不要穿你那双雨鞋了。我知道她是好心,我答应她不穿雨鞋穿的就是那双黄胶鞋——洗得发白的胶鞋,除此就是我母亲做的布鞋了。在上高中之前,我一直穿母亲家做的布鞋。暑假结束,我成了村里唯一考上高中的学生,从八里外的公社来到镇上读书,我就再也不穿母亲的布鞋了。
但从供销社买的胶鞋和雨鞋同样没有给我带来自尊和荣耀,更多的还是屈辱。
屈辱是正芳给我带来的,但我不会怪她。正芳班里的三个女生因为正芳知道了我,认识了我,虽然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那三个女生是我们学校穿得最时髦,打扮得最漂亮的女生,听正芳说,为首那个是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镇上医院医生的,一个是学校老师的。这三个女生每次见到我和正芳来到学校就高声喊:“雨鞋……雨鞋……”,然后就不怀好意的笑。我的脸一刹那间就红到脖子根,正芳就骂她们不是东西。
那时候,老师在班会上强调纪律时,总不忘加上一句,严禁给同学起外号。而我的外号“雨鞋”不是我们班上的同学起的,老师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每次远远地看见那三个不怀好意的女生望过来的眼光,我穿雨鞋的脚就不知该给哪儿搁,我恨不得地下有个缝,忽然就钻进去无影无踪。可我知道,我只要还在这个学校读书就永远也远离不了她们。就是在我没穿雨鞋的日子里,那三个卖烧馍不离笼拌的女生也会远远地喊“雨鞋……雨鞋……”
我曾经给母亲说了不下十次,我不穿那双雨鞋了,给我买双雨靴吧!可每次我的愿望都在母亲的叹息声里化为乌有。我知道,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要盖房,一个要结婚,我父亲每个月五六十块钱的工资买黑市粮都紧巴呢。
那个秋天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不顾母亲的劝阻,执拗的没有去上学。因为这个礼拜老天的脸总阴着,天空中的雨丝总也没有断过。正芳一次次给我捎来老师的话,让我快快去学校上课,都被我无言地拒绝了。在外教书的父亲礼拜六回家,从我母亲和正芳嘴里知道我没有去学校的真正原因后,破天荒没有骂我。我父亲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头上摩挲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的礼拜天,我父亲早早去了镇上,他找到了供销社的主任。我父亲掏出他一个礼拜的工资买的纸烟递给没拿正眼看他的主任。我父亲说,我今天就用这买粮食的钱给孩子买一双雨靴。你知道,这样,我们一家半个月就要吃稀饭了。可是,孩子上学要紧呐!……孩子大了,有脸了……算我求你,你给你的女儿说一声,再不要喊我的孩子“雨鞋”了,好吗?……算我求你……我父亲同样的烟递了三个人,同样的话说给三个人,三个人都被我父亲感动得连连点头。
后来三年的高中学习中,再也没有人喊我的外号了。当我奇怪地问正芳这是为什么时,正芳告诉了我这中间的秘密。她说,那三个女生不让她告诉我的。她们说,我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