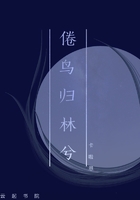次日清晨,骁卫军进入兰陵境内,在兰陵城西南十里处立营扎寨,冯远程令杨尚守营,自己率领近卫,到北面武卫军的驻营来参见徐汝愚。
从十月下旬始,刑坤民率领五校军便是绕着震泽湖行军,月余时间,行进一千二百余里,分兵接管沿路城邑,骁卫军进入兰陵境内的同时,两万五校军主力也进驻到兰陵东南的锡山城。随之其入锡山的还有吴州境内的四万降军。
樊彻见徐汝愚将两地的降军都集中到兰陵来,暗暗吃惊,暗道:难道要将十多万人马一下子都调到江水北岸去?早间传闻徐汝愚有觊觎东海之心,看来不虚,只是这十多万降军,又能抵得上什么大用?且不说士气大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连完整的指挥体系也建立不起来。
徐汝愚将南闽收归治下,南闽十数万降军尽归麾下,徐汝愚先组建卫戍军,又借义安战事,将卫戍军重整,纳入宿卫军的体系之中,不过新获得三万精锐之师,所耗将近一年的时间。
南闽一战,主要是徐汝愚与宗政、颜氏之间的战争,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南闽世家临阵倒戈,投向徐汝愚这一边,因而在徐汝愚重组南闽政局的时候,吸纳了大量南闽世家的人才;也正因为大量起用这些人才,才迅速稳定南闽的局势。
徐汝愚能放心起用这些人,与其父徐行有莫大的关系。徐行在南闽平匪之时,郑梦淮、洛山阳、彭奉源、何炯义、周宗昌等人与他相交甚厚,徐行与郑梦淮、洛山阳、马街亭、周宗昌更有半师之谊。
江宁出于打击祝氏的目的,悍然发动越郡战事,祝氏分崩离析,祝氏一系的归降将领人心惶惶,江宁也不会放心起用这些极易遭敌方势力策反的将领。樊族归降,由于樊文龙的关系,樊族的地位不会急剧下降,余杭降军会相对稳定,归附将领也大抵可用,但是要获得徐汝愚以及江宁诸公对樊族的这份信任却是极难。
樊彻正在营帐中胡思乱想之时,徐汝愚派人来请。
决意归降之后,樊彻已不复当初为一方霸主的锐气,性子变得谨小慎微;在徐汝愚从容儒雅的气质相衬之下,显出几分龙钟老态。冯远程率领骁卫军进入兰陵之后,兰陵的军务都交由冯远程、子阳雅兰、樊文龙等人主持,徐汝愚不大理会营中军务,倒常邀樊彻一道巡视军营;樊彻此时也没有当初离开余杭时的那般惶惶不安了。
江宁田舍翁,想来也不太坏,樊彻一边在心里如此安慰自己,一边随护卫去见徐汝愚,走到中军营帐,徐汝愚、邵海棠、张仲道、方肃等人却在营帐外相候。
徐汝愚说道:“今天我与邵先生欲去余杭军大营,邀樊翁一起过去。”
樊彻微微一怔,说道:“敢不从命!”
彭慕秋率领百余骑青凤卫护卫,众人离开武卫军大营,策马往东北而行。
江宁在兰陵周围设立三处大营,将兰陵围困当中,每一处大营的兵力都要多过兰陵城里的守军。樊文龙率领余杭降军在兰陵城东北结营兵力虽众,兵将士气与战力却不及其他两处大营。
青凤骑以百骑一队在三处大营与兰陵城之间游弋,将兰陵守军完全封锁孤城之中。城野之民都被勒令避入村寨、坞堡之中,兰陵城周围近百里方圆几乎看不见人踪,只有在接近村落、集镇的地方,才能看见村民在屋舍附近活动。为了避免兰陵军混迹在村民之中,青凤骑一般不接近村寨;若是平民无故接近游骑,也会遭到无情的射击。游哨要是在野外宿营,也会避开村寨。
遥遥望得见高耸的兰陵城墙,徐汝愚身子微挫,跨下骏马便缓了下来,视野里,尉潦正率领一队精骑汇合过来。
徐汝愚指着尉潦衣甲上染着的血迹,微皱着眉头,问道:“哪里染来的?”
尉潦拿着鞭梢朝后一指,说道:“顺这条溪河上去,有座小寨,西营派人过去叩寨征粮,让人打了出来,让我碰着,领人冲了一轮,将寨墙推倒,还未往里冲,就听人说先生过来了。”
尉潦所指的方向,冉冉升起一股黑烟,中间火焰腾腾,隐约有啼哭嘶嚎之声。徐汝愚剐了尉潦一眼,斥道:“征粮遭拒,也不用毁人村寨。”轻夹马腹,骏马如箭窜出,踏上溪边小径,往黑烟燃起处驰去。
邵海棠若有所思的望了尉潦一眼,与张仲道等人说道:“一起过去看看。”也扬鞭策马,紧随徐汝愚身后。
河床铺满卵石,清洌的溪水流淌,时至冬季,寒风袭来,却是溪水的温度较高,蒸腾氤氲水汽。两岸疏林里铺满枯黄的落叶,可以看得见林子对面零星的光。
徐汝愚等人赶到拒征的村寨,寨墙的外围已集结了三四百名青凤骑将士。青凤骑与青凤卫同属徐汝愚的亲兵,普通将士也都认得徐汝愚、邵海棠等人,分出十余骑迎过来。
青凤骑百人为一队游弋兰境内,遇到敌情则能迅速集结,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远避。
徐汝愚目光扫过众人,默不作声,寻了一处高处,策马上去,居临细观村寨布局。
溪河从此上去,又窄了一些,屋舍错落分布两岸,最上头有几进庭院颇深的宅子,护村寨墙土夯而成,只在临水的地方用砖石加固。溪水左岸缓坡上的寨墙塌坍了一片,想必是尉潦所为。寨墙缺口探出几双惊恐失措的眼睛。
徐汝愚手指着那处,眼睛却望着尉潦,说道:“从那里冲下去,可以稍稍借势;但是从那里下去,不到二百步就是平民屋舍,你就不怕有人暗中挑动平民生事。”
尉潦说道:“村里头人住在上头,上面的寨墙都是石砖混砌,寨墙上有箭垛子,深宅的院墙也厚,骑兵强攻难免有伤亡,我想将寨子里平民都赶出来,然后一把火烧他奶奶的……”
徐汝愚双眉一挑,说道:“青凤骑负责游侦,出现敌情,才可以协同步营作战,何时让你来攻寨子?”
邵海棠双眉紧锁,下了马,走过来,说道:“世家修寨筑堡,如星子散落于越郡大地,势弱抗征抗税,势强侵略乡野,确实让人头疼。”
江宁在兰陵附近集结了十数万的人马,粮草若从江宁运来,所耗甚巨。徐汝愚虽然施政宽仁,却深知从敌境征集甚至掠夺粮草是军队持续作战能力的保证。
徐汝愚所忧却非眼下征粮之事,而是日后如何治理这片鱼米之乡。
徐汝愚微微叹道:“世家宗族制在中州大地上延续了数百年。曾有‘在朝为名门,在野为乡豪’之说,却是在朝的名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家。北胡崛起,汉廷屡受打击,内廷势弱,在朝的名门衰退,在野的乡豪势力却急剧膨胀起来,逐渐成为割据地方的群雄。”、
徐汝愚手指着村寨上头的深宅,说道,“乡豪以武据守堡寨,以宗法约乡人。推及城邑,所行还是这一套,在险隘或交衢筑城,官长兵弁驻守其中,约束乡野;推及新、旧两朝之中州大地,骨子里又有什么不同?”语气带着些恚怒。
邵海棠微微一怔,听徐汝愚的话,不单对乡豪筑寨之事不满,更多的却是对行政结构里的宗法本质不满。
樊彻站得稍远,但是徐汝愚说这番话也没刻意压低声,以樊彻的修为自然听得只言不漏,心里暗暗叫奇:徐行著《置县策》意在扭转世家权倾地方的权力格局,择险隘处置县筑城,官长兵弁驻守其中,可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听徐汝愚的话,却不满足于此。
倒是方肃听得徐汝愚的话,垂首沉思,若有所得,却一时还想不通透。
徐汝愚收敛起微恚,缓缓说道:“江津、雍扬、汴州都曾是主客户人口达到数十万的大城,旧朝时的泉州,人口曾有一度超过百万。我有时在想,这些大城,与那些占据要害之地而修筑的郡府大城,到底有什么区别。”
樊彻忖道:江宁行《置县策》,择泉州、永嘉、青枫、溧水、凤陵、江宁等地治为大城,正是沿着茶马商道这条路线,正要张口说来,细细一想,却发现问题却非表面上看来的那般简单,继续深思,愈见其中复杂。
自古以来,统御之术、控制之要,限制民众也。
雍扬之所以成为大城,万民出入流动也。
多一分流动,则少一分控制,此乃历代帝朝限商、禁商的根源之一。
樊彻暗道:若能改变统御之术的根本,或能更改一二。但是这样的话题过于敏感,不是自己能说出口的。
徐汝愚似乎一时兴起,说及这事,也没穷究其中的深意,矮下身子,招呼方肃、张仲道等人上前去,说道:“此时下令拆去吴州、余杭两地的世家坞堡,是否尚早?”
邵海棠望了樊彻一眼,问道:“子彻以为如何?”
樊彻听徐汝愚的意思,却是有意立即就下令拆去两地的坞堡,只是有些过急了。
徐汝愚见樊彻脸上迟疑之色,笑道:“樊翁有话仅管说来,江宁没什么好,却没有因言获罪这条。”
樊彻微振神色,说道:“彻以为有些过急了。且不说那些乡豪,便是平民也习惯居住在壁垒寨墙之中。”
方肃说道:“乡豪以宗法控制乡民,乡民习以为常,视枷锁不为枷锁,汝愚曾说百年相易。虽说垒墙不过形式,但是要一时间都拆毁,却是不易。”
尉潦说道:“余杭暂且不论,吴州、兰陵等地,大军压境,挥刀所指,有所阻碍,也能克服。”
徐汝愚笑道:“却非用兵就能荡平一切。越郡经历战事甚频,吴州、兰陵等地,虽然没有燃烧起熊熊战火,但由于祝氏穷兵黩武,大量青壮劳力征入军中,这些地方的生产同样遭到严重的破坏。还是暂时保持稳定为好,只是这样一来,流民就不能立即填进这些地方,需从荒芜之地重新开垦土地耕种。”
只是那里还有流民可以填进来?樊彻这么想着,脸上却不动声色。
徐汝愚等人在此停了片刻,一队步卒过来,拖数辆大车在后面。
尉潦率领数百骑绕到小溪的上游,从溪水里捞起顺水而下的几根木头,绑到大车上,左右各用四匹骏马,拖着大车朝寨墙急驰。南侧的寨墙上站着数十名护丁,诧然望着朝寨墙冲锋的八匹骏,也忘了将手中长箭射出。
将撞上寨墙里,骑士控马旋身,八匹骏马堪堪避过寨墙,侧驰过去,后面拖着的大车却顺势撞上寨墙,只听得见訇然巨响,地动山摇,从箭垛口探出身子观望的七八人,一齐给震落下寨墙,无数泥块粉尘落下,罩得满头满脸。尉潦也不上前去捉人,只令身侧骑士取下背后拓木弓射杀之。
灰尘散尽,抹灰寨墙从撞击处显出数百道细小的龟裂来,大车在寨墙撞成无数碎块。
再这么来一下,寨墙就会坍塌。
尉潦正要令人拖另一辆大车去撞寨墙,却见墙上支伸了一面求降的素旗来,随即一张鼠目肥脸之人探出半个头来,尉潦转身去看徐汝愚,却见徐汝愚正策马离去。
尉潦忙对身侧一名左尉说道:“你在此受降,小心提防着些,也不要坏了规矩。”挥了挥手,领着精卫跟了上去。
徐汝愚等人在彭慕秋、尉潦率领的二百余精骑的护卫下,折向兰陵城奔去。兰陵城门紧闭,城门外都是青凤骑的游骑,城墙之上兰陵守军披坚执锐,刀戟如林,折射着昏白的日光。
徐汝愚等人在射程之外,绕过兰陵半座城池,正要策马往余杭而去,却见东城城楼之上,突然竖起祝昆达的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