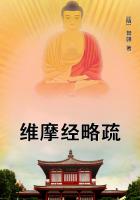在这次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南京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当蒋介石在西安他的那间“囚室”里一边研读着他的《圣经》,一面与循循善诱的周恩来进行着谈判时,这场民族危机就开始在首都政界那错综复杂的某些阴暗角落里,闪现出一线光明。
来自西安的最初消息,对国民党的官僚们产生了极强烈的震动。南京方面的人士平素更习惯于清谈,而不惯于采取行动。虽然,在这个政府中也不乏若干能员(而不在政府中当官的能员则要多得多),但他们中几乎没几个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行政权力。颇为典型的是,在起初召开的那几次可算得上是讨论应急措施的会议里,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争论议事日程和维护各自的“面子”上。直到最后,现任财政部长,一位留学美国带来某种民主主义情操的自由派人士孔祥熙博士,才被指定坐在了委员长的位子上,作为行政院的代院长。
孔博士在南京政府中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因为他是属于“宋家王朝”的成员。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家族体系,一度完全左右着中国的内部政治。他娶了宋霭龄,在各自都有一番惊人婚历的非凡三姊妹当中,大家公认她是最精明、最务实的一位。三姊妹中最小的宋美龄,成了委员长的夫人,业已愈来愈多地出现在中国公共生活的前线。她的机敏与通晓西方习俗,对那位一句外语也不懂的政府首脑给予的支持是无法估量的。在另一方面,宋庆龄,这位孙中山的遗孀,这些年来则一直处于隐居状态,并与其家族脱离了联系。偶尔(例如在上海大罢工期间,当救国委员会的领袖被逮捕时),因其同情左派分子而被迫隐居时,孙中山夫人也始终如一地忠于她丈夫的理想,坚持维护着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传统。她是中国革命中最使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以她的美丽和大无畏精神鼓舞启迪着年轻中国的所有进步力量。
不过孔博士一坐上新交椅,便似乎暂时忘却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论调被不厌其详地提起,这就是宣扬南京政府虽然处于一个独裁者统治之下,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此时国民党官员所最关切的,似乎就是要使世人确信:没有蒋介石,他们也同样能够继续把工作开展得更好。孔博士通过电台发表了长篇演讲,明确表示不同武装叛乱者有任何接触,与共匪也不能达成任何停战协议。并向全国人民做出保证:一定要维护政府的尊严,即使这意味着要凭借武力消灭“叛乱者”(此时委员长和他手下的一些最能干的军事人员也与他们在一起)也在所不惜。尽管这种“精诚团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似乎也不难看出,南京实际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至于此中缘由,也不难找到。
指派不同的人物充任各部门的负责人,而这些人的资历一般都似乎还能够胜任其职,但却不可能容许他们自身拥有任何非常强有力的或富于挑战性的思想观念,这正是蒋介石一贯采用的统治手腕。凡涉及重大的决策,最后的决定权总保留在蒋介石自己的手里。不难看出,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有利于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统治,而对于整个国家则完全不利。尽管如此,它依然勉勉强强地发挥着作用。毫无疑问,外国列强近年来之所以对南京政府表现出日益增加的信赖和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对蒋介石才干和实力的信任。
但即使在那些心怀不满的官僚们的内心深处,也将会滋生勃勃野心,而且生活在南京这座忧郁而杂乱无章的首都里,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众所周知的派系和小团体。这些派系在中国都是很知名的,只不过一般普通人不大可能知其内情罢了,除此而外,各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相互妥协、结盟也在频繁地发生着变化,使得即便那些中国政治的研究者们也会对此茫然不知所措,如坠迷宫。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西安的反叛期间甚为流行),用“亲日”和“反日”来区分那些派系,对说明问题也许更为方便一些。
这里需要对这些派系作一些说明。一般而言,任何中国人,甚至政治家,在中国这个风波迭起的历史阶段,通常大都会被看作是“反日”派。但在实际上,这一措辞目前理应被用于那些赞同对日本侵略采取积极抵抗政策,赞同至少在中国的某些显而易见的不满情绪未获得补偿之前,对日本实行不合作政策的政治领导人。在此名义下,聚集的有一些国外最熟悉的中国名人,他们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孙中山博士之子)、王宠惠及其他一些人,其名字通常被与那些称之为“欧美派”的派别联系在一起。他们大都是一些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人物,带有进步思想,并对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感情友好。所不幸的是,在西安危机发生期间,“欧美派”不那么得势,只有两个成员——孔博士和孙科——还有政府职位。但还有其他的派别组织,其性质属于自由派或社会民主派,只要能够获得机会,也会支持与他们相一致的总方针路线。
在另一方面(由于这里确实存在着有效的差别)的某些人,主要由一批军人组成。他们的权力是在蒋介石的直接庇护下获得的。对于这批人的政治力量,眼下还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在绝对忠于委员长的口号掩护下,显得默默无闻。与其他派别界限最明确的是人们所熟知的“黄埔系”,或称之为“军校派”,因为他们全仗“国民军”时期的军官们的支持。而在1936年12月,这伙人又恰巧处在特别强有力的位置上。
当时在这些人中的那些被视之为“亲日派”的人物里,有几位与委员长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物也可以被列入其中。他们包括像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多年来一直担任反共战役的主要组织工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外交部长张群;运输部长张公权;军委会成员熊式辉等人。就这些人单个而言,他们中没一个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他们拧成一股,代表的是一种鲜明的政策倾向:宁愿与日本合作,而不愿抵抗日本,并对中国共产党及建立联合阵线这一切合实际的观点怀有刻骨仇视心理。据中国许多地方的人们(不仅只是西北地区)推测,处心积虑地想要利用西安局势,通过干掉蒋介石,进行抢班夺权来为自己谋利的,正是以何应钦为首的这伙人。
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被安排负责迅速组建一支对付西安叛乱的“讨伐军”。而且也正是他,向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冒牌罗伯斯庇尔发出了邀请电,要他立刻从欧洲返回中国。汪精卫是这么一个人,即使在中国,他在政治上的投机记录也是出类拔萃的,以其与日本关系密切而为人们听熟知。他从欧洲通过海底电缆拍回了一份加急响应电,在临动身之前,还挤出时间与希特勒进行了会晤。随着蒋介石的被排除在外,这位副总理看到了这样一个天赐良机:领导一个以“黄埔系”军人系统为基础,并受到“反共协定”缔结国有力支持的政府。一听到汪精卫正要回国的消息,西安的领袖们毫不迟延地通知给了他们的那位囚犯,而对蒋介石来说,这则消息无疑会令他感到不快。他们俩是一对老冤家,在中国他俩毫无共存的余地。
蒋介石本人在南京的那些派别中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保持着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的姿态。既乐于在南京各派别之间相周旋,也高兴从中挑拨离间坐收渔利,以适应其总战略的需要。不管怎么说,在西安事变前的几个月里,他与军方人物的关系无疑达到了最密切的程度。而像冯玉祥、孙科这些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因为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并赞同与苏联结盟以对付日本人,自从11月在上海的大逮捕和发动新的反击浪潮以来,则受到了猜疑。不仅如此,另外有迹象表明,秘密组织“蓝衣社”(“Lan I shih”),在中国的公开场合谈论这个组织是非常不合适的,然而它作为一个半法西斯主义的团体,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狂热地反共,而且以前直接听命于委员长,已存在多年了)正在逐渐变得谁也无法控制。人们普遍认为,于1936年10月遇刺的湖北省省长杨永泰,便是“蓝衣社”的一个牺牲品。杨永泰也曾是蒋介石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显然,蒋介石是不可能会赞同处死他的——虽然他对于一年前发生的谋杀汪精卫企图,可能不会像这次这么感到恼怒。
总而言之,对当时的情况可以这么认为,在其被俘于西安期间,这位委员长所唯一不敢完全确定的,就是在南京究竟有哪些人才是他的真朋友。在12月12日之后,情况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变化,必然使他从内心深处为之一震,感受颇深。
南京断然拒绝与西安进行任何谈判,并调兵前去攻打叛乱者。甚至连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也乘坐着一辆豪华的私人小轿车前往陕西。他来此的目的是想要通过与冯钦哉的会谈,用贿赂从西北阵营里打开一个缺口,买通这位不履行协议者。但对于蒋介石的命运,南京方面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兵变不久,西安以东就开始爆发了敌对行动。时断时续的军事行动持续了好几天。南京飞机沿陇海线轰炸了好几个城镇,一中队轰炸机编队掠过了西安城。但反叛者们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他们只是埋头做着保卫西安的准备工作。
12月18日,委员长的得力助手蒋鼎文将军,被从西安释放出来,带着一封他的上司给何应钦的亲笔信飞到了南京。在这封信里,蒋介石预计他将在一周内返回首都,而在此期间,他要求能够暂停敌对行动,特别是轰炸。
在其关于西安危机的手记中,蒋夫人以极其生动的语调,描述了在那段令人紧张慌乱而忙碌的日子里,笼罩在南京军界里的气氛。她几乎是在单枪匹马地与被她描述为“萦绕在部分高级军官头脑中的一种可怕欲念进行着搏斗。因为这些人认定,他们意识到自己坚定不移的职责就是开动军事机器,并立即征讨进袭西安”。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已接管了空军。洛阳是河南的重要军事中心,也是对陕西首府西安发动袭击的良好基地,也为其所控制。似乎只是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和蒋夫人及其密友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对西安的空袭未能发生。
由于南京的战争贩子们不愿听到任何一句劝阻他们克制的话,甚至指控端纳先生“站在张学良一边”,肆意歪曲窜改他发自陕西的那些报告,尽管其中所列举的事实是完全可信的。基于同样的不妥协精神,他们起初曾拒不接受蒋鼎文将军带回的委员长的亲笔信。他们阻挠蒋介石夫人飞往西安(她还是在听到端纳所传来的消息后才产生这个念头的),并采用同样的手法,企图阻止她的兄长宋子文先生(前财政部长,也是南京政府治下最有才能的财政专家之一)响应张学良所发出的邀请。宋子文最后借口仅以私人身份去西安,靠谋略挫败了官方的反对,于12月19日飞离了南京。
两天后,宋子文和端纳双双回到南京,带来了和平解决事变和迅速释放委员长的一切希望。针对这一情况,蒋夫人一点不愿再等,坚持要陪他俩于12月22日重返西安。
宋子文成功地从南京方面的军事当局那里争取到三天以上的停战保证,而在这三天里,为释放委员长而进行的激烈谈判,在西安紧张地进行。蒋夫人和她的兄长非常清楚首都当时的情绪,也深知主战派把事情交由他们去办所潜在的危险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他们这几位秘密谈判者中,没有一个是南京政府的官方人士。他们所可能做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也许只不过是出于某种个人的本能,不可能提交给中央政府。但宋子文和蒋夫人的个人影响——更不用说委员长自己了——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在那几天里,最有趣的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恐怕要算是南京方面的官方态度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丝毫无助于委员长的释放和确保其人身安全。他们为那些祈求抓住机会进行谈判的人设置了一切人为的障碍。而这些人之所以祈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委员长的亲戚朋友,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普通公民,只不过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对国家的命运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倘若蒋夫人稍微有点不那么果断,照此看来,1936-1937年仲冬的中国完全有可能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所毁灭——一个能够博得全国支持的中国领袖的死亡,并由此而引起的内战爆发,其可能产生的唯一实际结果,只能是出现一场大灾难。在这里对少数几个能在这种时候保持清醒头脑的人说几句赞美的话还是合适的,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的表现都实在不怎么样。
作为委员长在西安获释前最后三天的实况记载,蒋夫人自己所说的故事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是由一位与所发生的事情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所讲述的。不过,其着重强调的是个人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已经知道,张学良几乎从一开始就准备释放委员长,并陪送其返回南京,条件是只要他能够令人信服地担保不再打内战。蒋夫人描述了“汉卿”即张学良当时的处境,说他本人对贸然逮捕蒋介石而感到悔恨万分,拼命恳求他的同伙们同意释放委员长。仅凭这段描述,也许还不足以公正地评价当时存在于西安各不同派别之间的实际合作程度。但她的记述中有一点是重要的,按蒋夫人自己的说法就是,西安的领袖们“在任何时候都从未提出过要金钱或增加权力和提高地位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外界观察家来说,蒋介石的被释放是个巨大的谜。在他们看来,似乎西北方面的领袖们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只是由于得到了巨额赎金的缘故。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蒋夫人关于“少帅”见她时那幅羞惭不已的样子,以及关于他建议要把委员长偷偷送出西安的记述,才是最不可信的。在她的记载中,蒋介石本人所起的作用纯粹是消极被动的。至于其他的人,除张学良而外,穷智竭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保住他自己的脑袋。当然实际的情况决不会完全是这样的。
在当时,有一点可以认为是公认的看法。扣押蒋介石既非是出自于个人野心的冲动,也不是私人冤仇使之然。它是一次政治行动,想借此影响到中国政策的转变,而在西北针对红军重新进行的一次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战役,则促使了它的爆发。由“叛乱者们”所倡导的政策,从“八点纲领”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改变政策的建议,委员长哪怕只消在原则上同意,无论从哪方面说,就没有理由再把他扣起来,从而冒“以内战结束内战”的危险。
让我们不妨暂时考虑一下西安方面对释放蒋介石所做的解释。委员长及其来西安探望他的亲友们一致同意,对少帅主张的“八点纲领”将给以适当的考虑。在此之后,由于南京方面黩武主义军人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从而使内战爆发的危险变得日益临近。而避免战端重开的最好办法,就是迅速释放蒋介石及其随员,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控制南京战争机器运转的人。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忠诚无私,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他已认识到自己对国家所负的责任,张学良执意要把他先前的这位俘虏陪送到南京。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简单得就像是童话里的故事,然而却是整个事件的真实写照。对此,只消作一些稍微现实一点的分析,对于产生这种高尚行为的部分原因,便会有所认识了。
没有人(至少那些熟知其为人的人)会相信,经过在西安的囚禁生涯,蒋介石会真的“洗心革面”。但作为一个明智的人,他还是服理的,并会重视舆论的力量——特别是在当时对其政治地位能产生致命影响的情况下。
从周恩来那里,从这个根据过去的经验使他不能不对之敬重的人那里,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南京政府展开全面合作,以换取他的某些保证。他们愿意改变其军队的名称,愿意使在西北的“苏维埃区”成为中华民国内部的一个“特区”,并承诺不继续土地和社会革命运动,直到抗日阵线得以实施。这是一种极其光明磊落的和平统一姿态,它是由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坚忍不拔,一直不受他约束的人提出来的。
蒋夫人在她关于西安的最后几天记载里唯一的一处关于共产党的叙述是头等重要的。她写道:“我们自始至终从未从‘赤党’那里听到一句威胁性言词。与外界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使我们确信,他们无意扣押住委员长不放。反之,他们倒更乐于尽快放了他。”她的记述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共产党把它的全部影响力,都转用在了迅速和平解决问题上。周恩来是位非常有说服力的发言人,认为正是由于他的那些建议才对蒋介石产生了某种影响,这是对事态顺利发展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即便从单纯的观点来看,委员长也会这样来推论的:与红军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较之于继续对他们进行代价极高的战役,不仅对他本人来说要减少不少麻烦,而且对政府而言也要划算得多,因为继续进行那场代价极高的战役显然已经变得愈来愈不得人心了(他在西安的处境是会不时地向他提醒记住这一点的)。
“少帅”不停地向他灌输人们所熟知的那套要求停止内战,建立起有效抗日组织的主张,因为他并不打算用威胁手段来促使主张的实现。西安的极端主义分子们可能会支持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由群众对他进行判决,但他们却得不到这样做的机会。当张学良发现共产党也赞同释放蒋介石的时候,他似乎感到自己可以放手行动了。然而毫无疑问,只有在与所有的助手们磋商之后,他才会采取行动。
毋庸置疑,对释放蒋介石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南京方面的态度,以及亲法西斯主义者、亲日派插手于中国政治权力的危险,这是蒋介石本人也不会不认真考虑的。因为这些被称之为“叛匪”的人警告他,需要提防的正是那些现在正在搞阴谋要毁掉他的人。张学良保护他,不使西安的极端主义分子得逞;共产党则全力说服别人支持释放他的主张。唯有在南京,在这个他原本期望找到他最忠实支持者的地方,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显然决定要发动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必然要以牺牲他和他的随员们的性命为代价。当他听到南京飞机吼叫着掠过头顶时,蒋介石必定明白了,他所面临的更大危险来自何应钦和他的轰炸机,而不是西安的那些逮捕他的人。
没有一个人——除那些希望从蒋介石的死亡中捞点什么的人而外——真的想要内战。如果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这正符合日本人的利益。南京的军人小团体就会趁机抢班夺权,而日本人则会在华北为所欲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这无疑是所有真正的爱国者们的利益之所在。唯有寡廉鲜耻的若干败类——这只是一小撮窃据重要位置的人——才热衷于制造战争。这就是一个独夫陷入险境后出现的局势,这种局势是不会不在他身上发生一定作用的。
就张学良而言,他可能原来指望从中国的其他地区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公开支持。如果出现了严重的交战局面,华北和西南的其他军阀无疑会出面调停,而其中也有某些人会站在西北方面一边。但到那会儿,大错可能业已铸成。如果蒋介石一旦被拉下舞台,再要想完成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都将是困难的。张学良似乎认准了这个道理,不值得冒这个危险;他的这个抉择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次抗日运动而开始的这场运动,在客观上却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迎合了日本的最大愿望——继续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
西安的许多赞同最终释放蒋介石的人,要求先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公开保证,或签订协议,然后才能放他走。能否得到这个保证,是很值得怀疑的。蒋介石是个很傲慢的人,无论如何,这种要求只能使他陷入尴尬境地,而且显然也会激怒日本人。在中国所能够干成的所有事情都是通过间接手段完成的:蒋夫人、宋子文等委员长的调解人,他们要比用强迫的手段搞到手的任何文件有价值得多。
圣诞节快到了,“宋氏停战”也已满期。空袭西安的危险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在增大,恳求释放委员长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了。那天一大早,由于“圣诞老人”友好地出现(正像她所说的那样),蒋夫人在谈论和平问题时显得比过去更为雄辩。而叛乱者中感情最脆弱的张学良,则是她的那些乞求言词的主要对象。他的侠肝义胆在经受考验:他要对委员长的生命安全负责,到今天为止,他一直保护他不受敌对分子侵犯,但他却无法保护他免遭他自己的国防部长的炸弹空袭,或避开受到威胁的普通群众的愤怒情绪。
由于知道他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因而少帅似乎是独自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当天下午,他老早就给杨虎城挂了个电话,向他这位闻言大吃一惊的同伙说,他本人准备立刻用飞机把委员长送回到洛阳。必须给杨一个简短的通知,因为“杨匪”有股倔强劲儿,不通知的话,将来是不会宽容他的。但杨虎城显然还是同意了他的安排,因为舍此而外的其他任何办法,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实际上,即便是到机场这一段路途,也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天下午,有消息说绥远地区中国防御部队的司令傅作义将军,要乘飞机抵达西安,因而在飞机场聚集了许许多多前来迎接的人。
临近下午四点钟,有两辆小卧车飞速穿过机场大门,经过静候傅作义的人群,一直开到停机坪上。当一些人觉察到他们认出的那个蜷缩在头辆车后排座位上的消瘦人影,正是面容苍白、留着黑八字胡的委员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一阵小声的嘀咕声从人群中传来:这不会是真的。要是这消息传到那些发血誓决不让蒋介石活着出西安的青年军官耳朵里,在这座陕西首府肯定会激起更多的暴乱。但小卧车径直开到了少帅那架巨大的波音飞机近旁,从而使离别行动做得尽可能地快。
在记载蒋介石离开的“官方”记录里,提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欢送仪式。也就是在这个仪式上,委员长表情严肃地斥责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并针对他们犯上作乱的罪恶行为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训导词。这篇演讲由蒋夫人以速记的形式抄写了下采,长达好几页。在中国的中学里,它已成为供学生们研习的一篇范文。
然而,要想弄明白究竟在何处、何时蒋介石曾发表过这样一篇演讲,这是困难的。依据对现场的最详细记载,蒋介石并没有做过临别的逗留。据说,当他们一起来到飞机旁时,蒋介石起初不敢进去,认为会把他用飞机拉到“苏区”。但“少帅”先他之前登了上去,于是他没有再谦让,也没有乘机再训导什么道德真谛。
不过,讲述委员长临别赠言的报告倒也有一个,经过了多方的证实,语气也要简捷实在得多。他从飞机上对杨虎城和陪送他的官员们说道:“过去我们双方都犯过错误。我的错误我坦率地承认。从‘双十二’到今天为止,我在这里当囚犯,发生内战的责任要由你们负。从现在起如再发生内战,责任就是我的。我决不想中国再有内战了。”
圣诞节下午四点刚过,巨大的波音飞机载着奔向安全地带的委员长,和前途未卜的“少帅”离开西安,向洛阳飞去。因为释放自己俘虏的张学良认为,唯有由他亲自陪着他去登门服罪,工作才算最后做完。而西安的朋友们,甚至连蒋介石(表面上如此)也都劝他说,他最后的这个举动毫无必要。在南京等待他的只会有危险,而不会是别的。
但张学良身上还带有某种浪漫色彩,这使他对自己所创造的这种引人注目的行为颇为欣欣然。他的宏伟计划(这真正来源于其个性)自然是要借此证明,他在西安事变中并没有心怀贰意,从而打消别人的疑心。这是一种科利奥兰纳斯式姿态,而现在却无法保证他即将落入同样的命运。
从飞机上,蒋介石开始把自己的诺言付诸行动。他下令陕西境内的“中央军”撤退到潼关以东,越过“叛乱”省份的边界。当天傍晚天擦黑之前,军队已经撤离华山,东行了廿华里。来自南京的挑战看来已经过去。
第二天,刚过中午,蒋介石的飞机便在南京机场着陆成群的人吵吵嚷嚷地奔上前去迎接他的归来;全国都为这种愉快的结局而欢庆。这位委员长似乎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得人心。
两小时之后,另一架飞机载着张学良和宋子文在同一个机场着陆。没有一个前来迎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