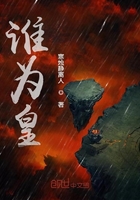秦历717年四月十七日,阴。帝都长安,勤政殿前广场。
“皇帝陛下万岁!”
“大秦帝国万岁!”
“……”
一阵阵的声浪将献俘仪式推向了最高潮。在队列最末压轴的是刚刚补充了新的战车的国防军第九十六卫。发出震天机器轰鸣的钢铁怪兽驶过第一大街的青石板路,顿时便让路旁观礼的民众热血沸腾。生出了有此强大武力,何愁战争阴云的情绪来。
不过,也有眼尖的民众看到勤政殿宫门上方的观礼台上,少了他们想要看到的某人身影。在这个接受万民欢呼的完美时刻,那个立下盖世功勋的人,究竟去了哪里?
“听说是病了。”人群中,不乏消息灵通人士。
“病了?病得当真是时候。我看是观礼台上有人不想让他威望过高罢了。”这是持有阴谋论的人的看法。
“也不见得,听闻帝婿没日没夜的工作。这可不是惜福之道,生病是迟早的事情。”
“没日没夜的工作?那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立刻有人驳斥这听上去荒谬的言论。转头嗤笑道:“莫非是长公主殿下偷人了不成?”
“噤声!现在这里到处是官府的暗探,你是想让咱们都去蹲大狱?”立刻就有冷静的人出口告诫。一群人顿时噤若寒蝉,这时献俘仪式已经临近尾声,民众再抬头向观礼台望时,发现观礼台上的皇帝陛下和一干重臣们都已离开。这才在村正里正的带领下,各自散去不提。
献俘仪式现场的欢呼声,自然也传进了未央宫里。孙铿卧在软榻上,手里依旧没有放下书本。听见声音抬起头来,略微怅然的叹了一口气。
“是不是恨不得马上病就好了,然后插上翅膀看看你的功劳?”羽衣轻笑道,顺手端起已经晾凉了的药盏,抢去他手里的书本,将药盏塞到他的掌心。
“倒也不全是。”孙铿叹道:“我在想那日的梦,先圣皇帝陛下究竟想要给我传达一个什么意思。”
“是你想的太多罢了。”羽衣道:“先圣皇帝若有灵,早就从坟墓里爬出来砍了现在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何必要托梦于你?”
孙铿小口抿着苦涩的汤药,皱眉道:“这见鬼的汤药要喝到什么时候?”
“喝到你完全健康为止。”羽衣随手写了一张单子,转交给身边侍立的良辰。低声吩咐了一句,良辰领命,拿着单子出去。
“我已经写了一些你需要完全忌口的东西。可可和茶是不能喝了,烟卷也要完全戒掉。”羽衣察觉到孙铿的疑惑目光,笑吟吟的解释道:“我还给薛汉臣下了死命令。从现在开始,你的工作时间只有八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就是抬也要把你从办公室里抬出去。”
“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孙铿摇摇头,索然无味道。
“乐趣有很多,比如安宁堡里有一群不听话的小崽子,如果你回去调教他们,我想效果会更好。”羽衣笑道。
勤政殿,皇帝陛下寝宫。
赢晚换了一身便服,回到了会客室里。有一位客人,已经等了他很久。
见到皇帝陛下进来,乔季站起身来,毕恭毕敬的欠下身去。
“乔老不必多礼。”赢晚双手搀住老人枯瘦的身体,温声劝慰道。
乔季这才重新落座,将手边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文件双手呈了过来,“这是陛下您要的记录,以及我对病情的一些见解。”
赢晚翻阅了一下,便随手放在了一边。抬起头来,目光炯炯的望着老医师道:“孙铿得的是什么病?”
“心疾!劳累过度,外加受了些风寒引发的。”乔季如实道:“孙铿的身体出乎我的意料,他非常健康。换做一般人像他这样拼命的工作,可不是惜寿之道。让他休息两三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就会恢复如初。”
“这样……”赢晚若有所思道:“那他的病与我相比,如何?”
“这不一样,陛下。”乔季缓缓摇头道:“帝婿有一副其壮如牛的躯壳,而您却不同。皇室一脉,历代以来,最健康的我只见过两人——庸亲王和长公主殿下。而您的身体状况,和先陛下有些相仿,甚至……”他沉默了一阵,决定坦白相告。“甚至还更加差一些。”
赢晚了然点了点头,黯然道:“看起来孙铿这样的人生,我一辈子是不要想体验到了。”
乔季道:“不仅不能体验,陛下您以后还要禁绝大喜大悲,大怒大惊。也就是说,心境要保持绝对的平和。再加上我为您调制的养心之药,才能得到与您祖父相差不远的寿数。”
“没有喜怒哀乐,人生还有什么乐趣?”赢晚索然无味道。
“这——”乔季恻然道:“这大概便是为王者的惩罚吧。”
“我知道了。”赢晚叹息了一声,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乔季起身行礼,安静的退了下去。
静室之中,只留下了赢晚一人。沉默许久,少年帝王才从深思中回过神来。走到书桌前,俯身写下一条命令。摇摇头又撕得粉碎,丢进纸篓里。摇铃叫来一个侍从,指着纸篓道:“把这拿去焚文坑烧了,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侍从捧着废纸篓离开皇帝的寝宫,径直前往位于勤政殿一角的焚文坑。每天的傍晚,都是焚文坑的工作时间。青烟袅袅升起,似乎夹着些许的墨香。这些低矮的砖房从勤政殿始建之初就一直存在,炉口经历过数百年的烟熏火燎,积攒下了厚厚一层炭灰。多少不能言说的秘密,从这些炉口进去,化为青烟飘上天空。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兵从侍从手里接过废纸篓,一言不发的走进去。侍从在门前翘首等着,过了几分钟之后,老兵拎着空了的纸篓出来,见侍从还在等着,冷冷多说了一句。“已经烧了,放心吧。”
侍从点头,焚文坑里当值的老兵从不言语,这是多少年来一直传承的规矩。多说这么一句,已经是违规了。他也不敢多问,接过纸篓便离去。老兵望着他的背影,唇边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手指缝间微微露出几枚纷乱的纸屑,他小心的将这些纸屑藏进衣袖中的暗囊里,若无其事的转身回到焚文坑的院子里去。
几个小时后,赢晚那张纸条重新回到了书桌前。一双苍老的手,将那黏贴的非常完美的纸条拈起来。对着烛光看了又看,最后还拿起手边的放大镜,一字一句的端详了许久。
“松翁能看出什么?”一旁的一个老人疑惑问道。
“字如其人。能看出一个人写下这些文字时的心境。”那位被称作“松翁”的老者放下纸条,高深莫测道。
“哦?那能不能讲讲看,这写字的人,究竟是什么心境?”老人饶有兴趣的追问道。
“笔法潦草,可见手书之人心情急迫,也许还有些慌乱和愧疚;着墨甚深,说明这件事情在他心中非常重要;写到最后几字,愧疚之心更强,落笔也显的犹豫不决。可见这条命令,在他快要写完的时候,已经开始后悔了。所以,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被撕得粉碎,丢进废纸篓里。”说完这些,松翁拿出一本写着“绝密”字样的书本,递到另一个老人的手里。得意的道:“这是孙铿教我的!这竖子,肚里倒是有些才学。并不是个草包。”
书本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三个大字“笔迹学”。下面一行小字,写的是:安宁堡少年营特侦科培训教材。编号被特意涂黑了,显然松翁不想让老人知道这本书的来历。
老人对松翁的心思哂然一笑,接过书随意翻看了几页。大串的理论教育让他顿感了无兴致。随手丢到一边,淡淡道:“这人的才学已经经过明证了。飞艇、火神、一式火箭……还有最近刚在第一大街上跑过去的一六年式装甲拖拉机!据说还有更猎奇的,十三区已经立项了大半年的时间。只不过咱们的人都太过脓包,总是打探不出所以然来。咱们还是说说皇帝陛下这条命令吧。是不是证明,这小子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信任?”松翁仰天大笑道:“信任这个东西从来都没在皇室的字典里存在过。赢晚相信的人只有他自己,甚至连长公主殿下,都是他要防备的人。”
“那……又是为何?”老人不解道。
“听说最近孙铿生病了。”松翁拿起一本书来,随意翻了几下道:“心病。”
“心病?”老人面露惊喜之色,“这小子活不长了,心病可是绝症。他这么卖力的工作,可不是惜寿之道。”
“是吗?”松翁讥讽的笑了几声,“那可要给院长阁下多找些乐子才是。”
“您是说……”老人面色一肃,垂首轻声询问道。
“那个计划,该启动了。”松翁叹了一声,面露萧索之意。“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会为了这个竖子的死活,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说完,他轻轻吹灭了烛火。等到老人再次点亮灯盏时,座位上已经空空,哪里还能看到松翁的影子?
老人叹了口气,站起身从密室中走了出去。这是长安闹市区最高的一座重楼,从阳台上俯瞰下去,这座繁华的城市尽收眼底。他沉默了几分钟,淡淡吩咐道:“给我备车,去长安客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