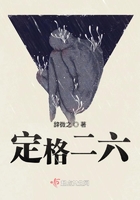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密云圆悟在天童山圆寂,在众人的请求下,道态继掌天童法席,由此走上弘法度人的道路。依《天童弘觉态禅师语录》所载的次序,道态出世之后,先后出住过天童山弘法禅寺、慈溪五磊山灵峰禅寺、台州广润禅寺、越州大能仁寺、湖州道场山万寿禅寺、青州法庆禅寺,然后再住天童山弘法禅寺。顺治十六(公元1659年)年,道态奉召人京为顺治皇帝说法,深受器重,受赐“弘觉禅师”法号。《五灯全书》卷六十六载清世祖顺治帝亲自迎接道态“进万善殿,驾随到,传谕免礼”,“赐座慰劳毕,即留师结冬万善殿,驾数临幸”,“上与学士王熙等,致问甚多,具载师《全录》”。道态在京师,凡在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顺治帝待他隆礼有加。然道态还是屡屡推辞,请求还山,顺治帝最后还是同意道态回南方,但留下了他的嗣法弟子月山晓晳(一本作“晓晳”)。道态京居凡八个月之久,辞归时,顺治送至北苑门,命使臣护归,并御书“敬佛”二大字与御画二幅以赠行。
道态离开京城之后,曾游历各地,到处宣扬他与顺治帝的问答机缘,对诸山与新王朝关系的理顺,做了大量的工作。《五灯全书》载道态回山后,“投老会稽化鹿之平阳,相山择吉,鼎建宝坊,卜诸兆宅于黄龙峰之下”,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准备好了安葬地。康熙甲寅(公元1674年)六月二十有七日,道态圆寂,“世寿七十九。僧腊五十五”。道态着有《弘觉态禅师语录》二十卷,编有《禅灯世谱》九卷,另有《弘觉态禅师北游集》六卷、《奏对录》、《山翁态禅师随年自谱》、《布水台集》、《百城北游》等。其中,《北游集》一书,被清世宗视为“不敬乖谬之书而销毁(今语录与《北游录》均收在《嘉兴藏》《随年自谱》则收载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东方学报》之中。道态的门人很多,《正源略集》载其门人有达变权、拙岩怀、天岳本昼、巨灵蟎、天岸升、云叟住、佛日晓晳、森鉴彻、古田元、冲然义、以夫可、节岩诱、灵远应、献可寂、神山瀛、南云晔、大雷庆、怀光灿、旷圆行果、芥庵大等。
之.道态的庙堂禅学。
(”道态的禅教。道态在圆悟门下得道之后,继主天童法席,其禅教在继承圆悟禅法的基础上略有改进。一方面,道态对正传、圆悟以来的剀切禅风有所继承,他继续采用喝、打来截断学人的拟思,使之当下领悟禅法的所在。另一方面,道态在接机中又并非一味地采用喝、打作略,他有时也采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来接引后学,有时还采用臂喻来激发学人的参悟。在道态看来,他之所以要采用喝、打的作略接机,无非只是“活人须用杀人刀”,这便是他继承圆悟喝、打接机的原因所在。在《天童弘觉态禅师语录》中,颇载有他的这种接机因缘,兹举三例如次。
僧参,展坐具,师拈拄杖。僧收坐具,师便打。僧喝,师又打。僧复喝,师挞下拄杖,云:“不打这死虾蟇。”僧无语,师云:“了?”复拟开口,师云:“且坐吃茶。”
僧参,人事件件,数云:“此是金华的,供养和尚。”师蓦竖拳云:“且道这个是那里的?”僧拟议,师云:“且坐吃茶。”少间,僧进云:“和尚除此外还有么?”师挝下拄杖,僧拾安旧处,师便掌。
僧问:“眼横鼻直时如何?”师便打。云:“老汉!不得草草打人。”师云:“今朝草草打这个汉。”僧礼拜,师云:“是你草草?我草草?”僧一喝。师云:“却是你草草。”僧拟议,师直打出方丈。
在第一例中,师徒见面首先是采用“展坐具”与“拈拄杖”等身势勘辩,待到学人收坐具时,道态便打去;而学人则用“喝”来应机,道态则再度打去。及学人再度“喝”时,道态才扔下拄杖,而面对这一机锋,学人却无语应机了。于是道态进而以“了”来激发其疑情,就在学人准备开口之际,道态的一句“且坐吃茶”,便把他刚刚生起的疑情打碎了。在第二例中,前来参学的僧人拿出礼物件件,并逐一说明这些供养的来源,道态便蓦然竖起拳头问学人“且道这个是那里的”。面对这一猝不及防的机锋,学人进入了迟疑之中,无言以对。此刻,道态用一句“且坐吃茶”缓和了气氛,而学人在稍有缓和之后,拟心又生,他反问道态除了竖拳之外,还有其他开示禅法的作略没有。此时,道态便扔下拄杖,学人则把拄杖拾起来安放在原来的地方,面对学人的这一伶俐的做法,道态立即一掌打去。第三例的接机则更是凌厉剀切,学人的问话把禅机推向了极顶,因而道态劈面便打。当学人要求道态不要草草打人时,道态便道“今朝草草打这个汉”。待到学人礼拜时,道吝再度勘验是谁草草,学人则以“喝”来应机,道态便指出是他“草草”。面对最后的这一机锋,学人却出现了犹疑,于是道态径直把他打出了方丈。在以上三例的接机之中,道态虽然均采用了打的方式来接引,但他并不像圆悟那样单单施展一条“白棒”蓦然便打,而是身势与言语兼施,只在关键时候才出手打破学人的拟思。
而在道吝的接机中,大多数场合是后是采用比较平和的方式。一次,一位禅僧请教道态某甲看个‘万法归一’,不会其中意旨。”道态便问他在寺院中是住在那一堂,学人不知这寻常句下藏机锋,便告诉道态是住在东禅堂。但道态对此并没有采用凌厉的作略,只是用一句极为平常的“归堂去”来激起他参究。又如一僧来参,道态问他从哪里来,学人回答从河南来,道态则用“我不问河南,问你那里来实质上是问他“生从何来”,自然也暗示了“死向何去”之意)一语进而勘验,致使他踌踏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道态施礼让他坐下,从而缓和气氛。学人因此也敢于请教道态“达摩西来意旨如何”了,而道态则以一句“你从河南来”,指引他去体验自身参学的当下意旨。
有时,道态的接机会采用比喻的方式,从而启发学人去参究。一次,有学人问道态“春至人间无硬土,因甚枯木不生华”,道态则采用偈颂的方式回答他:“意气不从天地得,英雄岂藉四时推。”在道态的这半偈中,蕴含了禅法的参究在学人自身,因而任何外缘均只是一种促使开悟的条件,而最终的了悟毕竟取决于学人自己。又如一库子(为禅家司掌会计事务之行者)请求道态开示,道态顺势道:“莫偷常住果子吃”。这一反常的开示语致使库子陷人了疑团之中,他径直告诉道态不会其中意旨,此时道态以一句平常的“不会且囫囵吞却”将之接引。偷吃常住果子的掌故,原本出自于《景德录》卷十二《睦州陈尊宿传》,本是睦州勘验后学激发疑情的话头。道态借用这个话头来接引库子,同样激起了他的疑情,就在库子疑情萌生之际,道态的一句“不会且囫囵吞却”,看似平和,然机锋如针藏绵中,一触即会血淋淋。
诚然,在道态的接机中,许多场合是松紧并用,使学人在那机锋的一张一弛之中领略禅法的真实义趣。有时,道态的接机先弛后张,让学人在经过平和的接引之后,蓦地提撕,当下体悟禅法意旨所在。例如有禅僧问道态“万法归一,如何是一”,道态平和地告诉他就是“适来礼拜的即参学的禅僧本人学人在此接引下,自然会去反省自身,从而观照“一”之所在。然而这禅僧并未当下领悟,却在继续问道态“一归何处”,对此,道吝猛然喝着说:“且拕这死尸去!”这最终的蓦然截流,对于斩断学人的拟思,促使他反躬悟道,自然是非常有益的。又如一在家居士问道态“弟子终日社梦,何日得醒”,而道态的接机则以“我这里醒亦着不得,梦自何来”一语,简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居士并未当下领悟,他还在问道态“争奈即今见梦何”,此刻,道态猛力朝居士推去,并提醒道:“醒醒着!”显然,这最终的用力提撕,自然会促使居士当下省悟的。再如:
居士问:“古人念念杜定慧,为是悟事、悟后事?”师云:“待你悟了向你道。”忽闻墙外买菜声,师云:“且道此人杜定慧外、在定慧里?”云:“定慧里。”师云:“以何为验?”云:“验在闻中。”师云:“还我适才问头来!”云:“非非想天去也。”师打云:“因甚却杜这里。”士无语。
面对居士提出的“悟前事、悟后事”,道态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说“待你悟了向你道”,这就如同赵州回答学人栢树子几时成佛的“待栢树子成佛时”一语如出一辙。就在这平和接机之时,墙外忽传来叫卖小菜的吆喝声,道态顺势问居士卖小菜者是在定慧内还是在定慧外。而居士却回答在定慧里,道态进而问他以何为验,居士回答“验在闻中”。道态则要居士当即归还适才的问话,而居士却大胆地说“到非非想天去”了。恰在此刻,道态蓦然朝居士打去,并问他自己为什么却还站在这里。这直下的一语勘验,自然会杜绝居士斗机锋时所驰骋小聪明,使他当即把外驰的心收回,回头照察自身以见性。
有时,道态的接机会采用先张后弛的作略,这样可以将学人在提撕之后,于稍事放松时蓦然见道。例如有学人问道态“才涉思维,便成剩法,思维有什么过”,道态在他问话声刚好落定时蓦然把他推出手炉,反问他“你试思维看”。学人经这一逼拶之后,进入了拟思之中,此刻,道态以平和的语气道出“才涉思维,便成剩法”,使之当下自省。又如有僧问道吝“如何是承言者丧,滞句者迷”,道态乃厉声道:“不快,漆桶!更是阿谁?”致使学人顿时进人拟议之中,恰在此时,道态以平和的语气道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像这样采用一张一弛之道来接机,或先紧后松,或先松后紧,自然可以使学人在参学中的情志处在恰当的状况中,因而也很有利于他们的悟道。事实上,道态之所以会这样去接机,乃是因为禅法自身的特质决定了他要如此做。在道态看来,禅法“如天普盖,似地普擎。翕也纤尘不立,张也横亘十方;释迦明辨无由,佛祖侵欺不得,一切平等,浩肽大均。说智说愚不得,说迷说悟不得,说理说事不得,说如说异不得。所以道灵秃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想,即如如佛。由于禅法自身具有这种特质,加上前来参学的禅僧的根机又各呈差异,因此作为禅师的施教,自然要随物赋形,观机施教了。
道态的庙堂禅学。道态的禅学思想代表了圆悟门下归顺皇朝的一派,因而我们把它称之为庙堂禅学。在《北游集》中,记载了道态进京与顺治帝的奏对机缘,所涉猎的话题除了禅宗之外,还包含了前代历史、文学鉴赏、书法技艺等方面,与此同时也包含了家常小事与人情寒喧等各种内容。对于道态应对顺治的语录,学界多持否定的态度,然客观地看来,道态与通诱之间毕竟存在许多差异,且在道态的觐见之中,除了阿谀庙堂之词以外,也仍有少数讽谏的微言,应该加以认真对待。在明清鼎革已成定局之际,道态被顺治帝反复征召,他不得不进京,处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自然是不容许他有多少忤逆的言行的。他的觐见与归来后的游历百城,到处宣扬其奏对因缘,为顺治帝更好地控制禅宗乃至整个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道态给顺治帝理顺皇室与禅宗乃至佛教的关系的同时,也给佛教的生存与发展营造了一定的空间。况顺治对待禅宗仍然存有一些的信仰,他并不完全像雍正那样自命作家君王,摆出南面的架势来整饬禅宗与佛教。
通观六卷本《天童弘觉态禅师北游集》,道态的进京觐见顺治应该是成功的,顺治帝曾多次命近侍持黄箧,传旨道态给他起名字。起初,道态给顺治起名“觉王”与“义成”,但顺治帝并不同意,他命中使传谕道态此乃诸佛洪名。朕何人,敢当此字!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可也。”道态乃改名“慧弃”与“山臆”,顺治遂以‘慧弃’自名,‘山臆’作字,刻玉为章,用之书画焉”。是后,道态还给顺治起了“穆庵”、“査庵”、“幻庵”等十二个名字,顺治则启用了“幻庵”二字。后来,道态还给顺治起了堂名,他起“师尧”之名作《师尧说》以进奉,获得了顺治的赏识。与此同时,顺治不但给道态赐号“弘觉惮师”,还以庐山瀑布水源处的地名给他的文集命名《布水台》,并命内廷画师给道态画像。对于顺治帝赐予的这些殊荣,道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在南归之后,曾作诗曰:“惭受天恩渥,惊闻佛事开;社资心意广,不惜大官财。仙梵凌天际,天真降九垓;为僧今半百,恍误(惚)蹋瑶台。尤其是他作于南归游历百城之后的《敕赐别山慧善普应禅师真赞》一诗,更是对昔日的皇恩眷恋不已:“百城访罢人烟萝,宗说滔滔似决河;盏洗禁池倾白月,经翻古洞涌金波。饮人以德同慈妪,荷法唯公绝比阿;道影师名重迭赐,袈裟沐尽御香多。道态的这两首诗来看,他对顺治的那种感情也并不完全是出自于应酬,而是出自于内心的感激。那么,道态的短短八月京师觐见,何以能产生如此深的感情呢?其间除了君臣情谊之外,更有一种宗教情怀牵动着他们两人的心。
首先,顺治帝毕竟是一代信奉禅法的君王,他对道态不但礼节周到,而且自己也曾身体力行参禅。在《北游集》卷二,载有顺治参禅的机缘语录,兹录一节如下。
上随问:“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何是不传的事?”师良久,问上云:“陛下会么?”上云:“不会。”师云:“只这不会的是个什么?是何境界?作何体段?皇上但这么翻覆自看,看来看去,忽若桶子底脱,自状了办。”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语看。”师云:“无毛铁鹞过新罗。
平心而论,从顺治参学的问话与道态的接机语来看,都是围绕禅法展开的,其中并无任何政治色彩。只是对待顺治的开示,道态不可能像平常的接引禅僧那么随意,乃至施以喝、打,他在不违禅法根本义趣的前提下,做了契理的开示。且最末的“无毛铁鹞过新罗”一语,也是纯然本色的禅家机锋语。顺治接着请益“如何做工夫始得与此事相应”,通诱门下的茆溪提出“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而道吝则认为“此语杜我禅和家即得;皇上日应万机,若一日稍不励精,则诸务丛脞矣。”当顺治再度请教“毕竟如何用心即得”时,道态这才指出:“先德有言,但能于心无事,于事无心,则虚而灵,寂而妙。皇上但遇大小事务,不妨随时支应,事后反观向来酬应的,毕竟从什么处起,从什么处灭,刻刻提撕,念念不舍,自然打成一片,事事无碍。显然,道态的回答比较适合于身为帝王的顺治之实际,事实上身居九五的帝王参禅,也只有在日理万机之余,反观先前的庶务,才能使朝政与参学两不误。可见,与茆溪相比,道吝在观机施教方面毕竟要老成得多,因而他与顺治之间的道谊也比较深厚。接着,顺治还向道态提出了如何使参学的念头不间断、参禅悟道后是否还人轮回等一系列问题,道态一一为之解答,其答话均契禅家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