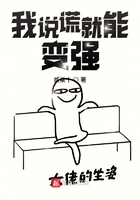师范在华严家的这一思想影响下,还进一步就总别与异同等范畴展开过探讨。在一次中秋的随堂开示中,师范提出了:“寻常月是中秋月,中秋月是寻常月。看来真个只寻常,道是寻常又还别。别,别,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续华严家的“六相”中,有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六种范畴,五代时期的法眼文益禅师曾将此引人其禅学思想体系中,并有过许多精彩的开示。到了宋代,禅学思想趋向于整合,各家的宗风逐渐地融合起来了,因此旁宗的前代祖师的禅教,也被他们所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师范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平等不碍分别,分别不碍平等”的禅观。他在一次上堂中说:“万别千差,处事同一家;事同一家时,万别千差。本着这样的禅观,他在禅修上主张“于其中间觅一丝毫彼我之相,了不可得,得到这个田地,是谓一味平等,无有高下。实,在禅家中,这种思想的最早提出,应当是中唐时期的青原系禅的实际开山祖师石头希迁,他在《参同契》中提出了“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的禅观。这一思想一直被作为青原禅系的根本思想,且在曹洞与法眼儿孙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到了宋代,各种灯录与公案文字迭出,加之评唱公案的文字禅也应运而生,自然会促进宗门之间的融合,从而彼此吸收其合理的禅学思想。诚然,站在具体的接机作略的方面来讲,确实存在着宗门之别,然站在一味平等的禅法本体来说,毕竟无任何分别可言。何况,在师范之前,曹洞宗的大阳警玄曾在圆寂前,修书拜托临济门下的浮山法远,让他代为传付法嗣。这一使命的完成,比起借鉴旁宗禅法来说,显然要更为进了一步,因为他必须精通旁宗思想与机锋作略才能做到。
之本自具足,直下承当。在明确了禅法的本体之后,师范于接引学人时,不但注重对禅法本体的开示,而且也没有忽视让学人在证悟本体的同时,去认识森罗万法的差别性。本此原则出发,师范认为这个作为“万物之母”的“大道之源”,在每人心里是本来具足的,因此,只要能够扫荡干净心头的尘垢,自然就会见到这个“大道”了。因而,师范认为:“我宗无语句,亦无一法与人,只贵各人自己鼻孔端直而已。显然,这也是禅门的祖师所常开示学人的一个句子,它揭示了禅宗提升学人自性的一贯主张,也体现了师范强调“自力”的禅学思想倾向。
在一次结夏的小参中,师范曾给学人这样开示过:
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言发非声,色前不物。才开口,触着空王祖讳;拟动步,踏断弥勒脚跟。头头总是生涯,处处无非妙用。所以道“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在师范这里,不但“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就连发诸口耳之间的语言也并非声音的本质,见诸眼前的景象也并非色法的实相。因此,就禅法的本体而言,只要开口便会触着“诸有”;只要举足,便与禅道大乖,它必须在离言语与一切有为的境界之外去证悟。只要进人了这一境界,也就万法皆空,一切随缘自在,乃至“头头总是生涯,处处无非妙用”了。为了让学人实现这一境界,在寻常的上堂中,师范不惜方便开示。他曾引经做过这样的开示:“鹄白乌玄,松直棘曲,山僧反复更思量,六六原来三十六。”其中的“松直棘曲,鹄白鸟玄”一语,出自于《楞严经》卷五中,前代祖师也常举过。在师范这里,他引用了经文之后,随即通过反复思量,而得出的结论则是“六六原来三十六”,这无疑是在启发学人去领悟“本来如此”、“本自具足”的至理。学人只要明白了这个至理,也就会从自家心地用功了,因而师范无时不在提示学人“伸脚原在缩脚里”的原理。
既然学人心中本来具足了“大道”,因此也无须假借外在的修持,只须朝学人自家心田直下悟去,便会获得月白风清的美景良辰。为此,师范告诫学人大凡明辨古今,决断是非,也须是斩钉截铁始得。”叫也的这一主张,纯是对临济直下承当作风的发扬,也是对六祖以来的曹溪顿旨的合理继承。在日常的开示中,师范曾如拉家常似的对学人说:
若论个事,直是省要易会,多是诸人自作艰难,自作障碍。所以有时东廊西廊见诸人和南问讯,山僧便乃低头相接。其实无他,只要诸人识得长老是西川隆庆府人事。若识得去,便与诸人打些乡谈,说些乡话。如今且未说你识得长老,且各自知得自家乡井也得。
“佛法本平常,莫作奇特想”,这是丛林中流传的名句。可是,出人丛林参学的禅和,往往容易堕人无尽的分别思量之中,乃至“自作艰难,自作障碍”。因此,师范提醒学人的悟道,只有去掉分别心,只须在寻常的见面问讯等曰常生活细节中去体会,才能识得“自家乡井”。在寻常的参学中,师范要求学人“不起一念”,“直得水云杂沓,凡圣交参,彼我情忘,主宾道合”。在师范看来,“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只有达到“说听俱忘,语默不二”的地步,才能进人“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一进一退,悉皆不二,是谓微妙清净平等不二法门”的境界。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执着很重的学人,师范虽然不像前代的祖师那般使用棒、喝等激烈作风,但其接引也颇具临济迅疾直接的机锋。他在平曰常常告诫学人,到他门下是“无道可学,无禅可参”的,只有用平常心去体验才能悟道。在一次端午节的开示中,师范的机锋语句,颇有临济“扫荡一切”的余韵在。
今朝五月端午,乳峰收得一服药,不是耆婆留下,亦非扁鹊传来。虽然不值分文,要且无病不治。所谓佛病、祖病、禅病、心病,一切毛病,凡曰服者,悉得痊愈。乳峰不敢珍惜,今日击鼓升堂普施大众,若是有病者来,左手吩咐;无病者来,右手吩咐。且道因甚如此?有亦不有,无亦不无。
好一个“佛病、祖病、禅病、心病,一切毛病,凡曰服者,悉得痊愈”,颇与临济老子的“逢着便杀”的作风相似,这等机锋,显然是对临济家风的赓续。
诚然,临济作风发展到南宋之后,也减轻了那种“痛下针锥”的锐利锋芒,因而师范在扫荡之余,还不吝开示禅法“有亦不有,无亦不无”之理。
玉指出两病,歇心对治。针对丛林中出出进进的禅和,师范在慈悲接引之中,逐步地发现了当时禅林中所流行的种种弊病。为了更好地促使学人悟道、更好地扭转丛林中的这些偏锋,师范对禅林时下的弊病进行了针砭。他在《示湛上人》中说:
学道无过两种病:若不滞在澄澄湛湛中,便在纷纷扰扰处。猛烈汉痛与摆拨,腾身一踯,透过那边,非但彼我声色能所俱亡,求其生死征兆了不可得,方谓之大休大歇大安乐、绝学无为闲道人也。到得恁么田地,犹只名自悟自了的人。若论蜀之三十六江,前头大有滩在,切宜勉之!
所谓学道之人的两种弊病,一种是“滞在澄澄湛湛中”,即落在禅门通常所说的“厌喧求寂”的独觉之病中;第二种是“滞在纷纷扰扰处”,即落在世法的纷纭纠缠之中。在这两种弊病之中,前者虽然于悟道有个人处,但偏于静处,不懂得如何去圆融世出世法;后者虽能容摄世法,但毕竟昧失了佛法作为出世间法的特质,落人了碌碌红尘之中。因此,师范才唤醒学人,让他们“腾身一踯,透过那边”,做到“非但彼我声色能所俱亡,求其生死征兆了不可得”,从而实现“大休、大歇、大安乐、绝学无为闲道人”的终极目标。然而,达到这样的境界,在师范看来,还只是“自悟自了的人”,而要实现自度度人的目的,还必须具有种种圆融、种种善巧才行,因而也必须努力继续前行。
在指出了当时丛林参学的两种弊病之后,师范针对这两种弊病,提出了对治的方法。师范对治这两种弊病的主要方法是“歇心”,即休歇学人的攀援心、求道心与一切分别心识,从而让他们用平等的心量去观照世间万物,获得不偏不倚的中道实相观。师范平日告诉学人“道在日用”,“若滞在日用处,则认贼为子;若离日用,别讨生涯,则是拨波求水。与此同时,他在《示仁上人》中,对此还有过更加详细的阐述。
道不可求,责在歇心而已。然此之一歇,不可强也,须假朝求暮讨,至意路绝处,忽然自歇。一歇之后,驰求之心悉皆止息,有如途路旅泊之人,欲诣其所,力在乎行,非行不能到。一到之后,伶俜辛苦等事悉皆止息,无复奔走。岂不见善财历五十三参,至弹指处,楼阁门开,入已(已)还闭,从前所得法门,所见境界,悉如梦幻。
在这里,师范所说的“歇心”,是指学人经过丛林参学的一番痛苦磨砺之后,再把他们求道的驰心放下,自然会如同长路奔波的游子忽然找到了归宿一般。此时,学人原先苦心寻觅的那个“道”,却也在休歇了诸缘之后,忽然出现于心头,使他蓦然获得了“春在枝头已十分”的悟境。可见,这里的“歇心”,实质上是针对进入丛林参学已久、苦耽参究的那一类学人而言,而不是针对刚入禅林的初学。
从上可知,师范所说的“歇心”,必须是在“历五十三参”之后,才能如此去做。反之,对于那些参学不久或者参学不深人的禅和,师范还会时刻警醒他们,让他们不要把时光“从脚跟下蹉过”。他在上堂中,还这样给学人开示过前面是悬崖万仞,后面是荆棘丛林,两边烈焰,火聚于中。如何转身?到这段开示,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譬喻经》中的破斥贪恋世法的一系列譬喻来叭看到那些触目惊心譬喻,自然会使我们立即警醒的。
此外,在师范平时的开示中,也不乏种种善巧方便,足以启发学人悟道,今举两例如下。
元宵,上堂:“人看人,火照火,无杂坏,忘彼我。与么会得,许你亲见燃灯如来,得受记别。如今十个五双多是坐在光影里,动椒随人脚跟后转,乃高声云。大众!众举首!”复云:“不信道。
上堂:“去年梅,今岁柳,颜色馨香依旧。依旧则故是,因甚南枝向暖北枝寒?”拍禅床云:“莫道春风有两般。”
在这两则开示中,前者先说出平等境界,然后蓦然指出当时不少学人“随人脚跟后转”,以激起学人疑情。恰在此时,师范忽然叫大众抬抬头,正当众人抬起头来时,他蓦然一句“不信道”,便把他们心头的分别心识打掉了。后者则先营造一定的意境,激起学人的分别意识之后,猛然一句“莫道春风有两般”,便把学人的分别心驱除干净了。像这样纵擒卷舒的教法,完全能够让学人在差别中见出平等,于平等中不昧差别,也可谓高明的禅教作略了。
1融合三教,重视外缘。面对与佛教并存的儒教和道教两家,师范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早在宋初,儒佛之争曾一度十分激烈,甚至还有许多大儒提出过排佛的主张,因此云门宗僧人契嵩作《辅教篇》,力图调融儒佛之间的冲突。李唐时期,道教曾一度被奉为国教,而在赵宋,也有几代帝王是信奉道教的。为了争取禅宗弘法的空间,顺利地弘扬好禅法,师范势必会将处理好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三教关系上,师范避开了三教各自的优劣之争,他在皇宫对答宋理宗时说:“三教圣人同一舌头,各开门户,鞠其旨归,则了无二致。”这就是说,三教同源,它们的修行方式虽然各自分道扬镳,但其最终目标却是相同的,因而三教之间是一种殊途同归的关系。
其实,师范还不止是在朝廷的奏对中主张调融三教,而且还用偈颂的方式传授学人,使其徒众自觉地接受这一主张。在他的偈赞中,还有一首《三教合面相》的偈子:“一三三一,三一一三。解不能散,聚不成团。今古合成闭口面,只因门尸(户)有多般。”至于这个“三教合面相”,在当时是雕像还是画像,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尊偶像被供奉在师范的径山道场,应当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师范认为三教之间是一种既无法拆散,而又不可能整合的关系,三者应当各自分道扬镳,而又共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整体。站在中国思想史的角度上讲,三教之间的互相碰撞与融合的整个过程,不但是中国佛教所无可回避的事实,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全过程。主动的调融三教关系,这不但可以为禅宗的发展争取恰当的生存空间’同时也可以使禅宗的发展更加趋向中国化。
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在师范的开示中,处处可以见到他援引佛典乃至儒、道经典说法的例子。我们姑举几例如下:
谢两班上堂:“方交正月一,又过了五日。世事冗如麻,光阴劈箭急。所以道:‘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乳峰看来,又有什么不乐处?东边有知事,西边有头首,山僧赢得倚栏杆,尽日仰头看云走。阿呵呵,时人往往听作山居歌。吻(入焦山普济禅寺)佛殿(开法〕:“你不识我,我不识你,狭路相逢,脑门着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师召大众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吻上堂:“古者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损。’正恁么时,蜻蜓许是好蜻蜓,飞来飞去不曾停;捉来摘除两个翼,便是一枚大铁钉。”
在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援引佛典开示,“是日巳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分别见于出《法句经》卷一、《出曜经》卷二与卷三。第二例中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一语,是出自于《周易‘系辞上》。第三例中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出自于《孟子尽心下》。第四例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损”,出自于《老子》第四十八章。像师范这样援引三教典籍开法,而且又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可见他对三教融合完全是出自于诚心,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与此同时,师范对于禅修,不但强调自力,同时也很重视外缘,他在《示垠侍者》中,曾有切身的经验之说。
学道如世巨商,经涉大海,渺无涯际。始须假舟楫,想橹棹。及其到也,只在须史。正恁么时,回视前来所用功力,一时俱息,当下自然稳贴贴地,奇珍异宝悉皆现前,方是自家元物。然后周贫济乏,随意运用,不由别人。在这里,“假舟楫,憩橹掉”这两个譬喻,正好把自力与外缘二者间的关系给道破。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在具体的办道之中,师范也不拒绝来自于帝王家的援助,因而使得几度火毁的径山道场不但获得了及时的修葺,而且屡屡扩大了原有的规模。但在这里,我们也得如实地说明,师范在争取帝王家外缘的时候,曾说过不少阿谀皇室的话,这在《奏对录》中,几乎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交代火灾事故上,他居然有这样一段无稽的搪塞之话:
在昔邸园精舍,亦罹此厄。唐宜律师尝问韦陀尊天曰:“世尊无量福海,当说法时,十方诸佛、诸大菩萨、诸天龙神悉皆毕集,是谓宋吉祥地、隶殊胜处、何得有此厄耶?”韦天答曰:“此南天王天乘大愿力,当重新此寺,是以爇之。
如此巧言令色,实在有损一代大禅师的形象,很不值得后世效法。至于他在皇宫中所恭维理宗的“须弥山为笔,香水海为墨,尽大地为纸”等肉麻话,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雪岩祖钦及其禅法